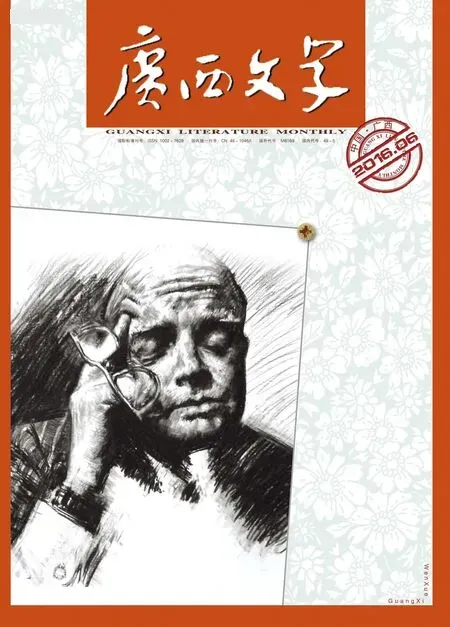散文新觀察之李存剛篇
劉 軍/著
生老病死作為人的基本身體屬性,因其苦與痛的相伴,固然在日常狀態中常常被懸置,但在精神屬性上始終扮演著達摩克利斯之劍的角色,進而高聳于人的心理結構之中。早期宗教、哲學的重要理念大多由此人本問題而衍生,佛教、道家哲學對身體的否定,希臘時期犬儒派對身體的推高,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而文學對生老病死的觀察與體驗,則遷延不絕,常讀常新。
單就疾病而言,物理性層面的繁多差異并不影響精神屬性的歸納與同一,蘇姍·桑塔格就曾指出:“疾病是人性的陰面。” 1997年,《相約星期二》在北美地區掀起的閱讀風潮,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年逾七旬罹患重疾的社會學教授莫里,歷經蒼茫而身處價值迷惘期的得意門生米奇,因為疾病與死亡的推門而入,相約星期二,在最后的十四周里,他們談道德的確立,談生命的意義,敘人生的向度。這些舌頭上綻開的思考與語言,匯聚成書,成為師生間“最后的合作論文”。這部書在美國各大圖書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譯成三十一種文字,累計銷量一千一百萬冊,同名電影兩年后在美國上映。2007年,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的2011年,陸幼青《死亡日記》在天涯連載,其他重癥患者也相繼通過個人博客、論壇、電視直播等載體,傳達自我對生死的思考。這股疾病書寫的潮流也影響到散文場域,形成一個病患散文寫作的單獨序列。這其中,有兩位作者以其書寫的系列性,引起同仁之側目。一個是來自黑龍江的女性作者竇憲君,其《沒心草》一書完整記錄了自我與疾病、與死亡抗爭的全過程。這部散文集子也因其本真性與深入性,獲得了在場主義散文獎。另一個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李存剛,一位來自四川的骨科醫生。他的散文集《喊疼》以及業已完成的《住院部日記》系列、《一病區雜記》系列,皆以代入的方式深入疾病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層面。
《身體病》一文因為疾病的視角而遠遠超出普通親情敘事的范疇。或者可以這樣表述,這篇文章有著內外兩種視角。外在視角基于親情、親族的描述,表姐夫因為重疾而死于壯年,一個家庭的經濟收入主體倒下了,這對尚在求學的兒子,對于主內角色的表姐來說,是一種不可承受之重。在這個敘事框架內,作者兼容了非病患的因素,其中有表姐與表姐夫的結合,呈現了鄉土婚姻的基本邏輯,遵循于傳宗接代、地緣、門當戶對等基本原則;有表姐與表姐夫的土里刨食的苦干精神;有太陽山伐樹背后現實利益對鄉土人倫秩序的沖毀。這些因素或繁或簡,無疑充實了文本的容量,拓展了敘事的向度。而對這篇文章產生本質影響的則為內視角的確立,這個內視角基于疾病和身體,直接朝向眾多農民對待身體和疾病的基本觀念和行為習慣。表姐夫與其父親同樣因癌癥離開人世,他們對待身體的態度帶有某種文化遺傳性。一方面,基于窮困的現實與文化的貧乏使得他們難以顧及身體內部發生的變化;另一方面,潛意識中輕視身體的傾向,使得他們一向以“強硬”的姿態對待身體與病痛,不撞南墻頭不回。在他們的思維深處,覺得只要能吃下飯,就會有力氣,有力氣則百病不侵。于是,很多時候,小病積累以至大病,一旦大病到來,便宿命般的轟然倒下。
拋開病理的層面,《身體病》如同社會學的樣本,所展現的,恰是中國式農民與疾病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凸起部在醫院,慘烈度集中于病床,而在日常生活的隱微之中,這場戰爭業已全面展開,并浩浩蕩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