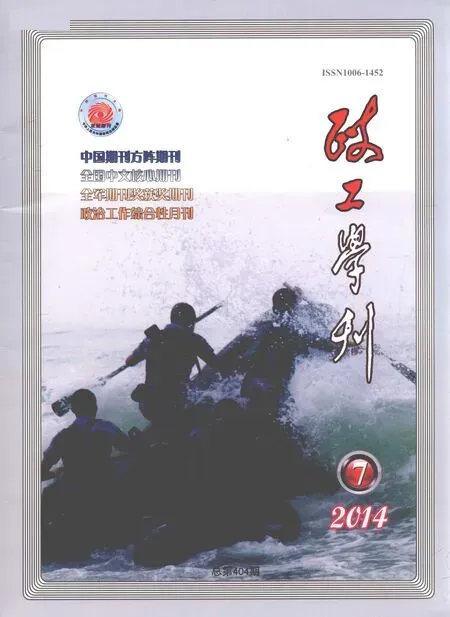緊貼使命任務(wù)特點(diǎn) 推動(dòng)動(dòng)中抓建落實(shí)
●92216部隊(duì)黨委
緊貼使命任務(wù)特點(diǎn) 推動(dòng)動(dòng)中抓建落實(shí)
●92216部隊(duì)黨委
近年來(lái),我部黨委堅(jiān)決貫徹“堅(jiān)定科學(xué)理念把方向、扎實(shí)有力抓手破難題、用好長(zhǎng)效機(jī)制提質(zhì)效”的思路,打造機(jī)動(dòng)先鋒隊(duì),確保各項(xiàng)任務(wù)圓滿完成。連續(xù)五年被師以上評(píng)為訓(xùn)練先進(jìn)單位、基層建設(shè)先進(jìn)單位,近百人次獲師以上表彰、榮立三等功。
一、強(qiáng)化三種理念,牢牢把握動(dòng)中抓建的正確方向
針對(duì)機(jī)動(dòng)條件下任務(wù)艱苦、情況多變、節(jié)奏緊湊等特點(diǎn),我們牢固樹(shù)立三種理念,確保部隊(duì)建設(shè)不迷航、不偏向。組織凝聚是最好的保證。每次執(zhí)行重大任務(wù),都召開(kāi)動(dòng)員會(huì)、部署會(huì)、誓師會(huì),明確任務(wù)性質(zhì)、要求及注意事項(xiàng);成立臨時(shí)黨組織,指定負(fù)責(zé)人,科學(xué)搭配干部骨干,做到既有領(lǐng)導(dǎo)帶頭又有骨干支撐,確保部隊(duì)走到哪里指示要求就傳達(dá)落實(shí)到哪里,加強(qiáng)任務(wù)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按綱抓建是最好的標(biāo)準(zhǔn)。落實(shí)《綱要》“過(guò)日子”,定期開(kāi)展“條令學(xué)習(xí)月”等活動(dòng),不斷強(qiáng)化官兵的條令法規(guī)意識(shí)。嚴(yán)格落實(shí)一日生活制度,建立專門(mén)的“四個(gè)秩序”檢查登記本,搞好經(jīng)常性講評(píng),做到苗頭問(wèn)題及時(shí)糾、共性現(xiàn)象集體改、個(gè)別情況專門(mén)點(diǎn),確保營(yíng)區(qū)內(nèi)外同標(biāo)準(zhǔn)、動(dòng)態(tài)常態(tài)一個(gè)樣。任務(wù)摔打是最好的平臺(tái)。利用執(zhí)行聯(lián)合演練、專項(xiàng)任務(wù)等契機(jī),采取壓擔(dān)子、結(jié)對(duì)子、老帶新等方式,在實(shí)戰(zhàn)化演訓(xùn)中培養(yǎng)鍛造人才。帶著研究課題、攻關(guān)項(xiàng)目執(zhí)行任務(wù),大力開(kāi)展戰(zhàn)斗力標(biāo)準(zhǔn)大討論活動(dòng),近年來(lái)梳理形成了多個(gè)研究課題及配套保障方案預(yù)案。
二、扎實(shí)三個(gè)抓手,著力破解動(dòng)中抓建的瓶頸障礙
我部執(zhí)行機(jī)動(dòng)任務(wù)頻繁,人員難集中、計(jì)劃難執(zhí)行、管理難正規(guī)等“三難”問(wèn)題突出,我們始終堅(jiān)持從搞好教育、謀好統(tǒng)籌、落實(shí)制度入手破瓶頸解難題。一是抓教育強(qiáng)化凝聚力。著力突破傳統(tǒng)施教模式,在人散心不散上下功夫。專題教育融入特色,綜合海軍軍種屬性、肩負(fù)使命特點(diǎn)、工作機(jī)動(dòng)方式,把海鷹作為標(biāo)志,提煉踐行“忠精勇銳、誠(chéng)樸敏慧”海鷹精神。重大教育落實(shí)措施,出臺(tái)“動(dòng)中抓教”3類26條措施,建立個(gè)人動(dòng)態(tài)檔案。經(jīng)常性教育統(tǒng)籌把握,時(shí)間隨機(jī)安排,內(nèi)容原則把握,形式靈活創(chuàng)新,叫響“千里機(jī)動(dòng)當(dāng)先鋒、海鷹出擊爭(zhēng)第一”的戰(zhàn)斗口號(hào),確保人員散得開(kāi)更收得攏、隊(duì)伍管得住更能攥成拳。二是抓統(tǒng)籌強(qiáng)化執(zhí)行力。抓好教育物資配套。配發(fā)野戰(zhàn)圖書(shū)箱、文體活動(dòng)器材,定期寄發(fā)《學(xué)習(xí)資料匯編》《教育快報(bào)》等輔導(dǎo)資料,確保動(dòng)中教育跟上部隊(duì)步驟、達(dá)到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分主次突出工作重點(diǎn)。重大工作相對(duì)集中時(shí)間、集中人員落實(shí);一般工作按計(jì)劃按程序展開(kāi)。分場(chǎng)合統(tǒng)分結(jié)合。大項(xiàng)工作動(dòng)員部署、情況講評(píng)相對(duì)集中,階段任務(wù)分頭實(shí)施,局部工作相對(duì)分散落實(shí),確保環(huán)節(jié)不落下、內(nèi)容不缺失。三是抓制度強(qiáng)化管控力。狠抓規(guī)章制度落實(shí),確保裝備出效益、官兵能打仗。因地制宜落實(shí)思想?yún)R報(bào)、個(gè)別談心等工作制度,廣泛開(kāi)展思想互幫、學(xué)習(xí)互教、工作互助、生活互愛(ài)“四互”結(jié)對(duì)活動(dòng)。貫徹“嚴(yán)管實(shí)備、精裝礪劍”思想,開(kāi)展“愛(ài)裝管裝月”活動(dòng),圍繞裝備管理“三化”要求,細(xì)化形成3類10余項(xiàng)細(xì)則。大抓野外駐訓(xùn)執(zhí)行任務(wù)安全管理,嚴(yán)格劃定活動(dòng)區(qū)域,設(shè)立警示標(biāo)志,做到隨時(shí)聽(tīng)招呼、守規(guī)矩。
三、健全三種機(jī)制,全面提升動(dòng)中抓建的質(zhì)量效益
機(jī)制管長(zhǎng)遠(yuǎn)、管根本,實(shí)踐中我們健全考評(píng)、協(xié)作、激勵(lì)三種機(jī)制,提升動(dòng)中抓建質(zhì)效。一是健全考評(píng)機(jī)制立標(biāo)準(zhǔn)。細(xì)化創(chuàng)先爭(zhēng)優(yōu)“五個(gè)好”“五個(gè)帶頭”標(biāo)準(zhǔn),分類厘清官兵職責(zé)、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開(kāi)展“樹(shù)一個(gè)目標(biāo)、訂一套措施、提一句口號(hào)、獻(xiàn)一條建議”公開(kāi)承諾活動(dòng),制定黨委、支部及個(gè)人《雙爭(zhēng)暨創(chuàng)爭(zhēng)檔案》,為表彰獎(jiǎng)勵(lì)提供基本依據(jù)。開(kāi)展“任務(wù)完成好、作風(fēng)紀(jì)律好、各方評(píng)價(jià)好”的“三好”評(píng)比活動(dòng),評(píng)比結(jié)果列入年底優(yōu)等工作、優(yōu)質(zhì)電文、優(yōu)秀個(gè)人“三優(yōu)”評(píng)比。二是健全協(xié)作機(jī)制促提高。縱向上,對(duì)上加強(qiáng)對(duì)機(jī)關(guān)請(qǐng)示匯報(bào),強(qiáng)化對(duì)大項(xiàng)任務(wù)工作方案的理解消化;對(duì)下加強(qiáng)與在外人員溝通協(xié)調(diào),做到上下貫通一致。橫向上,虛心取長(zhǎng)補(bǔ)短,年均派出30余人次參加聯(lián)合演練、代職輪崗、駐訓(xùn)幫帶,扎實(shí)學(xué)習(xí)兄弟單位好經(jīng)驗(yàn)、好作風(fēng)、好傳統(tǒng)。內(nèi)部上,實(shí)施機(jī)關(guān)基層換崗鍛煉,豐富任職經(jīng)歷,目前近半數(shù)業(yè)務(wù)骨干有機(jī)關(guān)工作經(jīng)歷。三是健全激勵(lì)機(jī)制樹(shù)導(dǎo)向。在評(píng)功評(píng)獎(jiǎng)、晉職調(diào)級(jí)上堅(jiān)持公正公平公開(kāi)前提,堅(jiān)決做到“四個(gè)優(yōu)先”:業(yè)務(wù)干部?jī)?yōu)先于領(lǐng)導(dǎo)干部;外出執(zhí)行任務(wù)人員優(yōu)先于在營(yíng)人員;執(zhí)行急難險(xiǎn)重任務(wù)人員優(yōu)先于一般任務(wù)人員;外出任務(wù)時(shí)間長(zhǎng)人員優(yōu)先于短時(shí)間執(zhí)行任務(wù)人員。通過(guò)抓住“四個(gè)優(yōu)先”,強(qiáng)化了爭(zhēng)著上一線、搶著扛任務(wù)的導(dǎo)向意識(shí),近年93%受表彰官兵執(zhí)行過(guò)機(jī)動(dòng)任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