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熊十力:“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熊十力本名“繼智”,“十力”是佛家術語,專指如來佛祖的十種智力。熊十力覺得這名很好,就不客氣地據為己有,其“狂”可想而知。佛家戒嗔戒怒,但信佛的熊十力一貫奉行“嬉笑怒罵”的處世原則,連權勢滔天的蔣介石都敢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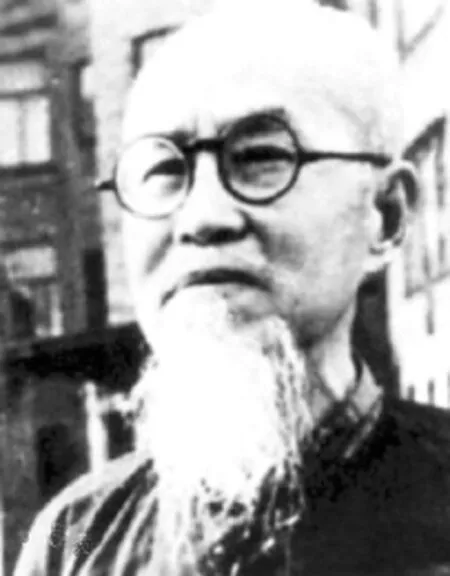
晚年的熊十力
敢在壽宴上痛罵蔣介石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黃岡,1917到1918年間,曾參與孫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慨嘆“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
1919年前后,熊十力來到天津南開中學教國文,不久因筆墨官司結識梁漱溟,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因緣。兩人相談甚洽,梁勸熊研讀佛學。1920年暑期開學后,熊再也沒有回南開繼續當老師,而是直接去了南京支那內學院,拜在歐陽竟無大師門下學佛。
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請歐陽門下弟子來北大頂替自己講授佛教唯識學。借此機緣,熊十力得以受聘為北京大學特約講師。
1926年,住在北京大有莊寫《唯識學概論》的熊十力因長期的困頓與凝思,積勞成疾,神經衰弱、胃下垂等多癥并發。1927年初,在蔡元培關照下,他南下杭州養疴。6年后,熊十力重返北大。1937年,日寇侵入華北,熊十力裝扮成商人,坐煤車逃離京城。
1941年,熊十力來到重慶梁漱溟所創的勉仁書院。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書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漢口王孟蓀家中。此時蔣介石正欲乘船還都南京,途經武漢,得知熊十力在漢口,便差人去請,想當面談談,看老夫子能為黨國幫些什么忙。熊十力一聽頓時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東西!”蔣素聞熊十力脾氣,也不生氣,讓陶希圣打電話給湖北省主席萬耀煌,囑其贈資百萬給熊十力,以助其辦哲學研究所。但熊并不領情,說:“我熊某對抗戰無寸功,愧不敢當。”
這年六月,熊門弟子,同時也是黨國要員的徐復觀將老師剛出版的《讀經示要》送了一部給蔣介石,蔣遂令何應欽撥款200萬給熊十力。熊依然堅辭不受,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趨老邁,身體很差,“此等衰象,確甚險也”,不適宜再出來開辦研究所。并給弟子徐復觀回信,訓了一通:“復觀以師事我,愛敬之意如此其厚,豈愿吾早無耶。”
蔣介石過50歲生日,邵力子又出面請熊十力為老蔣祝壽。熊十力駕到后,大咧咧地坐上正席,胡吃海喝。喝得高興,眾高官顯貴輪流吟詩作對,為老蔣唱贊歌。輪到熊十力時,他拿起筆來瞅兩眼老蔣的光頭,邊寫邊嘰歪:“脖上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篾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凈肉,頭。”蔣介石怒火攻心,氣得差點休克過去。
敢如此和蔣介石過不去,熊十力實在“牛氣”。不過,他的“牛氣”似乎與生俱來。坊間傳言,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小小年紀就曾口出“狂言”說,“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成年后哪怕是在校園為人師,他也不改火爆脾氣。比如在北大教書時,他常與小說家廢名探討佛經理論,兩人經常爭得唾沫星子亂飛。有一次,兩個老小孩甚至扭成一團,互相掐住脖子。不過打歸打,第二天兩人依舊談笑風生。
農村的自然環境,無論是山地,還是平原,相比較而言,都有著得天獨厚的空間優勢,動植物還是相對豐富的,這樣豐富的自然資源,必然會成為幼兒好奇的對象,因此也會成為幼兒率先觀察的目標。那么,在幼兒教育中,幼師便可面向自然資源,注重培養幼兒的觀察能力。
因去臺問題與得意門生翻臉
其實,熊十力欲辦哲學研究所的意愿由來已久。早在1931年,熊就曾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未果;1942年,老友們曾建議他到官辦大學里去開辦哲學研究所,他未接受,怕一入官府便不自由;抗戰期間,居正、陶希圣曾為他辦研究所事專門搞過一次募捐,也未成功。上文提及的官府撥專款來,他卻不為所動。此時,南開中學時的老同事孫穎川邀請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設在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哲學研究部,熊竟欣然前往了。
為了給弟子有個交代,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復觀,講明:當局若真想為國家培育元氣,最好讓自己自安其素,為所欲為,不必專款資助,只要不橫加干涉,便是一種支持。國家若真想辦此類研究機構,自可去辦中央研究院之類的,但這已與我熊某無關。他并舉章太炎之例,說“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資講學,而士林唾棄”。在他看來,若思想失自主,精神不獨立,學術無個性,便會導致游學無根,徒慕虛名。
入川不久,黃海化學工業社創辦的哲學研究部經費不足,再加上抗戰勝利后,川中已無“大后方”時期的人物聚集,使熊十力覺得在此難有大作為。1947年春北大復校后,熊聞訊便重返北大。他原以為可以重拾當年初到北大時那種平靜的治學生涯,然而內戰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其昀和哲學系主任謝幼偉出面相邀,請熊十力前去講學。但浙大校長竺可楨覺得他已老邁,不會有多大作為,倒不如請個年輕的來,因此熊郁郁不得志。
1949年春,國共戰局日漸清晰,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的廣州城,紛紛攘攘云集了各路觀望的人士,或走或留,這里都是一個不錯的臨時立腳之地。正在廣州近郊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他對國民黨早已失去信心,但對共產黨也同樣心存疑慮。
最后,熊十力認為,自己只是一介讀書之人,且已是“老朽”,無黨無派,不問世事,不論朝政,能奈我何?拿定了這個主意,熊十力決定留下來。這年春間,受聘于華僑大學的弟子唐君毅和錢穆曾前來探望,談及去留之事,錢穆回憶說“十力亦無意離大陸”。
不僅自己不離開,熊十力還寫信勸弟子們留下來。1949年4月10日,他寫信給徐復觀,力阻其不要攜眷去臺灣,他告訴徐,國民黨是守不住臺灣的。但作為國軍少將,徐復觀怎可能留下來?9月10日,熊又致信徐復觀,信中甚至問徐復觀,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去教書?此時南京已經陷落,在此當口,熊十力竟還惦記著中央大學的教席。徐復觀對老夫子沒有再客氣,他狠狠幽了師傅一默,讓他“直接去問毛澤東先生中大可去否”。熊看了來信非常惱火,再也不將徐復觀視為學生。
徐復觀走了,得意門生唐君毅和牟宗三也沒有聽從老師的勸告,一個到了香港,一個去了臺灣。
董必武郭沫若聯名邀其北上
此時,對于熊十力而言似乎只剩下入川一條退路。但還未及入川,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聯名發來的電報,邀他北上,共商國是。熊十力在回函中說,“如不以官府名義相加,而聽吾回北大,課本、鐘點、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時北還,一切照舊例,否則不欲北行”。
1950年1月28日,廣東省主席葉劍英為熊十力買好車票,安排好路上扶持之人,并親往車站送行。
車至武漢后,熊十力打算下車略住幾日,一是休息,二是略敘鄉情。林彪、李先念為其安排好住處,并設宴款待。3月7日,熊在武漢收到郭沫若來函:“已電李主席備車票并電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為北房無怪。至它一切,均請不必過慮。”
關于熊之北行,另據臺灣學者林繼平《我的治學心路歷程》中記述,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熊曾秘密乘火車來到廣州,準備轉去香港或臺灣,毛澤東得知消息后,立即電告四野林彪司令員在廣州攔截。林彪與熊十力是湖北黃岡的同鄉,林尊稱他為熊老師。熊十力無可奈何,只得跟隨回到武漢。無論版本有何出入,總之,在1950年的陽春三月,熊十力最后還是回到了北京。
甫一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便專程到車站迎接。如此規格,讓老書生甚感興奮。上世紀50年代初,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并未受到多少干擾。彼時大家都在一種激情的感召下,建設新社會。熊十力卻不為所動,他依舊老習慣,獨居,寫作,在家授徒。他的居處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也常來探望。
然而,此時熊十力的內心是孤獨的。他的學說逐漸被邊緣化了,著作也幾乎到了被人遺忘的地步。中國哲學會請他當委員,他提出兩個條件:不開會,不改造思想。他對自己的學生說:“我是不能去開會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1954年以后,政治空氣愈加左傾,老朋友們或被打倒,或被邊緣化,逐漸在學界失聲。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終于1954年移居上海兒子家。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傷感至極。之后,他也被卷入到了這場大潮之中。兩年后的1968年5月23日,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同舟共進》201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