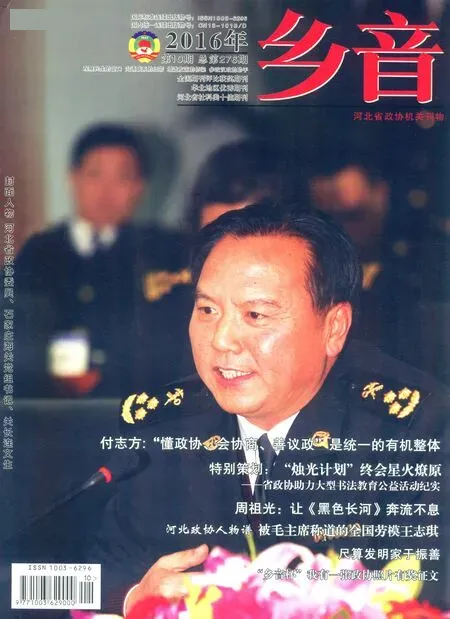周祖光:讓《黑色長河》奔流不息
文/聶穎
周祖光:讓《黑色長河》奔流不息
文/聶穎
【人物名片】周祖光,男,1961年生于河北唐山。先后就讀于河北師范大學美術系和中央美術學院賈又福山水研究室,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壁畫協會會員,河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唐山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唐山市委副主委,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美術院河北分院副院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美術院唐山市分院院長。河北省第十一屆政協委員,唐山市開平區政協副主席。
畫家周祖光的工作室內,幾乎什么都是巨型的:巨型畫案,整面墻的巨型畫板,還有一個整面墻的巨型書架。他應邀為人民大會堂創作的巨制《大岳雄風》,就出自這里。在書架最顯眼處,周祖光卻擺放了一張不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周祖光戴安全帽穿工作服,衣襟敞開,蹲在煤壁前與礦工們勾肩搭背,像多年的老工友相聚在一起,大家的臉上洋溢著快樂笑容。“這張照片,是我準備國畫《黑色長河》的素材時,在林西礦業公司拍攝的。我非常喜歡,還把它作為我畫集的封底。”周祖光說他是從開灤煤礦出來的畫家,“我的根在開灤。”
熾熱深沉的礦工情結
周祖光16歲下鄉,18歲被分配到開灤荊各莊礦上班,談起煤礦和礦工,他的感情就溢于言表,似有說不完的話:“我剛上班時,在采煤一線,攉煤打柱什么都干,每天受煤礦文化熏陶。”他上學是從開灤考出去,學成又回到了開灤教書。在礦上的十余年間,曾創作過十幾件表現煤礦的作品,在各級展覽中獲獎,也為開灤爭得過榮譽。“我對開灤有很深的感情。實際上,開灤的人文環境培育了我。”
周祖光是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煤礦的。可工作不管如何變化,地位無論怎樣改變,一直到現在,周祖光依然每年堅持到開灤的煤礦體驗生活,收集創作素材,“留下的影像資料越來越厚,礦工情結越來越深。”
開灤是一座跨越了三個世紀的百年老礦,文化歷史底蘊深厚,礦工形象雖然每年都在變化,但古樸勤勞的工作狀態卻是永久的。他非常喜歡這樣的礦工形象,“礦工們上井后,臉上有黑黑的煤渣,汗從臉上流下,那是一種勞動的美,能真實地反映出礦工的工作狀態。各種各樣的環境與人物,使我難忘,我希望我能用手中的筆,留住礦工的經典生活記憶,藝術地表現礦工的風采。”
周祖光說,隨著時間流逝,即使離開煤礦多年,但他的“礦工情結”卻愈加濃厚。“藝術品市場上對煤礦題材的畫認可度不高,大家都喜歡收藏花鳥和山水。但我不想那些,我一直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除了畫好山水、人物外,還把描繪礦工作為自己的一個重要創作主題,礦工是我人物畫創作的重點。”
每到外地參加公務或是學術活動,周祖光都極力向國內知名藝術家或各界宣傳煤礦和礦工。有一次,周祖光去中國國家畫院交流,與該院副院長張江舟、中國畫院(隸屬于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梁占巖探討他創作的幾幅新作品。其中就有他以礦工為題材的《黑色長河》,張江舟看后給予了高度評價:“能用水墨直面礦工形象的藝術家,在中國確實不多,祖光你做了件頗有成果的事。”梁占巖看完周祖光的畫后,倍受感染,激動地說:“我真想和你一起下井采風,我也要創作礦工題材的作品!”
在第十一屆全國美展現場,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也作過類似的評價:“用中國傳統水墨來描繪大型現代工業題材,是一種很有新意的嘗試。你的這幅作品是非常成功的,對各個博物館的收藏和重大歷史題材的表現都十分有意義。”
談到畫煤礦工人的技法,周祖光說:“我融合了花鳥和山水的技法來表現礦工,得到了業界認可與觀眾理解。”

一塊被扔進水里的干海綿
1998至2000年,周祖光在中央美術學院賈又福山水畫研究室研修近兩年。這兩年,成為他繪畫事業的轉折點。
在賈又福山水畫研究室上的第一堂課,讓周祖光明白了專業的分量:“賈先生要求我們,摒棄自己以前所有的繪畫習氣,必須扎扎實實進行傳統基本功訓練,那就是拜在古人腳下,一步一個腳印地臨習。”學畫期間,他對教授賈又福的印象深刻,“老先生將名利看得很平淡,只是告訴我們沉下心來,排除浮躁情緒,努力沿著傳統之路,宏觀探道,微觀求真,使我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中央美院,真正讓周祖光感到激動的,是每天下午的時光。那時他選修了許多課程:人物、山水、花鳥、書法篆刻,乃至雕塑……“在大學里面,研究生的選修課程是很自由的,每周教授正式上課的就幾節,我們有大量的時間練習繪畫基本功。當同學們課下休息時,我都不想浪費時間,而是奔走在各個選修課教室。那時候,我每聽到一位授課老師的名字,都如雷貫耳:侯一民、盧沉、姚有多、王鏞、田黎明、朱乃正、張立辰……我愈發感覺時間不夠用,就像轉動的陀螺一樣,有時一下午趕著上兩三種選修課。”
本是山水專業學生的周祖光,就像是一塊干海綿扔進了大海里,從方方面面汲取營養。在美院學習的兩年,他基本上沒回過宿舍睡覺。“和我同宿舍的研究生只在開學分宿舍時,見過我一面,后來,我便將行李直接拎進了畫室。”周祖光每天用兩塊畫板當床,放在地板上就睡。“一生難得有這么好的學習機會,能步入這么高的藝術殿堂,所以我格外珍惜。”
周祖光下課去食堂的必經之路,就是錢紹武的雕塑工作室。一次,他去打飯,走過工作室門口,發現錢紹武正給學生上課,他就拿著小飯盆站在旁邊聽講,入了迷。此后每到錢先生授課時間,他就跑去聽課。一天,他到樓下去買書,看中了書攤上僅剩一套的《八大山人全集》,老板告訴他那套書已經有人訂了。他好說歹說,讓老板將書賣給了他。沒過多久,錢先生來到書攤前,準備拿書時,聽說那套書被賈又福山水畫研究室的一個研究生搶先一步買走了,失望離去。后來在他們的一次聊天中,周祖光提到了最近買的一些好書。原來是你買走了?那套書是我訂好了要買的。”當即,錢紹武在他的工作室給周祖光寫了幅字:開卷有益。鼓勵周祖光多看書,落款寫的是“祖光老弟,積書甚富,乃有心人也”。
周祖光親身體會過生活的艱辛和痛苦,這次也品嘗了做學問的充實。似捅破了那層遮擋藝術創作視線的窗戶紙,打開了自己的思路和心胸。“我慢慢體會到了專業和業余之間的不同,也看懂了經典與平庸的區別。專業的人,總是在某一領域不斷地探索,追根溯源,不斷疊加,將傳統、知識積累、社會知識的修養與生活歷練綜合到一起,最終形成自己的東西。”

周祖光作品
凈化心靈的西藏之旅
“每去一次西藏,心靈都受到一次洗滌。”周祖光說,“來到西藏,你會不自覺地被那里的神秘氣息所感染,其場景令人震撼。”第一次去西藏,他只是跟著旅游團走馬觀花地游覽了一遍。第二次是跟著一位畫友和其他人搭伴去了熱門景點。第三次便和以往不一樣,幾個人直接租了三輛越野車,前往他們真心想去的原生態地區。
這一年,周祖光已經50歲,他與朋友們準備去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營。將到達那里時,周祖光被壯美場景所吸引,雪山、牧場、藏民、牛羊……他想多留一些這震撼的景觀,一路小跑著拍片,“我追著藏民們抓拍,一直跑動,無數次按下快門。”
當回到車上時,周祖光感覺呼吸越來越困難,緊接著意識模糊,昏了過去。向導見狀,馬上命車返回日喀則軍分區醫院。周祖光躺在醫院里,醫生們搶救了他整整一晚。
第二天,周祖光才醒過來。醫生對他說:“你都50歲的人了,還敢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跑動,膽子也太大了。倘若昨天檢查出你有腦水腫的話,我們就讓你寫遺囑了;如果你被查出的是肺水腫,那就得立馬雇用直升飛機把你送到西寧去。你這是撿了條命啊,趕緊回去吧。”一行人撤回到拉薩,但他卻戀戀不舍,不肯離去,繼續在大昭寺逗留了兩天,后在朋友極力規勸下,才回了內地。
從西藏回來,周祖光得了幽閉癥,不得不進行了脫敏治療,但他認為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他所畫的藏民,許多素材都來自這次驚險的第三次西藏之旅,名為《雪域祥云》的巨幅長卷系列作品,就是其重要收獲。此事過后,他體會到生命的本質意義,“與其說是一次生死考驗,不如說是一個藝術虔誠者的心靈洗禮。”
周祖光說,去西藏感受那份原始自然的狀態,純凈內心的靈魂,與在煤礦和礦工接觸,異曲同工。所以,他心里總想,該好好地創作一幅有關礦工的畫作了。“我去過西藏,藏民們對信仰的朝拜與礦工們對光明的朝拜殊途同歸,都是從生命本體和人文關懷出發。”
于是,周祖光開始醞釀創作《黑色長河》。“我這幾十年,已經積累了許多礦工的速寫稿,收集了許多資料,對井下搶險、運輸、攉煤等場景歷歷在目。我非常熟悉礦燈、電鉆等工具,拿起來就能畫。真正畫起來的時候也沒起草圖,就是一個場景接著一個場景地畫著,最后合在一起,都能連起來,頗有氣勢。”他共完成了8幅作品,分別表現了搶險、交班等各種工作場景。
其中《交班》這幅作品背后還有個小故事。周祖光在雜志上偶然看到了中國首屆線描藝術展征稿的消息,當時他也不清楚到底怎么用線才算是“線描藝術”,就試著把《交班》的線描稿交了上去,沒想到作品在評選中獲得了最高票數,還被刊登在了《美術》雜志上。“我用生宣,且墨線勾線也不是純傳統的線,而是濃淡干濕,變化豐富,盡顯書寫之態。那次展覽,許多人的作品勾線非常古板,這就顯出我的作品富有新意。”周祖光說,評委們針對作品投票的時候,認為他的線既不是純古人的線,也不是現代人所慣用的線,而是一種經過自己體悟得來的線,最后他的作品獲得了最高獎。而后,接踵而至的第十一屆全國美展,他將集中創作的8張巨幅系列作品《黑色長河》全部送去參展,并成功入選,標志著他的創作達到了高峰。
煤礦、礦工、高原、藏民,是一條貫穿人性光輝的創作母題。周祖光表示,自己將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深情繪畫礦工在各種場合喜怒哀樂的生活狀態,《黑色長河》將會繼續“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