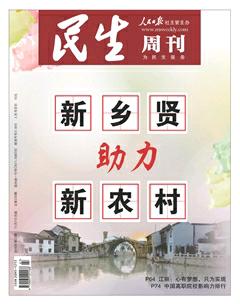鄉(xiāng)賢傳統(tǒng)再展時(shí)代魅力
趙慧
鄉(xiāng)賢?,作為中國古代社會(huì)特有的人文傳統(tǒng),長期填補(bǔ)著鄉(xiāng)村公共治理空間的空白,承擔(dān)著治理鄉(xiāng)村、教化鄉(xiāng)民、傳承耕讀文明的重任。
古代士紳鄉(xiāng)賢中的許多精英,年少時(shí)“學(xué)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年老后落葉歸根,告老還鄉(xiāng),最終完成了“生于斯、長于斯、回報(bào)于斯”的人才良性循環(huán)。
往事越千年,今天,古老的鄉(xiāng)賢文化,在新的歷史平臺(tái)上,再次展現(xiàn)其恒久魅力。許多成功人士,在濃濃鄉(xiāng)情的凝聚下,辭城回鄉(xiāng),或身居城市心系故土,為建設(shè)美麗鄉(xiāng)村,擔(dān)起責(zé)任。
古代:年老必還鄉(xiāng)
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費(fèi)孝通在他所著的《鄉(xiāng)土中國》開篇即談道,“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huì)是鄉(xiāng)土性的。”在鄉(xiāng)土中國,人民歷來安土重遷,除戰(zhàn)爭(zhēng)、災(zāi)荒、分裂、動(dòng)亂等時(shí)局外,鮮有大規(guī)模流寓遷移,鄉(xiāng)民大多終老本籍,離家仕宦亦多選擇告老還鄉(xiāng)。
先秦時(shí)已有官員退職還鄉(xiāng)的記載,《尚書》記載,“伊尹既復(fù)政厥辭,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歸即告老還鄉(xiāng),這也是史書有關(guān)告老的最早記錄。宋朝以前,官員致仕(退休)后一般都返回原籍,但只有宋朝官員“終身不歸其鄉(xiāng)”,致仕后寄養(yǎng)在朝廷專設(shè)的宮觀。
明朝建立,天下重歸一統(tǒng),唐宋以來的流寓之風(fēng)漸漸平息,加之政府明令官員致仕必須還鄉(xiāng)、流民歸籍不得隨意遷徙,鄉(xiāng)村重又繁榮,鄉(xiāng)土觀念再次為人信仰。及至明朝中葉,伴隨學(xué)校制和科舉制的發(fā)展,鄉(xiāng)紳作為一個(gè)階層登上歷史舞臺(tái)。
鄉(xiāng)紳的構(gòu)成除大量未入仕而有功名的舉人、貢生、監(jiān)生外,還加入了大量致仕、卸任還鄉(xiāng)的官員,而這與明朝嚴(yán)格的官員致仕制度密切相關(guān)。
明清兩代,政府皆明文規(guī)定官員最高年至七十必須聽令致仕,致仕后一律給驛還鄉(xiāng),不得留住京師或任職地。同時(shí),由于官員不得在原籍任官,且不得在任職地購置田產(chǎn),返回原籍幾乎成為官員的唯一選擇。
為了鼓勵(lì)官員還鄉(xiāng),政府不僅允許使用官車送回,沿途接待,而且依據(jù)官職、貢獻(xiàn)給予不同俸祿。文官告老還鄉(xiāng),武官解甲歸田,政府明令之下官員大量返鄉(xiāng),并補(bǔ)充進(jìn)鄉(xiāng)紳隊(duì)伍,鄉(xiāng)村亦因大批有文化、有實(shí)力、有資源的鄉(xiāng)紳乃至鄉(xiāng)賢的存在而充滿活力,成為絲毫不遜色于皇城大邑的所在。
“紳為一邑之望”
在封建時(shí)代,國家政權(quán)對(duì)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統(tǒng)治極為薄弱,盡管設(shè)有里甲、保甲等組織,但其作用僅限于編戶齊民、征收賦役,且后來日漸寥落,大多流于形式。
在《鄉(xiāng)土中國》一書中,費(fèi)孝通記述,“在鄉(xiāng)村里所謂調(diào)解,其實(shí)是一種教育過程。我曾在鄉(xiāng)下參加過這類調(diào)解的集會(huì)。我之被邀,在鄉(xiāng)民看來是極自然的,因?yàn)槲沂窃趯W(xué)校里教書的,讀書知禮,是權(quán)威。其他負(fù)有調(diào)解責(zé)任的是一鄉(xiāng)的長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長從不發(fā)言,因?yàn)樗卩l(xiāng)里并沒有社會(huì)地位,他只是個(gè)干事。”
一位縣知事亦曾感慨:“官與民疏,士與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
相比政府任命的官吏,“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無論是致仕官員還是舉人生員,都擁有庶民百姓所不具備的聲望、資財(cái)乃至特權(quán),自然成為鄉(xiāng)村執(zhí)行教化、禮儀、訴訟等公共事務(wù)的主持者,水利、賑濟(jì)等公益事業(yè)的組織者,甚至成為鄉(xiāng)民的代言人和保護(hù)傘。其中樂善好施、和睦鄉(xiāng)黨、謙虛好禮者更被推為鄉(xiāng)賢,為鄉(xiāng)民所擁戴,其言行成為一方之表率。
陜西大荔縣保存著一座古代糧倉,名為“豐圖義倉”,至今仍在使用。據(jù)史料記載,這座義倉由大荔朝邑人,晚清官至戶部尚書、軍機(jī)大臣的閻敬銘倡議修建,被慈禧朱批為“天下第一倉”。1900年關(guān)中災(zāi)荒,豐圖義倉開賑放糧,救人無數(shù),閻敬銘因此被人尊為“救時(shí)宰相”。
史載閻敬銘為官嚴(yán)正無私,致仕還鄉(xiāng)后更是“尚孝友親睦”,熱心公益事業(yè),捐資修建義學(xué),成為一代鄉(xiāng)賢。
除興辦學(xué)校、教化鄉(xiāng)民等文化活動(dòng),以及公益性的賑濟(jì)救災(zāi)、扶危濟(jì)困外,鄉(xiāng)村公共工程建設(shè)的籌謀和規(guī)劃,幾乎全賴鄉(xiāng)紳、鄉(xiāng)賢得以完成。這些公共工程包括修橋筑路、開河筑堤、興修水利、建祠修廟等,而且,即便是在國家政權(quán)遭到威脅時(shí),政府角色日漸收縮,地方鄉(xiāng)紳賢達(dá)的重要性卻愈加凸顯,鄉(xiāng)村文明依舊生息不輟。
讓鄉(xiāng)賢回得去留得住
時(shí)移世易,如今的鄉(xiāng)村生態(tài)已大異于從前,鄉(xiāng)村治理模式也幾經(jīng)變化。有學(xué)者認(rèn)為,鄉(xiāng)賢文化在今天鄉(xiāng)村基層治理中依然有其價(jià)值,但傳統(tǒng)鄉(xiāng)賢文化依賴士紳個(gè)人威望維護(hù)鄉(xiāng)村秩序穩(wěn)定與公正的做法,與現(xiàn)代社會(huì)以法律和契約作為秩序基礎(chǔ)的觀念相比已格格不入。
的確,培育傳統(tǒng)鄉(xiāng)賢文化的時(shí)空和土壤已發(fā)生變化,尤其是鄉(xiāng)賢文化所依托的鄉(xiāng)村現(xiàn)狀堪憂。近年每逢春節(jié),回鄉(xiāng)筆記便廣為流傳,其中透視出的鄉(xiāng)村凋敝、空心化、失根現(xiàn)象觸目驚心,而其直接原因就是鄉(xiāng)村精英人群的凈流失。
不過,亦應(yīng)看到,傳統(tǒng)鄉(xiāng)賢文化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diǎn),用鄉(xiāng)情、鄉(xiāng)風(fēng)、鄉(xiāng)約教化鄉(xiāng)民,協(xié)調(diào)解決沖突等做法仍值得今人借鑒。
如何讓那些從鄉(xiāng)村走出去的優(yōu)秀人才落葉歸根、反哺鄉(xiāng)村,當(dāng)然不能靠“官員致仕一律還鄉(xiāng)”的法令,不能簡單照搬舊時(shí)“鄉(xiāng)紳治村”的成例,而應(yīng)培育新鄉(xiāng)賢文化,在縮小城鄉(xiāng)差別、建設(shè)美麗鄉(xiāng)村、涵養(yǎng)文明鄉(xiāng)風(fēng)上下功夫,各地亦應(yīng)營造鄉(xiāng)賢回鄉(xiāng)的豐厚土壤,讓更多新時(shí)代的官員、企業(yè)家、知識(shí)分子等社會(huì)精英,愿意回去,回得去、留得住。
這是一道可以解也能夠解好的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