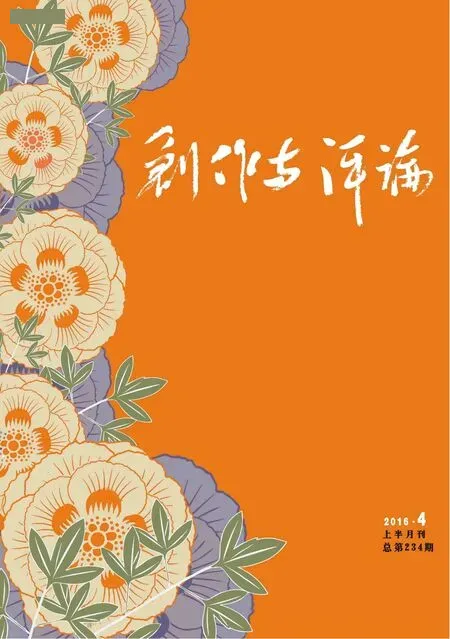小樓一夜聽春雨
——評潘小樓的小說
○李壯
?
小樓一夜聽春雨
——評潘小樓的小說
○李壯
作為一個從小在城市里長大的可憐家伙,我對中國農(nóng)歷節(jié)氣的意識僅僅停留在那一個個好聽的名字上面。甚至可以說,在我心中,這些最基本的“能指”所引起的聯(lián)想,也都不是農(nóng)作物的收播生死或自然天氣的轉(zhuǎn)變,而是現(xiàn)代生活符號世界中無數(shù)個漂浮的概念——“大雪”給我的第一反應(yīng)是永遠是三片小雪花并排放置的圖案,那是童年時候,新聞聯(lián)播過后天氣預(yù)報里的氣象等級符號。與之類似,都市里的童年有一種樂趣,叫做“開著冷氣鉆棉被”,那種酷暑之下溽熱焦躁又無處躲藏的經(jīng)驗,在我們的記憶里其實相當(dāng)稀少。這是現(xiàn)代生活的便利,也是現(xiàn)代生活的乏味;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我們生理方面的舒適度,卻也粗暴地刪削了心理體驗的波峰波谷——在過去的歲月中,任何無法逃避的生理挑戰(zhàn)都會導(dǎo)致心理層面的特殊反應(yīng),現(xiàn)在我們身體對外在世界的記憶卻已平滑得像一塊每日都刮的黃油,于是只好低頭對著游戲機尋找一點人工的刺激。
潘小樓的作品忽然使我想到這些,是因為她的小說中有一股強烈的節(jié)氣轉(zhuǎn)換的味道,并密布著隨之而來的“波峰波谷”。潘小樓的小說里有四季的變化,這種變化未必是在同一篇小說里完整地表現(xiàn)出來,更多時候是在不同文本的并置和對照中得到顯現(xiàn),并且在近似中又有微妙的不同:《端午》是濕溽、《小滿》是悶熱、《女孩們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里有一種微微眩暈的中暑感;《秘密渡口》的清涼透著寒意,《魁山》彌漫著隱隱的蕭瑟,《喀斯特天空下》則像文中的地下河流洞口一樣臨界于冷與熱兩個世界的邊際。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節(jié)氣的轉(zhuǎn)換在她筆下并非耽于外在,而是滲入了人物的性情。外部環(huán)境的微妙變化,感知于肉體,更作用于內(nèi)心;它不僅推動了氣溫計里汞柱的升降運動,更參與了小說人物的定性和塑形。以《小滿》為例,一個吉普賽女郎式四處遷居的母親似乎是富有詩意的,她可以是浪漫主義小說家筆下一位神秘卻純粹的人物,或者加西亞·洛爾卡詩歌里迎著棕黃色濃稠陽光起舞的迷人少婦,但她本身并不足以支撐起一篇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這篇小說的成立,其根本在于外部世界特殊氣息的內(nèi)在化:小滿之夜,因為年幼的“我”的一次疏忽,母親在身心雙重意義上遭受了屈辱,這推動了一次新的遷徙,并且導(dǎo)致了一個新的人物順利介入小說——小滿作為那個羞辱之夜的產(chǎn)物,就這樣生生地插進了母子二人的生活;她終將導(dǎo)致人物關(guān)系平衡的打破,小說敘事的引擎由此真正啟動。同時,隨著年齡的成長,“我”漸漸明白了那個小滿之夜意味著什么,充滿恥感的生活令“我”不快(小滿這一人物作為恥辱的符號偏又每日晃蕩在眼前),而這一切歸根到底卻是“我”自己的過錯,一種無處發(fā)泄的憤怒最終指向自身,主人公孤僻、冷漠、充滿不安全感的性格正是由此而來。那盞偷偷熄滅的燈,連同小滿時節(jié)彌漫于空氣中的特殊氣味一起,強有力地參與了“我”的性情塑成。這種性情是如何在歲月中變得堅硬、頑固,又是怎樣在命運的顛簸中出現(xiàn)了隱秘的裂紋,這才是小說真正的重點。與之類似的是《魁山》。神秘的巫醫(yī)行跡、鄉(xiāng)間的民風(fēng)民俗、山水間半屬野生半屬人工的日常器物(如那條冒水的石坑),看似是外在的風(fēng)情,實際上也已同九伯這一人物的內(nèi)質(zhì)外形生長在了一起。可以這樣說:西南邊陲大地那濕熱、滯重、騷動、帶有神秘之美的氣息,在潘小樓的筆下已充分地內(nèi)化于人物性情,并成功化生為一股股壓抑而又猛烈的生命力,在文本中汩汩流淌開來。
在此意義上,潘小樓的小說中具有一種古典與現(xiàn)代并在的奇特風(fēng)味。其古典之處在于對外部世界的書寫:偏遠卻熱鬧的西南小鎮(zhèn)、隨自然輪轉(zhuǎn)波動起伏的溫度感知、在現(xiàn)代世界侵入的大背景下尚未徹底消亡的民風(fēng)民俗等等。但當(dāng)所有外部世界元素進入文本和人物的內(nèi)部,出現(xiàn)的則又是一種充滿現(xiàn)代意味的變異:孤僻的性情、躁動的青春、遙不可及的安定感、渴望救贖的心。潘小樓筆下的人物是充滿疑問的,小說情節(jié)的進程基本可等同于人物的問題史。這個過程中浮現(xiàn)出的“問題”往往充滿現(xiàn)代意味。《端午》會讓我們聯(lián)想到白娘子的故事,在那個民間傳說里,催生變化的關(guān)鍵性道具是雄黃酒(它直接道破了“人妖殊途”的道理),到了潘小樓筆下,道具則變成了帶有窺視意味和欲望覺醒隱喻的小鏡子;在端午顯形的妖怪,也不是千年白蛇,而是內(nèi)在于主人公、長著一幅弗洛伊德式臉孔的怪獸(月娘本是父親的情人,而在后文中與主人公發(fā)生情感糾葛的,又是其同父異母的妹妹)。同樣具有現(xiàn)代意味的是作者對人物心理世界的解讀方式。她的透視深刻、犀利,卻又不失節(jié)制,如同油井上方的鉆孔,洞打得深卻依然只是洞,我們需要在那些狹長的黑暗之中,自行揣度地表下涌動的石油。潘小樓筆下的故事往往清晰,但情節(jié)的明澈并未導(dǎo)致文本意蘊的失控性噴發(fā);故事可以解謎,真相可以大白,但復(fù)雜之物不宜輕易拆解,成熟的書寫也理應(yīng)拒絕那些扁平泛濫的抒情。潘小樓在這一點上做得不錯,盡管有時她的故事講得有點繞、跳得有點猛,但那種糾纏的余味保留住了,并且由于找到了現(xiàn)代人格中那些頗具獨特性的幽暗角落,這些小說大多是有效的。
說到“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引述盧卡奇的一個觀點,他認為現(xiàn)代語境下的小說,其內(nèi)在形式便是“成問題的個人”的自我完成。潘小樓的小說基本都是有關(guān)于一個個“成問題的個人”。和盧卡奇的闡釋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潘小樓筆下的“問題”一般不會觸及主體價值的自我確證或世界的總體性想象,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內(nèi)心之中展開更集中的演繹;進而所謂的“自我完成”,也就變成了人物情緒乃至情結(jié)尋求自我安置的過程。這是潘小樓女性的一面、溫柔的一面、細膩的一面,它為小說注入了一種內(nèi)在的溫度感。潘小樓人物的“問題”,往往根源于青春時代的歷史遺留物,諸如《端午》里那場半是自覺半是傳染的朦朧情欲、《魁山》里那句陰魂不散的讖語、《秘密渡口》里王一美忽然從水面下浮現(xiàn)的橄欖色皮膚等等。潘小樓的小說在經(jīng)驗和細節(jié)方面有很強的彌散感,但又為讀者留出了一條荒草之下的隱秘山路,能讓我們溯游而上,找到故事最初的原點。當(dāng)這個原點被作者用一個畫面、一個動作甚至一句對白的方式凝固下來,小說就會在某個瞬間突然充滿了詩歌的韻味。潘小樓的小說充滿了這種詩歌的色調(diào),同時,它還跟關(guān)乎詩歌的另一個詞有關(guān),那就是青春。作為80后的青年作家,“青春”一詞似乎變得有些敏感,隨著“青春寫作”在多年前的商業(yè)出版大戲中被過度透支,甚至成為了浮夸、模式化和不成熟的代名詞,與青春有關(guān)的一切經(jīng)驗仿佛也都帶上了原罪,成為許多寫作者在文本中刻意要避免的東西。這并不是一種理性的反應(yīng),而那些太急著把青春與自己的寫作撇得一干二凈的作家,或許也會帶有一點不自信甚至反向浮夸的嫌疑。事實上,青春不是寫作的原罪,而是關(guān)乎經(jīng)驗的原罪;如果前者意味著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的某種禁忌或“諱”,對后者的挖掘卻正是小說的本意之一。一個作家的18歲很可能在暗中決定了其一生的寫作,我們也很難想象,一個人的靈魂構(gòu)成會跟青春期時遭遇的人和事毫無瓜葛。真正重要的是,優(yōu)秀的小說家不能僅僅把這“罪”放大到遮天蔽日,而要能寫出“罪”背后的“原”,寫出地平線盡頭那模糊的身影,揭示出青春記憶中某個微小而重要的時刻,是怎樣在人物未來的歲月中輻射出漫長的衰變期。潘小樓寫出了青春之罪的“原”,并在這一原點的基礎(chǔ)上放射出延展性十足的射線,因而縱使她的筆觸常與青春為伴,但總體的經(jīng)驗視野卻顯示出一種寬廣。
潘小樓的小說在更多時候?qū)儆谇啻簲⑹碌淖兎N。她的張力不是外在而是內(nèi)在的,并非確鑿無疑、張揚恣肆,而是在反復(fù)的延宕和猶疑之中刻畫出文中人物的內(nèi)心圖景。潘小樓小說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少年,某場特殊的經(jīng)歷導(dǎo)致其內(nèi)心的異變,此種異變彌漫著青春期的獨特氣息,比如叛逆、迷茫、孤獨、偏執(zhí)等等,都是經(jīng)驗史中曾被一再書寫又至今依然無法繞過的關(guān)鍵詞。這類人物的情感色調(diào)是相當(dāng)鮮明的,在行動層面上卻往往陷于混沌——他們能夠明確地感知到自己的內(nèi)心,卻無從獲知自己應(yīng)往何處去。《端午》一篇在這一點上頗為典型。在結(jié)局打開之時,當(dāng)主人公“我”面對著舒小白的尸身,潘小樓替他這樣總結(jié)道:“看著她一臉的純凈與無辜,我禁不住在心里打了個冷戰(zhàn)。純粹的人偏執(zhí)起來往往是最可怕的,她會像飛蛾一樣不顧一切地撲扇到她自己所堅信的光點里。”其實“我”也有純粹而偏執(zhí)的一面,不同之處在于,“我”尚沒有尋到自己那枚“堅信的光點”。盡管在小說開篇時主人公就預(yù)先坦白,“我的童年,在我七歲的夏天就徹底結(jié)束了”,但這種“結(jié)束”,正意味著更漫長的“開始”,而且是一場無限期的放逐。隨著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去,主人公也在孤獨甚至冷淡的模具里不可逆轉(zhuǎn)地凝固成形。舒小白的執(zhí)著與堅信,或許正是“我”的反襯;她以她的死暗示了另一條道路的不可行:即便那個有關(guān)身世的秘密能夠一直封存下去,在彼此不知情的情況下兩人走到了一起,舒小白的內(nèi)心真的就可以不受折磨嗎?唯有一死,才能夠徹底解開倫理的困局。飛蛾撲火的結(jié)局無一不是毀滅。攜帶著記憶中的傷痕漫無目的地游蕩下去,似乎是主人公唯一可做的選擇。唯一確定的東西只存在于過去,這也就是小說最后那場夢境存在的意義:在殘酷的謎底解開之后,現(xiàn)實中父親一閃而過的身影并不能構(gòu)成實質(zhì)性的撫慰,只有在縹緲的回憶中,化身亡靈的親人們再度將自己圍攏,漂泊的心靈才能獲賜瞬間的安息。
與之不同的是另一種形象:歷經(jīng)滄桑的成年人。與少年形象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相反的是,這類主體在行動層面上不成問題,都是因某種特殊的機緣或頓悟,決定重新回到心靈的原點去完成一次了結(jié)。但在方向確鑿的行動路線背后,卻是情感世界的空洞與猶疑。在被歲月與世間生活摻入了過多色調(diào)之后,他們的內(nèi)心呈現(xiàn)出混沌的灰色,這也是他們在行動層面義無反顧地進行回溯的原因——通過拆解舊日的心結(jié),他們試圖厘清自己。這類故事形成了一種“后青春”式的內(nèi)在形式,它不是向前尋找,而是要重溫舊日的謎題,并給出一個遲到的解答。這是救贖,是對青春時代留下的難題的破解,是在肆意揮灑與一團糟糕之后默默清理殘局的宿命。這種結(jié)構(gòu)成為了《女孩們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的敘事動力。不同的女孩一再回返到那個詭異失控的夏天,完成了一次“羅生門”式的講述,隨之裸呈的,是18歲燦爛陽光背后那些陰影密布甚至蜘蛛寄生的角落。《喀斯特天空下》里母親的骨灰,其具體的安置方式只不過是一個外在化的契機,主人公對自己人生的反觀梳理,才是這一趟回鄉(xiāng)之旅的重點所在。《秘密渡口》的主人公在一次次錯過情感的“安定版本”之后,終于在衰老的預(yù)感中再次回到年輕時踟躕過的河邊,在這里他沒有遇到多年前的情人,遇到的只是女子身后的未亡人。王一美的死,是兩位未曾謀面的男人的隱秘共謀,因此,兩人都在歲月中背負上了沉重的內(nèi)心壓力,終于趨使他們再一次走回這片水邊——小說中亦真亦幻的神秘“水猴”,正是兩人心結(jié)的具物化象征。很明顯,在這類小說中都存在一種強烈的“向回走”的模式,清晰的行動路線,意味著對混沌迷惑的內(nèi)心世界的重新梳理——這是小說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它對時空場景的分割重組最終呈現(xiàn)在具體的人物形象之上,遠要比文本中多次出現(xiàn)的“X年前”、“×個月前”這樣簡單粗暴的“華麗麗分割線”有效得多。關(guān)于這種結(jié)構(gòu),最為典型的是《青檸》。中學(xué)時代那場曖昧而怪異的感情經(jīng)歷,最終引導(dǎo)著主人公再次回到工廠廢棄的宿舍房中,并在這里將自己封存已久的處子之身奉獻給了一個相識不久的男人。這篇小說在我看來是微有瑕疵的,問題就出在一頭一尾的當(dāng)下時間里,主人公所作所為的儀式氣味過于濃重,反而干擾了主體部分里對情竇初開的工廠子弟女孩內(nèi)心波瀾的精彩刻畫。然而,單就人物形象模式和小說推進的動力機制而言,《青檸》無疑極富代表性。
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人的生命是從一個他已經(jīng)忘記的經(jīng)驗開始,并以一個他必須參與卻不能了解的經(jīng)驗結(jié)束。這就是小說家在書中所能呈現(xiàn)出的人物。”這句話既關(guān)乎現(xiàn)實意義上生理的人的生死問題,也關(guān)乎虛構(gòu)文本中作為角色的人的生死問題,或者說,它隱喻著小說經(jīng)驗和敘事的生死起止問題。一個已經(jīng)忘記的經(jīng)驗,是如何被重新憶起,并以問題的形式開啟了小說的敘述?對于那最后的經(jīng)驗(不論是人物生理意義上的死亡,還是小說敘事的終止),人物又是以怎樣的方式不可回避地參與其中,卻最終沒有留下明確的答案?這涉及到小說寫作者介入文本的方式姿態(tài),也就是一段情節(jié)怎樣截取、一個故事如何講述的問題。就講故事的風(fēng)格而言,潘小樓似乎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細密、舒展是她的特點,盡管喜歡用戲劇性較強的轉(zhuǎn)折來推動故事前行,但潘小樓并沒有在這一過程中變得緊張僵硬。我喜歡她筆下那些深入心神的撫摸、生活縫隙間的窺視、甚至偶爾旁逸斜出的枝節(jié),也喜歡看她優(yōu)雅地保有幾分節(jié)制,時不時放松一下人物間緊繃的弓弦,讓文字在幾顆不安的心臟間輕輕柔柔地游走。也許跟導(dǎo)演系出身的背景有關(guān),潘小樓的小說里有一種搖臂鏡頭的感覺。我們常用一個詞叫“鏡頭語言”,拍攝者隔著鏡頭,借助畫面的剪切和視角的轉(zhuǎn)換,把一個貼在地上的故事拍得立體起來、生動起來,并且賦予它講述者自己的溫度。現(xiàn)在潘小樓的手中沒有鏡頭了,她能依憑的只有抽象的文字,那么調(diào)度畫面和色彩的視覺功夫,也就平級轉(zhuǎn)換成了聽覺功夫——聽故事和講故事(而非看和拍)的藝術(shù)。潘小樓的聽,是古典式的聽。她不會借助現(xiàn)代技術(shù),讓薄薄的竊聽器把地攤上掉針的微小細響都記錄在案;她的傾聽隔著一層泛黃的窗紙,屏蔽掉那些過分細碎或過度尖銳的響聲,重點捕捉那些日日尋常卻與心靈有關(guān)的部分,例如悄然出走的關(guān)門音響,或是空空的老屋里多年前腳步的回聲。隔窗聽來的故事,經(jīng)由這女子的深情轉(zhuǎn)述,便有了一重溫婉的意思,且不論故事本身是否殘酷,落在心里,總歸覺得舒適。陸游的名句藏進了潘小樓的名字,同時也很符合她的小說氣質(zhì):“小樓一夜聽春雨”。只不過原詩后面還有一句,叫“深巷明朝賣杏花”。潘小樓的小說,勝在對徘徊于途中的問題人物的刻畫,但徘徊過后,似乎又了結(jié)得草率了一些。對瞬間困境的截取和表現(xiàn),在迅雷驟雨的短篇中可以自足,但在潘小樓這些枝蔓鋪展、情緒充沛的中篇里面,似乎就顯得有些不夠——畢竟這是綿綿春雨,不是來去倏忽的雷暴啊。福斯特所說的“不能了解”,也并不意味著寫作者的袖手旁觀,畢竟在小說虛構(gòu)的特殊意義世界里,寫作者本身在生死之外,他(她)是一位臨時性的上帝。我期待能在潘小樓的小說結(jié)尾看到多一些的異動,看到人物在走入黑暗之前,在某一瞬間披拂上了日落時分流溢的晚霞,而不是走著走著,就從監(jiān)控攝像頭的視線范圍里自然消失了。這當(dāng)然不是說必須在所有問題的終點給出一個虛假的解決,而是因那個特殊的時刻在小說中切實存在,我們就希望寫作者能夠展示出問題的另一面、展示出人物心中某一絲此前未有過的響動——哪怕它很輕微。那是一夜春雨后輕推窗欞的吱呀響聲,是結(jié)束,卻也是開始,它關(guān)乎一段敘事的真正完成。現(xiàn)在,“小樓春雨”已經(jīng)聽得很好了,我所期待的是天亮?xí)r分,樓中的女子在巷尾邂逅到一朵杏花。這是我對作者更長久的期待。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研部)
本欄目責(zé)任編輯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