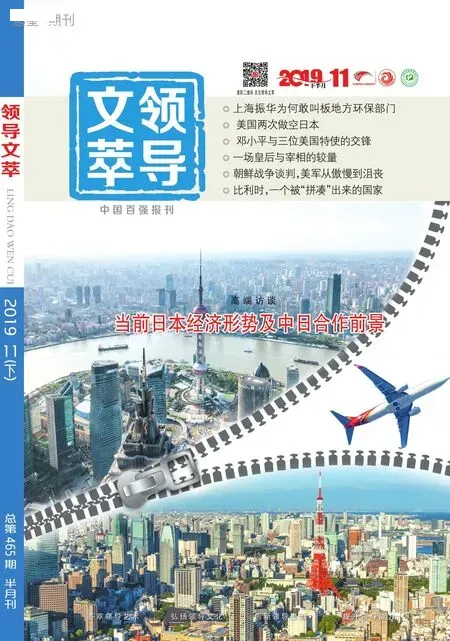一旦結(jié)發(fā)相伴到老
張松
他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一歲半時,母親也撒手人寰。祖父年邁,已經(jīng)七十多歲,做不得重活。為了讓他繼續(xù)學(xué)業(yè),在好心人的撮合下,10歲的他與鄰村大他6歲的她完婚。沒有請客,沒有花轎,邀請幾個親戚吃了一頓飯,他們完成了生死契約,將相依相伴一輩子。
結(jié)婚那天,她只帶了幾件衣服,住進他家。這哪里是家?家徒四壁,新房有門無窗,房頂上還長著青草。逼仄的房間里,祖父蜷著身子,窩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她一陣心酸,挽起衣袖收拾起來。他好奇地看著自己的媳婦,眼前這個個頭比他高很多的女孩。

她看著他笑了笑,他也笑著回應(yīng)。看她干活,他主動跟在她的身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了一會兒活,他覺得一點都不好玩,噘著嘴。她看出了他的心思,叫他去玩。他玩得興起,忘記了回家吃飯。她找來了,他正和小伙伴玩官匪游戲。他被抓進“大牢”,要推出去“槍斃”。她一把拉過他,緊緊地抱在懷里,心疼地說:“不能玩這種游戲,我會擔心的!”說著,撫摸著他的頭。他掙脫她的懷抱,又跑了過去,隨著小伙伴的一聲“槍響”,他應(yīng)聲倒地。然后爬起來,看著她哈哈大笑。她一陣揪心,發(fā)現(xiàn)他在自己的心里如此重要,成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管了,拉起他往回走,要他回去看書寫字。
她沒有上過學(xué),不認識字,但她知道只有讀書才能改變未來。她之所以選擇他,因為他是“文化人”,才毅然到了這個貧窮的家庭。以她的條件,她完全可以找一個家境好的。來到他的家里,她當起了家里的頂梁柱,既要照顧年老行動不便的祖父祖母,還要照顧年幼的他。
1905年,16歲的他去百里之外的永平府中學(xué)讀書。她舍不得他走,送他到車站。離別那一刻,他發(fā)現(xiàn)她頭上有一根白發(fā),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異常醒目。他的鼻子一酸,落下淚來。看著他落淚,她舉起了手,停在空中,想了想,又放了下來。他將她的手捧在手心,仔細地端詳。這是一雙布滿干繭的手,上面有很多條口子,有的地方還滲出了血。列車快要啟程,他轉(zhuǎn)身要走,卻停下了腳步,回過頭來,看著她,在心里對自己說:“等我學(xué)成歸來,我會讓你一輩子幸福。”然后,匆匆上了火車。
列車緩緩啟動,消失在鐵路的盡頭。她蹲在地上,腦子很亂,擔心他的安全,擔心沒有人給他做合口的飯菜。想著他去讀書,成為文化人,她又開心地笑了,回去準備多種些地,再買幾頭豬來喂。
兩年后,家里再次發(fā)生變故,疼他的祖父病逝。他接到信是幾天后,祖父已經(jīng)下葬。祖父的喪事,已經(jīng)花光家里的積蓄。她沒有告訴他,叫他安心讀書。他不知道,為了讓他能夠繼續(xù)學(xué)業(yè),家里已經(jīng)到處舉債。他很內(nèi)疚,只有用優(yōu)秀的成績來回報。中學(xué)畢業(yè)后,他考上了北洋法政專門學(xué)校。
1913年7月,他從法政學(xué)校畢業(yè)后,只身去了北平,爭取到日本留學(xué)的機會。這一別又是三年。回國后,他投身于政治活動,經(jīng)常東奔西走,見面的次數(shù)屈指可數(shù)。她沒有抱怨,知道他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而忙碌奔波。1918年,他在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謀得一個職位,基本穩(wěn)定下來。他迫不及待將她接到城里,還在房間里修了炕,跟老家的一模一樣,他怕她不適應(yīng)城里的生活。對她來說,能夠陪在他身邊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沒有任何要求。
原以為日子就這樣安穩(wěn)地過下去。1924年,國民黨當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蘇聯(lián)避難,讓她和孩子回老家。她不想回鄉(xiāng)下,要跟他走,死也要死在一起。考慮到孩子的安全,她還是回到了鄉(xiāng)下。
“三一八”慘案后不久,他被捕入獄。法庭上,他們再次相見。他說,她是我的妻子,我做的一切與她無關(guān)。看著他憔悴的樣子,她失聲痛哭,差點暈倒在地。她知道兩個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她當天被釋放后,沒有回家,而是圍著監(jiān)獄轉(zhuǎn)了半天。
不出所料,他和二十多名革命者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被殺害。那年他38歲,結(jié)婚整整28年。得到消息后,她哭暈過去,不相信他會死。如果要她陪他,她會毫不猶豫地跟著他一起走。她多么希望這一切是做游戲,就像小時候,他被“槍斃”后,再爬起來,看著她哈哈大笑,可這一切回不去了。收拾失落的心情,她帶著年幼的孩子回到老家。整整六年時間,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思念成疾,她病倒在床,卻仍掙扎著來到北平。他的靈柩停放在妙光閣浙寺,無法安葬,這是她這輩子未了的心愿,她請求北京大學(xué)將他安葬。北大校長蔣夢麟召集了一些共產(chǎn)黨人,發(fā)起公葬,讓他入土為安。忙完這一切,她已經(jīng)病入膏肓。35天后,她也離開這個世界,安葬在他的身邊,跟他永遠在一起。
她無私付出,他無怨無悔,他們的故事讓人感動。他叫李大釗,是我國早期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著名學(xué)者;她叫趙紉蘭,一個目不識丁的、包著小腳的農(nóng)婦。他們是結(jié)發(fā)夫妻、包辦婚姻,但不影響婚后的甜蜜恩愛。在另一個世界里,相信他們共續(xù)今生未完的緣分:他坐在書桌前,看書寫字;她守在旁邊做針線活。他們的生活簡單樸素,沒有戰(zhàn)火,沒有硝煙,沒有俗世的喧擾,做一對恩愛夫妻,一旦結(jié)發(fā),就相伴到老。
(摘自《做人與處世》
- 領(lǐng)導(dǎo)文萃的其它文章
- 共產(chǎn)黨員如何做到“不忘初心”
- 紙上俱樂部
- 經(jīng)濟七則
- 新書推薦
- 刺客行
- 怎樣才能成為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