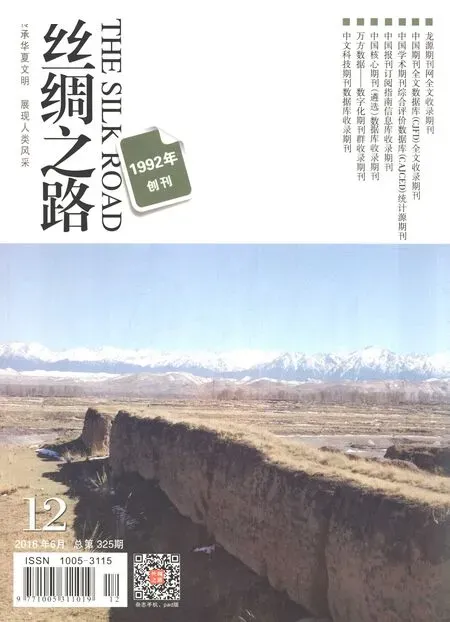唐代官服服色變化與政治變遷*
李媛媛 肖鵬程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400715)
?
唐代官服服色變化與政治變遷*
李媛媛 肖鵬程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400715)
[摘要]一個時代的服裝往往能投射出一個時代的文化偏好趨勢,而官員的官服則可以透視一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唐代官服服色制度在繼承前代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發展成為品色服制度。但其品色服制度的內容和貫徹程度在整個唐朝并非一成不變。唐代官服服色的變化折射出了唐代的政治變遷情況,也可以使后人從中洞見唐衰亡伊始的征兆。
[關鍵詞]唐代;服色變化;品色服制;政治變遷
*本文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生創新科研基金項目成果,指導老師為侯振兵。
一、“服有裘冕,典章興矣”——唐代服色的重要地位
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昔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上古簡儉,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習,乃改正朔,易服色,車有輿輅之別,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繢,飾之以繡,華蟲象物,龍火分形,于是典章興矣。”從有“禮”開始,服飾一直被作為區別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中,用顏色的規范來區分身份等級成為唐代服章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并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品色服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直觀的視覺效果上看,顏色是最明顯的區分方式。服飾的形式和配飾都只是在某些細節部分作了不同區分的設計,某些需要近觀才能察覺出來,而服飾顏色的不同則不需要仔細觀察就可以很容易地知曉著裝人的身份等級。
其次,從當時特定的文化背景看,李唐王室與西北的鮮卑族有著密切的關系,雖然已經基本漢化,但仍然保留著胡風遺跡和審美取向。少數民族一直對鮮艷醒目的顏色特別敏感,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北齊“高氏諸帝常服緋袍”。少數民族文化影響了唐人的審美取向,唐人也表現出喜歡艷麗的顏色如“緋色”的審美取向。
最后,唐代染色工藝的空前發展,為唐人重視服色提供了技術支持,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唐代以前,服飾顏色較單一,官員的身份區別也沒法特別用服色加以區分,其原因之一即為當時染色工藝尚不發達,難以染制顏色鮮明的布料。
二、唐代官服服色變遷概況梳理
唐代服色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遷。其主要變遷發生在武德年間、武周時期和“安史之亂”以后。
(一)唐初的官服服色——以《武德令》為中心
武德四年(621),制定初步的常服規范,即為《武德令》:“三品以上,大科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以下,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其色黃。”唐初的官服服色基本是以《武德令》為中心,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和完善的。
貞觀四年(630)二次下詔修訂《武德令》,《唐會要》載:“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敕七品以上……其色綠。九品以上……其色青。”上元元年(674)詔:“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分析,我們可以理清當時服色的主要等級從高到低依次是紫、緋、綠、青。品服制逐漸完善的內容主要是在這四種基礎色上增加深淺的區別。唐初基本奠定了以紫色、緋色為上色,綠色和青色則為次色的基本格局。
(二)武周時期唐代官員服色變遷
武周時期的基本服飾制度也符合唐初的《武德令》,也以紫、緋、綠、青為基本色。但與唐初相比,最大的區別是,武周時期盛行“賜紫”和“賜緋”。“賜紫”和“賜緋”即指紫色和緋色因其品色高貴而被皇帝用來賞賜以顯恩寵,即對于官階不夠著紫色和緋色官服的官員也允許他們著紫色或緋色服飾。
武周之前,已有賜紫制度,但賞賜數量有限,賞賜范圍較小,多賜予有大功或王室之人。武周時期,出于拉攏官僚、鞏固統治的需要,大興“賜紫”和“賜緋”。同時為打擊李唐王室,排除異己,掀起了揭發舉報之風,很多舉報人也因此獲得“賜紫”或“賜緋”的恩寵。《新唐書·車服志》記載:“武后擅政,多賜群臣巾子、繡袍。”《唐會要·內外官章服》也載:“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帶。”唐詩對武周時期的“賜紫”也多有描述,如唐代詩人王建《舞曲歌辭霓裳辭十首》:“一時跪拜霓裳徹,立地階前賜紫衣。”由此可見武周時期賜紫、賜緋數量之多、范圍之廣。
(三)唐中后期官員服色變遷
唐中后期,統治者對于服色的規范仍然很重視,宣宗和文宗是典型的代表。《資治通鑒》卷249載唐宣宗大中八年二月:“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但宣宗、文宗對服色規范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唐中后期的官服服色情況與唐初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混亂、僭越的情況。
據《新唐書·鄭余慶傳》記載“時數赦,官多泛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并且朝廷頻賞以籠絡地方節度使,許多地方刺史被給予“賜紫”的榮譽。據《冊府元龜》卷673“牧守部褒寵第二”記載:“李佐為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李愬元和中為坊、晉二州刺史,以理特異,詔加金紫……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歸義軍時期,服色混亂、僭越的情況更加突出,河西歸義軍政權前后過渡期的張承奉自立金山國,以“王”的身份賞賜紫衣、緋服。
三、從官服服色透視政治變遷
(一)《武德令》頒布時期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唐代前期主要以《武德令》為基礎,對服色做出規范并形成品色服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順應時代的要求。當時王朝新創,朝政初統,初建的唐王朝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大一統,制度比較混亂,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不斷涌現,需要用一種新的官服制度來彰顯新王朝的不同,需要用一種“禮”和“規范”來樹立一種權威,同時也需要用一種符號來使中央官僚形成一個統一的集體,緩和各個團體的沖突,更需要一種符號來鞏固“士族中央化”的成果。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希望有統一的官服制度來區分不同的等級,而品色服制度順應了這一要求,簡單明了的視覺差異起到了很好的等級區分的作用。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中央政府相對強大有力,頒布的詔令能得以貫徹,起到作用。
(二)唐后期政治形態與服制關系
與前期相比,唐中后期政治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服色規范方面的法令更加嚴格規范。但也應當注意到一個問題,服色等級在明確的同時,也越來越細化,基本上六品及其以下級別的官員都不能服用緋、紫,剝奪了原來低級官吏服用緋、紫的權利。
另一方面,服色規范效力有限,僭越情況難以禁止。上文提到,朝廷常常采取以“賜紫”、“賜緋”的恩寵來籠絡地方節度使,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地方政權自行賜服的案例也屢屢出現,這體現出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掌控力日趨薄弱和松弛。
雖然有服令的禁約詔敕影響力有限,但它仍然意味著中國古代服飾制度由禮治向法制的轉變。唐前期,社會相對穩定,主要奉行禮令并行的政策,重視禮的道德約束作用。“安史之亂”后,唐朝的政治社會生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禮的作用越來越難以實現,制禮和立法活動基本停止。
四、官員服色變化的影響
(一)服色變化體現的政治變遷內容
縱觀整個唐朝,雖然出現過一些變動,但官員服色變化的整體趨勢大致為在法律規范方面越來越嚴格,在實際生活中越來越混亂,僭越的情況層出不窮。唐朝以紫、緋為上色,青、綠為次色,但很多官階不夠格的官員也借由很多泛濫的賞賜著紫色或緋色。實際上,官服服色的混亂、僭越情況已經開始顯現出唐朝衰亡的征兆。唐中后期,雖然文宗、宣宗等時期對品色服制進行了更嚴格的規范,但因為執行力度不夠,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私自賜紫的現象,說明了中央權力的衰落,地方政府勢力日益強大,但中央政府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對地方的管理權,在已無實際軍權控制地方的情況下,通過規范官服服色等宣示中央權力,表示對地方仍有名義上的控制權。
(二)唐代官員服色文化對后世的影響
唐代服飾以式樣繁復、配飾多樣、色彩艷麗為主要特征,體現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對后世的影響極其深刻。品色服制這種通過服色來明貴賤、區分官員官階等級的方式,為中國古代官服制度增加了新的內容,影響了宋、遼、明、清的官服制度。在唐衰落之后,“賜紫”、“賜緋”制度因其過于泛濫失去其實際作用也漸歸衰落,但其延伸出的在服飾方面進行賞賜的制度一直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清代的“賜翎”、“賜頂戴”、“賜黃馬褂”等。唐代品色服制、賜紫等制度雖未被后世直接繼承,但開創了以服飾顏色、配飾來區分官階、明貴賤知等級的先河,對后世的官服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北宋·王溥.唐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長沙:岳麓書社,2009.
[4]北宋·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5]北宋·王欽若.冊府元龜[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6]納春英.唐代服飾制度與服令變化[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10,(12).
[7]馬冬.唐代服飾專題研究——以胡漢服飾文化交融為中心[D].陜西師范大學,2006.
[8]王春慧.唐代服章制度與敦煌賜紫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12.
[9]李怡.唐代官員常服制度考[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10).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2-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