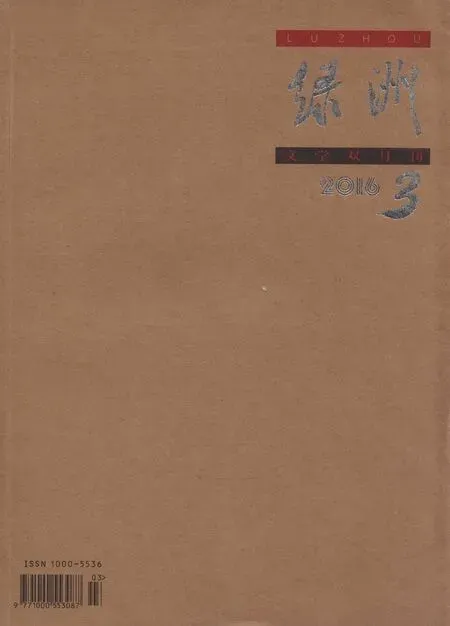假戲假做
馮積岐
假戲假做
馮積岐
他們到達西水市的時候下午四點半了。
他們住進了市內的假日大酒店。這里距離明天開會的地方只有兩站路。
走進賓館的房間,他們各自泡了一杯茶,有滋有味地喝著。
胡來說,出去走走吧。
牟醒說,西水市的角角落落,哪個地方沒走過?
胡來說,要不,把蘭花叫來?
牟醒說,算了吧,只有半天會議,我沒有告訴她要來西水市。
胡來說,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現在給她打電話也不遲。
牟醒一笑:你想她了,得是?你有她的電話,你給她打。
胡來也笑了:啥人嘛?你的情人,我想她干啥?我是說,女人要常伺弄,你不伺弄她,時間一長,她就成為別人的了。
牟醒一笑:我是有自信的。蘭花說過,再過五十年,她還是照樣愛我。她給我發誓,只愛我一個。
胡來說:你這么相信愛情?
牟醒說:你不相信愛情?
胡來說:愛情是什么?愛情是一種理想,理想就是海市蜃樓,永遠不可企及,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愛情不能懸在空中,要落地,落在實處。所以嘛,愛情最終歸結于肉體。
牟醒吭地笑了:照你說,愛情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床上那點活兒?
胡來說,有愛情就必然上床。你和蘭花長時間不上床,還能有愛情嗎?說句你不愛聽的話,她早睡在別人的身底下了。真正的愛情是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結合。缺了上半身或下半身,都不行。
牟醒說,你小看蘭花了,她只愛我一個,她對我愛的死心塌地,在海南島,你是目睹過的。愛情,首先是一種美好的情感。愛情來自大腦和心臟,不是下半身。沒有純潔的情感,你把她整天看守著也是枉然。
胡來說,好吧,你就陶醉在你的愛情中,我出去走走。
胡來下了樓。
牟醒和胡來一同在省城里的群眾藝術館供職。他們是大學里的同學,是一對好朋友,他們之間,無話不說。牟醒和白蘭花相好的事是牟醒主動告訴給胡來的。白蘭花在西水市群眾藝術館工作。有一年,牟醒去塞北市舉辦全省群眾文化工作培訓班。在塞北,牟醒和白蘭花相遇相識了。初秋的塞北,涼風習習,風景如畫。每天晚飯后,白蘭花陪著牟醒去郊外散步,兩個人談文學、談繪畫、談書法。不論談到什么話題,白蘭花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牟醒對白蘭花的第一印象是:才女。在一片小樹林,當白蘭花主動地偎依住牟醒的身體的時候,牟醒緊緊地抱住了她。當天晚上,兩個人就睡在了一起。牟醒結婚十年了,他在妻子那里從來沒有享受過如此龐大的肉體之歡。他愛上了這個小他十三歲的已婚女人白蘭花。從此以后,兩個人逮住機會就幽會。當兩個人交織在一起的時候,白蘭花呻吟著說,我、只、愛、你一個。
白蘭花的這句話刀刻一般刻在了牟醒的心里:我只愛你一個我只愛你一個我只愛你一個。
有一年,海南島舉辦學術研討會,主辦方點名要求秦西省的牟醒和胡來參加。去參會的前兩天,牟醒給胡來說,我想帶上蘭花一起去,行不行?胡來說,有啥不行的,三個人更熱鬧了。再說,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牟醒一聽,激動萬分:朋友還是朋友,只有真誠的朋友才能這么相互理解,相互關照,相互支持。
到了海口,住進一家賓館。當天晚上,牟醒就給蘭花說,當著胡來的面,你不能對我太親熱,這樣,對胡來有刺激。他是咱們共同的好朋友。蘭花說,分寸我會掌握的。他有沒有女朋友?咋沒有帶?牟醒說,他有好幾個女朋友,可沒有一個好過一年的,幾個月就分手了。據我所知,身邊暫時沒有。蘭花說,你們男人都這么花心。消費女人像吐瓜子皮一樣。我只愛你一個,和你相好一生一世。不會只好幾個月就分手。牟醒說,你的老公呢?蘭花說,和老公只是搭伙兒過日子,誰還說愛不愛的話?牟醒說,我也只愛你一個。蘭花笑了:那就開始愛吧。牟醒把蘭花壓在了身底下。當蘭花很殘忍地喊叫了一聲之后,牟醒急忙捂住了她的嘴:胡來就在隔壁,你忍著點。蘭花吃吃地笑了:忍不住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現在死了都值了。
上了飯桌,蘭花給牟醒夾一筷子菜,必然要給胡來夾一筷子菜,蘭花和牟醒碰一次杯必然和胡來碰一次杯。
到了風景點上,蘭花和牟醒合一個影,必然和胡來合一個影——她一只手挽住胡來的有胳膊,頭顱緊緊偎依胡來的胸,一副十分親熱的樣子,比她和牟醒在一起親熱多了。晚上睡覺前,牟醒和蘭花要在胡來的房間里去聊一會兒,直至蘭花呵欠不斷。牟醒一看,就挑破了:你倆回房間睡吧,不必來安慰我,你倆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蘭花說,胡大哥真好。胡來一笑:肯定沒有牟醒好。蘭花臉紅了:才說了你一句好,就說壞話了。胡來說,咋能說是壞話?牟醒好不好,你不知道嗎?蘭花說,當然知道。
有一天晚上,牟醒感冒了,他吃了一片感康老早上了床。蘭花說,不去胡大哥房間了?牟醒說,要去,你一個去,我頭痛,老早睡呀。蘭花說,你不吃醋?牟醒說,吃啥醋?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還怕他偷了你?蘭花俯下身在牟醒的額頭上親了親:我去坐一會兒就回來。牟醒說,你去和他說說話,他一個人孤獨。
牟醒在睡意朦朧中聽見蘭花說,你出汗了。牟醒說,你也出汗了。蘭花說,出點汗好。牟醒說,好,好,都好。蘭花不知道牟醒是在說夢話,還是清醒著,牟醒說,你咋才回來?天快亮了吧,你們得是睡了一覺了?蘭花說,別說夢話了,睡覺。牟醒說,睡,睡,我只睡你一個。蘭花躺在牟醒身邊,一會兒就睡著了。
胡來還沒有回來。
牟醒從包里拿出來一款新手機。這是他上午才拿到手的——他五年的話費超過了一萬五千元,移動公司獎勵了他一款手機。他辦了一個新號。吃畢中午飯,他和胡來上了高鐵,還沒有使用過一次新手機。
拿起手機,牟醒不知道該打給誰——這個新手機號,他不想叫更多的人知道。他想了想,還是先和蘭花通個話——不,既然昨天沒有告訴她,他要來西水市,今天就更不能說了。先匿名給她發個短信,來個假戲假做——算是和她玩一回游戲:
親愛的,我是你的一個男朋友,可以約會嗎?
可以,你在哪里?
牟醒搖了搖頭,揉了揉眼睛。手機屏幕上還是那句話:可以。你在哪里?這個白蘭花,怎么連姓名也不問就答應了約會?看來,這出假戲必須演下去了:
我在西水市,你在哪里?
我當然在西水市。在什么地方約會?
西府大酒店,怎么樣?請你吃晚飯。
幾點?
六點整。
可以。報上你的姓名。
見面自然知道。
既然是我的男朋友,怕什么?
我想給你一個驚喜,叫你知道,我就是你日思夜想的人。
我連姓名都不知道,怎么約會?莫非設局?
你是西水市的女畫家,誰還敢騙你?當年,咱們恩恩愛愛,在一起翻云覆雨的情景歷歷在目。你忘了?
既然有肌膚之親,還怕我知道你是誰?算什么男人?我不來了。
你在省城有幾個情人?就我一個吧,還用我說出姓名嗎?
我在省城的情人一大把,你不說出姓名,我知道你是哪一個?
別開玩笑了。你說過,只愛我一個,只有我一個。見面你會很驚喜的。
不見面。
牟醒額頭沁出了汗,這出戲做不下去了。他剛合上手機,陷入沉思。手機鈴響了。他一看,是白蘭花打來的,沒有接,過了一會,他又給白蘭花發了短信:
我不方便接,請理解。
和誰在一起?女人嗎?
和市政府領導在一起,談工作。
不要演戲了。你的演技太低劣。
蘭花,我本來想給你一個驚喜的,既然逼我,我就告訴你,我姓胡,明白了嗎?
在省城,我有兩個胡姓朋友。不知你是哪一位?
大胡。
我知道了,六點見。
如果是戲演,這一出,已經合上了幕布,牟醒想,如果他不去,這個手機號蘭花遲早會知道的,他會責備我,說我在試探她。如果去,蘭花問他,你來西水市為什么不提前告訴我,是不是還有約會——到那時候,他怎么也說不清的。令他更吃驚的是,蘭花竟然在省城有兩個胡姓朋友。是蘭花胡謅的,還是真的?牟醒正在為難之際,胡來回來了。
牟醒把剛才和白蘭花互發短信的內容給胡來敘述了一遍,胡來說,兄弟,不是我說你,這就怪你了,你說你是不是想試探蘭花?說心里話。
是。
蘭花是你的妻子嗎?你試探她,有這個必要嗎?即使她只愛你一個,世上也不會有永恒的愛。你不在她的身邊,你知道她會做出什么來嗎?
不知道,但我相信她只愛我一個。
還相信她的那句話?你算得上愛情庫里的愛情專家了。你說這戲還演不演?
當然要演,我不能因為這點小事失去她。
怎么演?
是這樣,你拿著我的手機去和她吃一頓飯,就說是你剛才發的短信,叫她看一看。你不正好姓胡嗎?
胡來在房間里走動了一圈。胡來說,危難之際,還是朋友靠得住,再不要提什么情人了。能給你當情人的女人同樣可以給別人當情人。
不,她只愛我一個,我不懷疑她,不然,這一出就不演了。
好。她只愛你一個。我去替你圓場。
胡來走后,牟醒突然覺得心里空蕩蕩的。走進餐廳,他對什么飯菜也沒胃口,只喝了一碗稀飯,就下了樓。
華燈初上。牟醒毫無目標地在西水市走了一圈,上到十三樓時,已經晚上九點了,他打開房間的門一看,胡來還沒有回來。他急忙給胡來撥電話,回答是:沒有在服務區。牟醒的心跳加快了,他一急,于什么也不顧,給白蘭花打電話,回答是:你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這可怎么辦?牟醒認識西水市群眾藝術館的館長,他先是問館長,白蘭花還有沒有其他手機號,回答是,不知道。他又問館長,白蘭花家住在什么地方?館長說,群眾路,大眾花園十五棟十樓六號。牟醒下了樓,攔了一輛的士,直奔群眾路的大眾花園。他只有一個念頭:我去找她。我只愛你一個我只愛你一個我只愛你一個。假如她不在家,你貿然找她,你怎么回答她的愛人?見了面再說。這已經不是演戲,這是生活,是刻骨銘心的生活!牟醒這時候十分清醒。他斷然上了十樓,按響了六號房間的門鈴。開門的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男人。男人用疑惑的目光壓住他:你是誰?牟醒說,這是白蘭花的家嗎?男人說,就是。牟醒說,我是蘭花的同事,找蘭花有事。男人說,打她手機呀,她不在家。牟醒說,手機關機了。男人說,她五點多打電話說,她去省城里開會,上了高鐵。牟醒似乎忘記了他身處何地,他咬著牙說:開狗屁會。哄人的話。白蘭花。好一個白蘭花!牟醒失態了。他扭頭就走。男人啪地一聲關上了門。
回到賓館。牟醒輪番給胡來和白蘭花打電話。回答是一樣的:不在服務區。關機。牟醒明知電話打不通,卻還不停地撥,一直撥到了凌晨一點多。牟醒毫無睡意。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只愛你一個只愛你一個只愛你一個。
牟醒在房間里來回走動著。
牟醒站在窗戶跟前,遠眺著閃爍的霓虹燈。他雙手抓緊了自己的頭發,咬著嘴唇,生怕眼眶里的淚水噴涌而出。
牟醒抽了一支煙,靜靜地坐了一會兒。蘭花在他眼前頭晃動,那雙美麗的大眼睛一睇,紅潤而性感的嘴唇啟動了:我只愛你一個只愛你一個只愛你一個。牟醒干巴巴地苦笑了幾聲,將頭埋進被子里,發冷似的抖動著:情人情人情人情人啊!
牟醒背起自己的包,拉上了門,到一樓的前臺去退了房間。他坐上了去高鐵站的的士。
凌晨四點半,牟醒回到了省城里自己的家。他本來想打開門輕手輕腳地走進去,可是,不知怎么地走到了客廳,放置肩上的包兒時打翻了一只瓷茶杯。妻子被驚醒了。她半裸著到客廳一看,不是竊賊,而是她的丈夫:咋回來了?不開會了?牟醒跌坐在沙發上:我不舒服。妻子坐在他旁邊,不舒服就去醫院,要緊不要緊?牟醒看了妻子幾眼:不要緊。妻子的手觸摸他的額頭,他倒在妻子的懷抱里放聲大哭了。
責任編輯王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