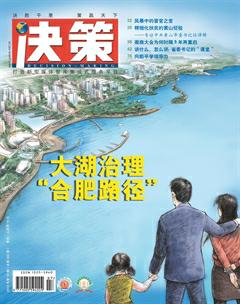杭州“基金小鎮”密碼
劉炳輝

杭州“基金小鎮”掛牌一年多來,以打造中國“格林尼治小鎮”為定位,累計入駐金融機構500余家,集聚高端專業人才1600多名。其背后到底有哪些力量在推動?
浙江省“特色小鎮”已然成為眼下炙手可熱的基層發展創新品牌項目,并且隨著浙江和江蘇地方領導干部的交流也開始在江蘇逐漸推開擴大。2015年6月4日,第一批浙江省省級“特色小鎮”創建名單正式公布,全省10個設區市的37個小鎮列入首批創建名單。其中杭州上城區玉皇山南基金小鎮,是浙江近百個特色小鎮創建單位中的佼佼者和明星。
杭州基金小鎮所在地,以前主要是陶瓷品市場為核心的石材初加工和倉儲業,轄區內有鐵路機務段、維修廠等大型國營單位,還有大量民居,整體而言可謂建筑陳舊,布局散亂,基礎設施殘破。經過地方政府頗費心思的“三改一拆”重新布局后,2015年5月16日,正式掛牌成為基金小鎮,現在儼然是以打造中國“格林尼治小鎮”為定位,累計入駐金融機構500余家,其中不少為行業內領軍企業,集聚高端專業人才1600多名,繼2015年稅收破4億元后,今年一季度小鎮稅收已超過3億元,同比增長313.85%。管理資產規模也從去年的近1800億元增長到一季度末的2800億元,目前已超過3200億元。
但是,在獲得中財辦首肯并被各地積極學習的熱潮之下,我們需要冷靜的思考和總結分析,“特色小鎮”背后到底涉及到哪幾個方面的條件支撐,而杭州基金小鎮恰恰給我們一個解剖麻雀的良好契機。筆者認為,以杭州基金小鎮為典型個案的浙江省特色小鎮建設,深層次涉及至少四個領域:產業、地域、空間和供給側。
產業:
區域轉型升級的大潮流
在這一輪“特色小鎮”建設中,杭州無疑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并且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所謂“特色”,首先指的是產業上的特色,隨后才是自然人文生態環境方面。浙江省在推廣和宣傳特色小鎮時,非常明確且突出的指出了其“聚焦浙江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興產業,融合產業、文化、旅游、社區功能的創新創業發展平臺”。制造業在這里顯然不是毫無原因地被排在了第七位,而且還要加一個形容詞“高端”。這就是當前浙江省對于下一步產業發展的一種長遠考慮和定位。作為全國人均最富裕的省份、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長三角的南翼,這個東部沿海大省的定位和眼光無疑已經指向了遠方。“特色小鎮”的浪潮只有放在這個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也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基礎。
而且,這當中杭州無疑在浙江省內又具有獨特優勢,因為杭州有阿里系、海歸系、浙商系和浙大系這四支創業創新的“新四軍”。這種優勢在浙江省11個地級市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否則為何同屬浙江省的寧波梅山金融小鎮和嘉興南湖金融小鎮都乏善可陳呢?在杭州基金小鎮被考核為“優秀”的同時,另外兩個小鎮只有頗具危機感的“合格”。這些都說明,即使同在長三角、甚至同屬浙江省內,哪怕寧波總體經濟實力穩居省內“老二”,嘉興距離杭州僅僅一步之遙且距離上海更近,若無整體的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大背景,基金小鎮也是難以做大做強的。
同樣從民營經濟的“低、小、散、弱”(層次低、品牌小、結構散、創新弱)制造業起家,但杭州更為超前和具有遠見的產業定位和政府大力推動轉型升級,使得其成為和深圳比肩的近年來轉型升級成功樣板,這已經讓省內即使位列“老二”的寧波都“壓力山大”,近年來寧波官民都屢屢追問被杭州越拉越大的原因,整個城市陷入“反思”。杭州現在已經成為國內金融體量第五的重要城市,沒有這個強大的實力為基礎,玩金融顯然是不現實的。杭州基金小鎮敢于鎖定中國的“格林尼治小鎮”,也是因為自身的金融體量加上比鄰上海的區位優勢,這使得其具備與比鄰美國金融中心紐約的格林尼治小鎮相較高下的底氣。反觀位于杭州和上海之間的嘉興,雖然距離全國金融中心上海更近,但自身的金融實力太弱且缺乏足夠的人才,使得南湖金融小鎮欲振乏力。可以說,整個浙江省只有杭州相對較好的完成了從傳統制造業向文化創意產業、互聯網電子商務、金融、旅游等高端第三產業轉型的過程,寧波、溫州、紹興等省內經濟強市也還任重道遠。因此,各地在打造各自的“特色小鎮”時,需要高度注意結合本地的特色,目標遠大是好的,但也需要腳踏實一步一步來。學習浙江“特色小鎮”的經驗,也要撥開表面的靚麗成績單,深刻分析觀察其背后更加抽象和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地域:
長三角城鄉一體化優勢
一提到“小鎮”,很多人容易聯想到是一個“鄉土氣息”很重的偏僻之所,因為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傳統是“城鄉二元”體系,城市里是繁華熱鬧、交通便利、物質充裕、文化昌明等,而“鄉鎮”往往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物質匱乏、愚昧無知等。可以說至今中西部一些地區的城鄉發展差距還是較大的,但問題在于長三角一帶已經改變了這種傳統的發展落差格局,實現了城鄉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在浙江省各地的11個地級市和90個縣區中,多數地方是很難說縣區就比市區發展差多少,“強縣”是這個地理面積上的“小省”的一個特點。加之高密度的高速公路網絡建設,使得各地交往極為便利,再加上近年來突飛猛進的高鐵網絡建設,整個長三角區域內部已經出現某種“同城化”趨勢,尤其是在蘇南、上海和浙北之間,高鐵都是1小時交通圈。這個基礎性的社會支持條件,不能夠忽視但又常常被忽視。
再回到杭州基金小鎮,如上所述,這個小鎮即使是真的在所謂“鄉下”,其實也不必擔心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會有任何問題。但還要指出的是,這個小鎮其實是在杭州市中心,是比鄰錢塘江且距離西湖最近直線距離不過3公里的地方。“小鎮”只是一種措辭上讓這里顯得自然生態環境更加優美迷人,但絕非是說位于“窮鄉僻壤”,這也是外界容易“望文生義”后陷入誤解的地方。
這里不得不重新思考審視浙江省提出的“特色小鎮”概念,其也反復強調過“特色小鎮‘非鎮非區,不是行政區劃單元上的一個鎮,也不是產業園區的一個區,而是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聚焦浙江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興產業,融合產業、文化、旅游、社區功能的創新創業發展平臺。”由此我們便明了,這樣的“小鎮”,也許很可能完全就是幾棟寫字樓,如果周圍環境恰好比較優美,那么順帶建設成旅游風景區也是可以的。但絕不是說,“小鎮”就一定要具有風景如畫的自然生態環境,而只是指空間上的聚集效應,這種聚集效應也跟浙江省多年來形成的“塊狀經濟”歷史特色有關,是一種歷史的傳承。
空間:
螺螄殼里做道場的傳統
對于浙江省“特色小鎮”,很容易忽視“小”字。對于這個“小”,原浙江省省長李強,曾于2016年初在《今日浙江》上發文,講到“特色小鎮是破解浙江空間資源瓶頸的重要抓手,符合生產力布局優化規律。浙江只有10萬平方公里陸域面積,而且是‘七山一水兩分田,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在非常有限的空間里優化生產力的布局。從塊狀經濟、縣域經濟,到工業區、開發區、高新區,再到集聚區、科技城,無不是試圖用最小的空間資源達到生產力的最優化布局”。
各地自然資源稟賦不同、歷史文化差異較大、產業結構特征和發展水平迥異,所以創新平臺的建設也需要因地制宜。既要理解浙江省“特色小鎮”的由來和內涵,也要看到其特點和局限。比如同樣是長三角省份,江蘇省和浙江省面積相當,但卻是“七田二水一分山”,江蘇是全國最不缺“田”的省份,這是與浙江的一個巨大差異。所以浙江的發展經驗很多具有“山區經驗”的特點和制約,而江蘇則風格迥異。因此雖然地理上比鄰,但吳越之間千百年來無論在居住人群、歷史風俗、經濟產業結構、文化特征都具有較大的區別。同樣是“做道場”,“螺絲殼”里有其做法,“天壇”上也有其做法,玩法可以完全不同,但也都有可能玩好。
“小”并非天然的給定條件,不必過于拘泥于此,但“小”背后體現的節約意識、講究效率的精神則是我們各省各地都需要認真對待和學習的。這就是看表面和看實質的區別,否則拘泥于浙江省提出的“特色小鎮”的“其規劃面積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設面積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教條不能自拔,就過于愚蠢了。
供給側:
現代服務型政府體系
以上經驗,有些具有廣泛的可學習、可復制性,有些則是一些因地制宜的地方性舉措,并非各地都需要教條主義地遵循。但浙江“特色小鎮”在字面上看不出來、卻具有更深刻時代意義和廣泛學習性的地方,在于其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供給側改革”的探索,建立現代服務型政府體系,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良性互動探索出更多新的內涵。2015年9月,中財辦主任劉鶴在浙江調研時曾指出,“對特色小鎮印象最深的是處理好了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為企業創業提供條件,大膽‘放水養魚,讓企業家才能充分發揮,這對我國經濟結構升級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包括杭州基金小鎮在內的近百個特色小鎮,其有一條特征或者說經驗在于,政府要能夠深刻理解和執行類似于“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的服務理念,具體如推行一站式辦公、一個窗口對外、一條龍服務,最大限度地精簡審批流程,最大限度地去掉中間環節,為創新創業清障搭臺。杭州基金小鎮深刻領會小鎮的核心財富在于“人才”,為了使人才有用武之地而無后顧之憂,依據杭州人才新政72條,制定一系列有針對性的人才政策,出臺了金融、科技、人才“1+3”政策體系;為高端人才就近提供人才公寓;邵逸夫醫院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鎮國際醫療中心落成,面積約800平方米的醫療中心可為園區人員提供國際醫保結算,并開通就醫綠色通道;設立從幼兒園到初中的國際化雙語學校,解決人才子女教育問題。甚至于考慮到很多海歸對沖基金經理,大多是專業技術型的“理工男”,在企業管理、商業運作方面往往并不擅長。小鎮為幫助他們成長,在最初的股權結構設計、企業經營管理等方面都積極參與并給予指導。
具體的政策都很容易學,到小鎮取取經拿走一疊文件資料回去就可以復制,但這種理念和精神才是根本,沒有這種理念和精神指導,任何具體的政策也僅僅是字面文字而已。以杭州基金小鎮為代表的浙江省“特色小鎮”建設,未來的征途還會有很多荊棘,這并不奇怪也無須諱言,但從以上四方面情況因地制宜走出一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路,則是各地都需要認真思考和鉆研的。
(作者系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