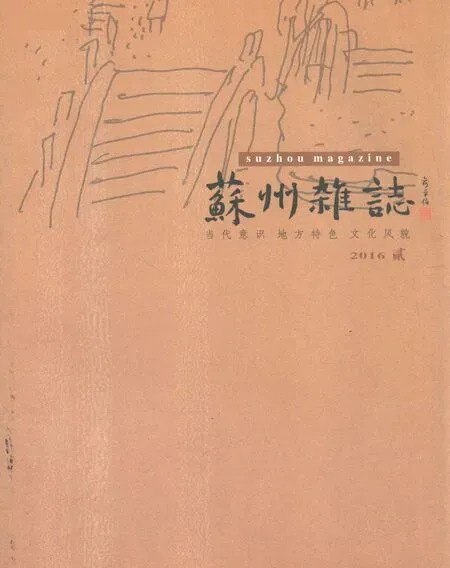蔣風白先生
馮其庸
蔣風白先生
馮其庸

蔣風白作品
蔣風白先生是著名的書畫大家,我與蔣老是同鄉,我是無錫,他是武進,聽起來是兩個地名,但實際上是緊連在一起的。蔣老比我大九歲,是我的大兄一輩。他早年從著名畫家潘天壽學,深得潘老的神髓。但后來他轉益多師,自己拓展了寬廣的畫境。
我認識蔣老,已經是“文革”之后,記得是上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了。有一次我去蘇州,蔣老特意陪我到甪直看保圣寺唐楊惠之的泥塑。又看到詩人陸龜蒙的斗鴨池。我們在甪直午飯,魚蝦之鮮美,久居北方的人偶一品嘗,會真正領會到江南魚米之鄉的特殊風情,尤其是甪直婦女的服飾,讓你感到既特殊又新鮮,真有光彩照人的感覺;而她們一開口,你才會領略到真正的吳儂軟語,因為當地還保留著濃厚的吳語特色,而在蘇州這樣的大城市,吳語的成分已經被普通話沖淡不少了。此行我們還經過了橫塘、石湖等勝地,但要找陳圓圓和范石湖的遺跡,卻是茫然無存了。盡管這樣,對我這個一貫喜歡調查歷史遺跡的人來說,也仍是不虛此行。何況橫塘、石湖都還保留著蒼茫的湖面,可供你作歷史的遐想。
后來,我又去蘇州調查吳梅村墓,蔣老特意請了他的朋友徐文魁兄來,陪我一起到鄧尉。那次雖然沒有找到梅村墓,但一個月后,終于把梅村墓找到了,并由幾位朋友出資為之重建。這件事的開頭,也是與蔣老有關的,所以值得一提。
我去蘇州的次數多了,記得有一次,蔣老一定要留我看他的一批畫,大概整整看了半天,我幸虧看了這些作品,對蔣老的畫才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實際上蔣老是個全能的畫家,可以說,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幾乎無一不能,無一不精。我特別欣賞他那幅《踏雪尋梅》圖,無論是風雪中的山水、人物,還是那頭瘦驢,和那座古老瀕危的竹橋,滿幅的氣氛讓你感到濃郁的詩意和天然的美景。無怪乎這幅畫有盧前、梁實秋、張充和等名家的題評了。我還看過他的幾幅人物畫,也極精。無論是眉眼衣紋,用筆都極精到,使人感到如行云流水,筆墨酣暢而轉折有致。還有他畫的翎毛,如八哥、喜鵲、蒼鷹、鸚鵡、蠟嘴、麻雀等各色鳥類,皆能栩栩如生。尤其是他畫的八哥,學名鴝鵒,其用筆之精到、爽利、準確,令人心折。畫家之筆,如俠士之劍,劍法不精,不能入神;畫家的筆法不精,拖泥帶水,造型就不能準確,形象就不能生動。而蔣老用筆,可說筆無虛發,筆筆準確,一個鴝鵒,只消幾筆,使毛羽松然,欲飛欲住。生動至極。我曾見唐寅的《鴝鵒圖》,其所作鴝鵒,只寥寥數筆,便婉轉枝上,欲啼欲飛。我乍見蔣老的鴝鵒,竟如唐畫,可見筆底的功力和神韻。蔣老所畫花卉,如海棠、月季等,用色之鮮靈,真可稱“活色生香”。我園子里有甸貴的西府海棠兩枝,每到花時,初如胭脂,嫣紅欲滴,始花時紅極而嬌,坐對名花,令人欲醉。我看蔣老的海棠,竟如我園中之初發海棠,其筆墨之精,用色之鮮靈,好像剛從枝上移來,令人嘆服此老畫筆設色之精能。至其所作荷花,構圖仍師法乃題,荷花的造型畫法,亦是從潘翁處來,可謂盡得潘翁之秘。

蔣風白
但蔣老所作的梅花,則自出機杼,既不受近代吳昌碩的影響,也不受王元章、金冬心等前賢的規范,竟是自出手筆,別具風標。有一次他來看我,恰好我要到友人壺藝大師周桂珍處為她題寫她新作的紫砂壺,蔣老也欣然同行,因為是緊鄰,出門即到。我題完幾把茶壺后,請蔣老一揮,蔣老說他沒有畫過茶壺,尤其是要一手托著茶壺,一手即在壺上著筆,覺得很不習慣。但見獵心喜,覺得很有趣,他就拿起畫筆,一手托著茶壺,畫了起來,他一邊在壺上畫梅花一邊卻連說不行,他一連畫了兩把就不再畫了,但我拿來一看,雖寥寥幾筆,卻是神韻獨造,后來刻好燒出后,更見精神。畢竟蔣老老筆紛披,著手成春,不同凡響。后來他自己看后,也覺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原說將來再來畫幾把,但后來竟未能來。所以這兩把蔣老畫的梅花紫砂茶壺,就成為蔣老畫紫砂壺的絕筆,也是紫砂壺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我認識蔣老的時候,蔣老已摒棄其他,專畫蘭竹了,我曾問他為什么要作這樣的選擇。他說畫要精,要達到超越前人,必須專,如果樣樣都畫,這很難達到最高境界。由此可見蔣老的目標高遠,對自己要求之高之嚴了。當然歷史上并非沒有真正全能的畫家,那實在太少了,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徐文長,可以說他于畫道,無一不能,無一不精,但這樣的人畢竟太少了。所以蔣老雖然早年于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等無一不能,但他最后的抉擇還是十分正確的。
說到蔣老的蘭竹,自是他的專項,我與他相交近三十年,見他所畫蘭竹夥矣!而且他還不時地要我為他題跋,近二十年來題得更多,我雖有辭窮之感,但故人情誼,只能勉為其難。
蘭竹在我國的歷史上是重要的一門,可以說是代有名家,就是近世,也有吳昌碩、蒲作英、符鐵年、白蕉、陳定山、蕭龍士等,都是畫蘭竹的高手。其中白蕉、陳定山、蕭龍士三位我曾直接交往過。另外還有當代畫家朱屺瞻先生,也好畫蘭竹。他曾為我畫過四米長的蘭竹長卷,由劉海粟大師題引首。朱老的蘭竹,如疾風暴雨,節奏強烈,筆墨如狂飚突起,令人心驚魄動,自然是一件驚世之作。還有一次他住北京飯店,我陪他游長城等地,臨別時,我去送行,他忽然拿起筆來,縱橫飛舞,頃刻為我畫一幅四尺整幅的墨竹。可能是因為他忽然興到,用筆有如狂草,我看了驚嘆不已。再往以前看,清代的石濤、金農、李方膺、鄭板橋都是畫竹大家,其中我最佩服石濤。石濤的蘭竹,自然天成,最得蘭竹的神韻和天趣,但世人卻只知鄭板橋的蘭竹,而不知其他。板橋的蘭竹,自然也是直節堂堂的大家,世人愛他也自有他的可愛之處,但比之石濤,就缺少自然之趣,而顯得筆有定勢,不如石濤之自然多姿。
蔣老的蘭竹,我認為方之板橋則有余,方之石濤則不足,或在兩者之間。方之板橋有余者,蔣老的蘭竹,有板橋之勁節而富有變化,無論是竹是蘭,蔣老均較多姿,構圖亦能擺脫定式,力求自然,此所以較之板橋,略勝一籌,然欲如石濤之隨意生姿,自然天趣,相去尚自有間,非可以咫尺計也。
現在蔣老離開了,其遺墨余韻,流布人間,人們爭相收藏,日益見重。予曾為蔣老題其畫蘭竹,今即以此詩為本文之殿。

蔣風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