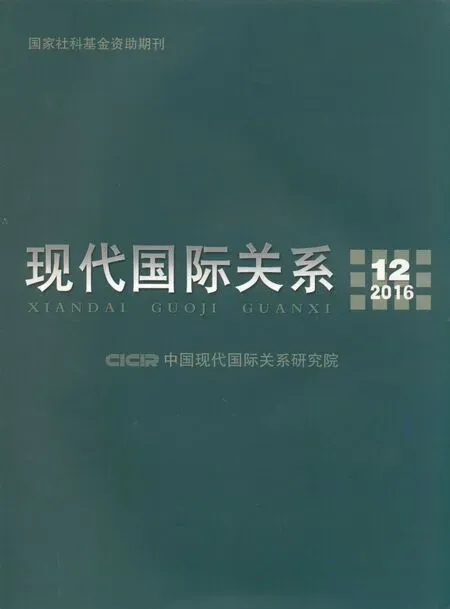美國對華威懾與脅迫及中國應對*
張文宗
美國對華威懾與脅迫及中國應對*
張文宗
威懾與脅迫是兩種不同的戰略,后者比前者更具進攻性。“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奧巴馬政府重要的“外交遺產”。在實施該戰略的過程中,在釣魚島、南海、網絡安全、朝核及伊核等問題上,美國對中國實施了軍事威懾及非武力性脅迫。總體看,這些手段尚屬輕度強制,與近年美國對俄羅斯、敘利亞、朝鮮和伊朗的嚴厲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有顯著區別。在中美存在重大分歧的領域,兩國的戰略回旋余地在縮小。未來如果美國對華加碼威懾和脅迫,中國可以更積極有效地應對,但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難度將增加。
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 威懾 脅迫
[作者介紹] 張文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美關系和美國政治研究。
中國崛起和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改變和正在改變著中美關系的內涵。隨著中美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威懾、威逼、脅迫、脅迫外交等冷戰期間的流行語言和冷戰后美國對一些中小國家的政策手段,日益出現在中美兩國的戰略敘事中。在釣魚島、南海、網絡安全和防擴散等議題上,奧巴馬政府頻繁對華實施威懾和脅迫,對華政策的主動性、強制性和進攻性增強。在一些熱點問題上,中美兩國的政策回旋余地均在縮小。未來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共和黨傳統的國防鷹派政策,美國對華升級強制手段和中國提升反制力度的可能性都會上升。
一、威懾、脅迫與脅迫外交
威懾(deterrence)和威逼(compellence)是兩種戰略,其中威懾指通過威脅使用武力,嚇阻對手不要做某事,威逼則是通過武力威脅迫使對手做某事或停止做某事。從時間點上看,在對手采取行動前發出威脅是威懾,在對手采取行動后發出威脅是威逼。*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95.從性質上看,威懾有一定消極性和被動性,而威逼則具有較強的主動性和進攻性。*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pp.69~72;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Simon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Westview Pres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94; Lawrence Freedman ed., Strategic Coercive: Concepts and Ca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轉引自陳東曉:“對后冷戰時期美國脅迫外交的一種理論分析”,載沈丁立、任曉主編:《現實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第183~188頁。威逼又分為脅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又稱為強制外交)和訛詐(blackmail),其中前者是迫使對手停止或取消(stop and/or undo)已經開始和實施的行動,后者則是逼迫對手發起或實施一個新行動。*結合亞歷山大·喬治和羅伯特·阿特的研究,脅迫外交可細分為四種類型:一是迫使對手在尚未完成目標的情況下停止正在開展的行動;二是迫使對手取消某項已采取的行動;三是迫使對手在政府和政權方面做出改變;四是迫使對手不要重復它已經采取的行動。參見錢春泰:“美國與強制外交理論”,《美國研究》,2006年第3期,第51頁;劉欣:“強制外交概念與手段小議”,《國際研究參考》,2016年第6期,第9~10頁。相較而言,訛詐又比脅迫外交更有進攻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認為,脅迫外交與軍事密不可分,威脅使用武力或使用有限武力是脅迫的必備手段,其他手段還包括經濟制裁、外交孤立等非武力性脅迫,以及說服、有條件和解等非脅迫性手段。*劉欣:“強制外交概念與手段小議”,《國際研究參考》,2016年第6期,第10~12頁。
威懾和脅迫在國際關系中屢見不鮮,現代意義上的脅迫外交是冷戰的產物。與通過武力擊敗對手及迫使對手屈服相比,成功的脅迫能夠以較低成本實現政策目標,因而“非常具有吸引力”。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肯尼迪政府通過威懾和脅迫相結合的戰爭邊緣政策,迫使蘇聯撤回了部署在古巴的導彈。1994年海地危機期間,通過小規模入侵行動,美國兵不血刃地迫使海地軍政府放棄政權。美國是二戰后實施脅迫外交最頻繁的國家,但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絕非易事。美國戰略家羅伯特·阿特表示,除非決策者做好使用武力或解套的準備,否則不要輕易發起脅迫外交。一旦失敗,決策者將面臨是戰爭還是后退的艱難抉擇:選擇后退不僅丟面子,還削弱今后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選擇動武則代價慘重。*Robert Art and Patrick Cronin,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3, p.7.冷戰后期及冷戰結束后,針對一些敵對的中等強國或小國,美國自恃有能力脅迫對手屈服,但其發起的脅迫外交失敗多于成功。*美國學者總結了1990~2003年美國實施脅迫外交的8個案例,認為成功率僅20%左右。如1990~1991年海灣戰爭前,美國未能脅迫伊拉克軍隊撤出科威特;1998~1999年,美國和北約也未能脅迫塞爾維亞軍隊退出科索沃,而是通過持續的空襲達到目的。See Robert Art and Patrick Cronin,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3.
隨著全球化發展和國際經濟相互依賴的增強,美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意愿降低。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耗資巨大卻未能實現最終的軍事和政治目標,再次證明征服性和占領性戰爭的困境。同時,技術擴散使更多國家掌握了精確制導、巡航導彈等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陸權大國在與海權大國的博弈中至少在近海具備了相當的主動權,進一步遏制了美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意愿。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厭戰情緒的高漲,對戰爭的態度更為謹慎,明確降低了武力在實現國家政策目標中的作用。在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提出和推動的“巧實力”外交,即力圖在不直接動武的情況下,綜合運用經濟、軍事、文化、網絡等工具“重振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被稱為“不做蠢事”的奧巴馬主義,一個重要特征是更積極地使用軍事威懾和非武力性脅迫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參見 Jeffer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April 2016,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上網時間:2016年8月15日).蘭德公司的一篇報告認為,相較于硬實力和軟實力,“脅迫力”(the power to coerce),即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應對敵手的戰略應該而且正受到更大重視。該報告認為,在使用武力的成本太高,中國和俄羅斯都在使用脅迫手段的情況下,美國應該充分利用在金融、貿易、網絡、外交等領域的優勢,更頻繁地使用經濟制裁、外交孤立、支持對象國反對派、網絡攻擊等手段,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參見 David C. Gompert and Hans Binnendijk, The Power to Coerce: Counting Adversaries Without Going to War, Rand Corporation, 2016, pp.2~9; pp.35~38,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000/RR1000/RAND_RR1000.pdf.(上網時間:2016年8月20日)在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過程中,美國官方和學者在指責中國對日本和菲律賓等鄰國實施脅迫的同時,認為美國也在對中國實施威懾和脅迫。*參見 David Lampton, “ The US and China: Sliding from Engagement to Coercive Diplomacy”, August 4, 201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63-us-and-china-sliding-engagement-coercive-diplomacy; Bonnie Glaser, “China’s Coercive Economic Diplomacy”, July 25,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07/chinas-coercive-economic-diplomacy/; Ben Connable, Jason H. Campbell and Dan Madden, Stretching and Exploiting Thresholds for High-Order War: How Russia, China, and Iran Are Eroding American Influence Using Time-Tested Measures Short of War, RAND Corporation, 2016, pp.17-23,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000/RR1003/RAND_RR1003.pdf.(上網時間:2016年8月20日)
二、美國對華威懾與脅迫的主要舉措
冷戰期間和冷戰后,威懾與脅迫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內容。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核訛詐、1996年臺海危機期間派遣兩個航母戰斗群試圖迫使中國停止威懾“臺獨”勢力等,則是脅迫戰略的典型運用。奧巴馬政府沒有對華實施以武力威脅為核心的脅迫外交,而是使用了軍事威懾和非武力性脅迫,主要表現在一些熱點問題上對華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
第一,美國在釣魚島、南海防空識別區和黃巖島等問題上對華實施了軍事威懾。軍事威懾是冷戰后美國對華防范政策的一部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威懾,主要針對中國強勢維護領土主權的行為。日本宣布對釣魚島的所謂“國有化”后,為威懾中國不要在釣魚島采取軍事行動或其他控制釣魚島的舉措,包括奧巴馬總統、克里國務卿在內的美國政府高官多次表示,《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于“日本擁有施政權的所有地方,包括釣魚島”。針對中國可能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ADIZ)的傳聞,時任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麥艾文稱,美國不接受也不承認中國所設立的(東海)ADIZ,中國設立新的ADIZ將是“挑釁且破壞穩定的行為”,“將導致美國改變在區域的軍事部署”。*“U.S. ‘Could Change Military Posture’ if China Sets up Second ADIZ”, Feb. 1,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2/01/national/u-s-could-change-military-posture-if-china-sets-up-second-adiz/#.V4CTdUt961s.(上網時間:2016年8月10日)麥艾文并未明言威脅動武,但“改變軍事部署”構成一種模糊威懾。南海仲裁案結果出來之前,為威懾中國不對菲律賓采取“報復”措施,如劃設南海ADIZ、在黃巖島進行陸域吹填、劃定南沙島礁的領海基線或專屬經濟區等,美軍派兩個航母戰斗群在西太平洋地區活動,數艘艦艇在黃巖島和中國所控制的南沙島礁14~20海里范圍內巡邏。美國防長卡特威脅稱,一旦中國在黃巖島有所行動,美國和地區其他國家將采取應對行動,這“不僅將導致局勢緊張,還會使中國孤立”。*Ashton Carter, “Meeting Asia’s Complex Security Challenges: Q&A”, June 4, 2016,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6-4a4b/plenary1-ab09/carter-qa-2e98; Bill Gertz, “Pentagon Warns of Conflict Over Chinese Buildup on Disputed Island”, April 29, 2016,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pentagon-warns-conflict-chinese-buildup-disputed-island/.(上網時間:2016年8月20日)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專家葛萊儀則呼吁對中國劃設“紅線”,將黃巖島納入《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的適用范圍。*Simon Denyer, “Storm Clouds Gather over South China Sea ahead of Key U.N. Ruling”, April 27,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storm-clouds-gather-over-south-china-sea-ahead-of-key-un-ruling/2016/04/27/fd5d1c7b-d425-4567-b225-921c7ee1ffba_story.html.(上網時間:2016年8月25日)
第二,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石油勘探和陸域吹填實施了外交壓力和軍事脅迫。為阻止中國正在開展的行動,即迫使中國“停止相關行為”,美國不僅發出了脅迫的威脅,還使用了脅迫手段。對“海洋石油981”鉆井平臺實施的“中建南”項目,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稱,各國應通過協議“自愿凍結”此類“挑釁性行為”;美國參議院通過第412號決議案,敦促中國立即將鉆井平臺和護航船只“撤離”南海海域,“恢復南海原狀”等。*決議案同時稱,上述決議不應被解釋為宣戰或授權動武。參見 “S.Res.412 - A Resolution Reaffirming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ly Lawful Uses of Sea and Airspa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for the Peaceful Diplomatic Resolution of Outstanding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and Disputes”,113th Congress (2013-2014),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3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412.(上網時間:2016年9月10日)針對中國對所控南沙島礁的陸域吹填,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邁克爾·福克斯提出“三凍結”建議,即各方不再“奪取島礁與設立前哨站、改變地形地貌現狀、限制針對他國的單邊行動”;*Michael Fuchs, “Remarks at Fourth Annual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July 11, 2014,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4/07/229129.htm.(上網時間:2016年9月10日)防長卡特敦促相關聲索國“立即并永久中止”填海造地活動;*“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Joint Base Pearl Harbor, Hawaii, May 27,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75/us-pacific-command-change-of-command .(上網時間:2016年9月20日)國務院副發言人馬克·托納則提出“三停止”,即停止“填海造地、新建工程、對前哨地點的進一步軍事化”。*Mark C. Toner, “Daily Press Briefing”, August 6, 2015,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5/08/245764.htm.(上網時間:2016年9月20日)在實施脅迫的過程中,美國采取了三種手段。一是單邊外交施壓。除對中國提出明確要求外,美國官員,包括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國務卿克里、時任防長哈格爾和參聯會主席登普西、國務院和國防部發言人等,對中國維權活動使用的語言均是攻擊性和貶損性的。如稱中國的舉動有“挑釁性”,“無助地區和平與穩定”,美國對此“嚴重擔憂”,且反對“任何國家用恫嚇、脅迫或威脅動武”等手段推進自身主張。二是試圖利用小集團或多邊場合孤立中國。美國推動七國集團發表聲明,強烈反對任何一方試圖“單方面以恫嚇、脅迫或動武手段堅持其領土或海洋權益聲索”;*“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Maritime Security”, April 11, 2016, Hiroshima, Japan, http://www.mofa.go.jp/files/000147444.pdf(上網時間:2016年9月12日)美日澳三國防長對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嚴重關切”。*“Japan-U.S.-Australia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May 30,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Releases/News-Release-View/Article/605538/japan-us-australia-defense-ministers-meeting-joint-statement.(上網時間:2016年9月20日)美國防長卡特還利用第15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污蔑中國筑起“自我孤立的長城”,試圖占據道德制高點、拉攏地區國家孤立中國。三是實施軍事脅迫。美國軍艦、轟炸機以所謂“航行自由”或“誤闖”為由,進入中國相關島礁12海里,試圖以炫耀武力、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脅迫行動”挑戰中國的主權和專屬性管轄權。
第三,美國在網絡安全和防擴散問題上對華實施了有限的經濟制裁并威脅升級制裁。“斯諾登事件”表明,美國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強大情報偵察和搜集能力,對別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的窺探無出其右。但在美國看來,中國“通過政府支持的網絡行動”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秘密和知識產權,不屬于傳統情報活動且“必須停止”。為迫使中國接受美方要求,美國先后對華采取了外交施壓、司法起訴和經濟脅迫。為提高經濟脅迫的可信性,美國小試牛刀,2015年1月以朝鮮對索尼影業發動網絡入侵為由,對朝鮮實施了新制裁。2015年4月,奧巴馬簽署行政令,稱一旦美國重要基礎設施和計算機系統遭到網絡攻擊導致嚴重損失,總統將宣布國家進入“緊急事態”,授權對其他國家的個人及組織實施制裁。同年9月,美國官方釋放了準備制裁“參與竊取商業機密”的中國個人和實體的信號,以迫使中國“停止其涉嫌從事的、通過網絡從美國機構竊取商業和經濟情報的活動”。*Ellen Nakashima, “U.S. Developing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over Cyber Thefts”, August 30,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administration-developing-sanctions-against-china-over-cyberespionage/2015/08/30/9b2910aa-480b-11e5-8ab4-c73967a143d3_story.html; Tal Kopan, “President Obama Talks Tough on China Cyber Sanctions ahead of State Visit”, http://edition.cnn.com/2015/09/16/politics/president-obama-china-white-house-sanctions/index.html.(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在防擴散問題上,為強化對伊制裁促其重返談判桌,奧巴馬政府一方面憑借國內法先后制裁了珠海振戎、昆侖銀行等中國公司,一方面勸說沙特等國提高對華石油出口,并通過給予中國豁免的方式誘壓中國予以配合。2016年1月6日和2月7日朝鮮分別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及發射“光明星4號”衛星后,奧巴馬總統2月18日簽署了對朝鮮更嚴厲制裁的法案,其包含的“二級制裁”條款主要針對與朝鮮有大量鋼鐵、煤炭和礦石貿易的中國企業,目的是迫使中國同意加大對朝制裁。*“H.R. 757: North Korea Sanctions and Policy Enhancement Act of 2016”,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4/hr757/text/enr; Michael Gershberg and Fried Frank, “U.S. Enacts North Korea Sanctions Legislation”, http://www.friedfrank.com/siteFiles/Publications/WorldECR_Gershberg_March2016.pdf; Geoff Dyer and Charles Clover, “US and China agree North Korea sanctions”, Feb.25,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7b8c012-dba9-11e5-98fd-06d75973fe09.(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美韓還決定推動在駐韓美軍基地部署“薩德”系統事宜,以增加對華戰略壓力。
美國對華強制行為的增多,是中美關系趨于緊張的表現。回顧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臺是個關鍵節點。該政策觸發了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的升級,迫使中國在能力增強的基礎上升級維權行動,而相關行為又招致美國的強勢應對。另外,從中美在網絡和伊核等問題上的博弈看,美國對華強勢政策并未局限在地緣政治領域。當前,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尚在組建執政團隊,其外交安全戰略及對華政策大方向尚未可知。不過,通過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顧問的言論,大致可看出幾分端倪。從個人層面看,特朗普崇尚實力,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對外輸出美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傾向,其世界觀更接近現實主義。從其團隊看,特朗普的“圈內人”信奉“以實力求和平”,批評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過于軟弱,支持增加軍費以建設更強大海軍。*Peter Navarro and Alexander Gray,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Nov.7,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0日)從黨派背景看,特朗普雖非傳統的共和黨人,但作為共和黨總統,將在相當程度上被該黨青睞軍工集團和鷹派國防政策的傳統所塑造。*參見 “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 Republican Platform 2016,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1]-ben_1468872234.pdf.(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0日)從未來對外戰略重心看,特朗普嚴厲打擊“伊斯蘭國”,敦促日本、韓國等盟友承擔更大防務責任,修復美俄關系等思維,并不意味著美國會放松在亞太的戰略投入。鑒于美國打壓崛起國的戰略傳統、共和黨軍事鷹派色彩、特朗普經濟上對中國的強硬等,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將維持或者至少不會減少對威懾和脅迫戰略的運用。
三、美國對華威懾與脅迫的效果評估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軍事戰略報告,將朝鮮、伊朗、“伊斯蘭國”、俄羅斯和中國視為五大挑戰。對于這些美國眼中的威脅和挑戰,奧巴馬政府采取了從使用武力、威懾到脅迫的政策。美國對“伊斯蘭國”持續進行軍事打擊,對敘利亞政府實施了脅迫外交,對俄羅斯使用了軍事威懾和非武力性脅迫手段,對朝鮮加大了脅迫力度,對伊朗則實施了脅迫與談判相結合的戰略。綜合美國政府和戰略界主流的評估,美國對伊朗的政策較成功,因為制裁和外交壓力是促使伊朗經濟惡化、領導層生變及伊核協議最終簽訂的重要原因。*Hassan Hakimian and Toni Johnson, “ How Sanctions Affect Iran’s Economy”, May 23, 2012, http://www.cfr.org/iran/sanctions-affect-irans-economy/p28329; Kenneth Katzman, “Iran Sanctions”,May 18, 2016,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S20871.pdf(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Zachary K. Goldman and Elizabeth Rosenberg,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 The New Face of Financial Warfar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6, pp.5-6,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_Economic_Statecraft_061115_v02.pdf.(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對敘利亞的脅迫外交看法兩極,一些人認為奧巴馬政府在敘利亞政府“跨過紅線”后未采取軍事行動,嚴重損害了美國的聲譽。另外一些人認為美國的軍事壓力和俄羅斯的提議最終移除了敘利亞1300噸化武,取得了軍事打擊未必能取得的效果。*Pamela Engel, “Former US Defense Secretary: Obama Hurt US Credibility When He Backed down from His Red Line on Syria”, Jan. 26,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obert-gates-syria-red-line-obama-2016-1; Derek Dhollet, “Obama’s Red Line, Revisited”, July 19, 2016,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7/obama-syria-foreign-policy-red-line-revisited-214059.(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5日)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在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過程中,美國沒有發出軍事威懾和軍事脅迫,而是發起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奧巴馬政府認為,美歐的壓力雖未能阻止俄羅斯向烏克蘭“分裂分子”提供軍事支持,但懾止了俄進一步的“侵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普京的戰略考量,并削弱了俄羅斯經濟實力和軍事潛力。*“Remarks by Celeste Wallander,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Senior Director fo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on U.S. Policy”, June 26,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6/26/remarks-celeste-wallander-special-assistant-president-and-seniorcy on Russia.(上網時間:2016年10月20日)對朝鮮的脅迫效果與對俄類似,雖未能迫使朝鮮凍結核計劃或放棄核武,但削弱了朝鮮并使其更孤立。
至于美國對華威懾的效果,中美可以而且一定會有不同評估。威懾效果難以衡量,在于威懾的目標是懾止對方沒有從事的行為。威懾發起方可以認為成功地嚇阻了對方,而目標方則可以稱原本就無意開展某項行動。例如,美國可以認為,中國迄今沒有劃設南海ADIZ或在黃巖島填海造地,是自己實施威懾的結果。中國完全可以不理會美國的說辭,聲稱做與不做、何時做均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不受美國影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中國會根據空中安全受威脅的程度決定是否劃設南海ADIZ。*“2016年2月26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43501.shtml.(上網時間:2016年10月25日)至于在南沙島礁部署防御性武器、宣布相關島礁的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等問題,中國都會堅持以我為主、于我有利的原則。可以說,威懾的特征有利于雙方保住面子,達成某種程度的戰術穩定,雖然這種穩定是臨時和脆弱的。
美國對華脅迫,涉及脅迫目標的選擇、雙方實力和意志的較量、退出和解套戰略等,評估更難。這其中涉及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因果關系困難的問題。只有脅迫方發出的要求和最終結果之間有直接因果聯系,脅迫才算有效,但建立這一聯系并不容易。例如,在“海洋石油981”南海勘探問題上,中國外交部7月16日證實“中建南”項目“完成作業”,這離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走鉆井平臺僅過去6天。美國可以認為施壓奏效,中國則表示在臺風多發季節之前完成作業,已“按計劃順利取全取準了相關地質數據資料”。*“‘海洋石油981’鉆井平臺順利高效完成西沙中建島附近海域作業”,2014年7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7/15/c_126757221.htm.(上網時間:2016年12月1日)另外,越南的行為增加了評估的復雜性。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美國發出制裁威脅與中美達成共同打擊網絡犯罪的共識相隔十余天。美國一些學者認為脅迫起到效果,美國網絡安全公司的報告也稱,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自雙方達成協議后大幅下降。*Scott Warren Harold, “The U.S.-China Cyber Agreement: A Good First Step”, http://www.rand.org/blog/2016/08/the-us-china-cyber-agreement-a-good-first-step.html;Adam Segal, “What’s the Future of Chinese Hacking?”, July 30, 2016, https://motherboard.vice.com/read/future-of-chinese-hacking.(上網時間:2016年8月10日)不過中國可以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就反對網絡攻擊和網絡商業竊密,自己也一直是網絡攻擊的受害者,推動構建合作共贏的中美網絡安全執法合作機制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中國2011年和2012年曾減少從伊朗的石油進口,2016年3月2日支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270號決議,對朝鮮實施了“史上最嚴厲制裁”,但中國的決定是基于防擴散責任、穩定中東和朝鮮半島局勢、穩定中美關系等多種因素,很難說美國的“二級制裁”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二,脅迫的能力、意圖和意志問題。與脅迫能力相比,博弈方意志的較量、對脅迫后果的評估影響著雙方的行為。在對南海所控島礁的陸域吹填過程中,中國沒有理會美國要求停止施工的要求。施工過程中,美國派偵察機進行了挑釁性的抵近偵察和騷擾,但沒有發出動武威脅,美方艦機也沒有對中國作業船只實施攔截和沖撞。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2016年2月在五角大樓表示,以武力阻止中國填海造地和實施軍事化并非美國的首選措施,“美軍能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但我認為你不會鼓勵我們以那樣的方式去阻止中國。但使用軍力是總統掌握的各種選項之一。”*“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Briefing by Adm. Harris in the Pentagon Briefing Room”, Feb. 25, 2016, http://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673426/department-of-defense-press-briefing-by-adm-harris-in-the-pentagon-briefing-room.(上網時間:2016年10月20日)美國可能認識到,一旦采取過激措施,必將觸發中美軍事對峙甚至沖突,而這是現階段美國不愿看到的。筆者接觸到的一位美國戰略家坦言,除非做好與中國沖突的準備,美國沒有能力阻止中國。實際上,在自己的領土上施工,中國有比美國更堅定的意志,一旦發生軍事對峙,中國退讓的可能性極低。而一旦美國實施了脅迫外交又敗下陣來,美國的信譽就將蒙羞。在實際操作中,美國實施了所謂的“成本增加”戰略,即通過對中國維權行為的頻繁曝光、強化與盟友和伙伴的軍事合作、推動東盟對華施壓等,試圖讓中國在外交和戰略上付出更大代價。*Patrick M. Cronin, “Countering China’s Maritime Coercion: How to Impose Costs on Coercion, Deter Intimidation, and Offset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eb. 2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2/countering-chinas-maritime-coercion/; 趙明昊:“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對華制衡的政策動向”,《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1期,第33~34頁。
第三,雙方外交資源的利用問題。博弈方均需要壯大自己的朋友圈,以在實力、道德、政治和外交上占據優勢,爭取主動。在南海問題上,美國除依賴日、菲、澳等盟國外,還積極拉攏東盟和印度,同時利用七國集團和歐盟發聲。中國則從俄羅斯、巴基斯坦、非洲國家尋求支持,并利用上合組織發聲。這在南海問題是雙邊解決還是多邊解決,是通過仲裁解決還是談判解決等方面表現突出。在外交孤立與反孤立的斗爭中,第三方提供何種支持、支持的力度和持久性等,都會影響脅迫效果。在與中國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一些國家的領導人表態支持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例如,在中國和塞爾維亞簽署的聲明中,中塞雙方一致認為,在南海問題上,應根據雙邊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由直接當事方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和平解決領土和海洋爭議問題。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塞爾維亞共和國關于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2016年6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3365.shtml.(上網時間:2016年9月10日)這顯示如同對待臺灣問題一樣,中國愿意付出政治和外交資源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顯示了維護主權的堅定決心。支持美國立場的國家外交表態是一回事,會否在局勢升級后給予美國行動上的支持是另一回事。即使這些國家為美國提供行動上的支持,能否長期持續也存在疑問。
總體來看,美國對華脅迫的力度,不及美國對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脅迫力度。迄今美國沒有對中國實施規模較大、措施嚴厲的經濟制裁,這與中美關系競爭與合作交織及中國應對脅迫的能力有關。中美經濟深度相互依賴,一方實施大規模制裁,必將遭到另一方的嚴厲報復。面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前景,美國在動用制裁工具上選擇了謹慎。在南海等問題上,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發展中大國,作為合理、合法維護國家主權的政治實體,有強大的資源和堅定的意志應對和化解美國的壓力。中國的朋友圈龐大,尤其是努力與東盟構建命運共同體,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政治立場相近,這使中國在與美國的法律戰、輿論戰和外交戰上并非總是處于下風。
四、中國的應對思考
隨著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深化,尤其是地緣政治矛盾的進一步凸顯,兩國戰略回旋余地都在縮小。當前的東亞,朝鮮頑固推動核武的實戰化逼近美國的“紅線”、美韓決意部署嚴重損害中國戰略安全的“薩德”系統、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日本安倍政府持續推動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戰略、美軍艦機頻繁進入中國島礁的領海等,預示著中美可能面臨更多的“近身博弈”。對于美國加碼的威懾和脅迫,中國既可以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待時日,也可以運用底線思維與美國針鋒相對,以斗爭維護利益。
第一,中國需要在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上展現堅定意志,但可以后發制人。在臺灣、釣魚島、南海等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中美博弈在能力和意志兩個層面展開。在中美能力差距仍然很大的情況下,意志較量更為重要。中國的戰略意志越堅定,美國對華實施威懾和脅迫時就會更謹慎。如果美國政府更寬泛地解釋《與臺灣關系法》,并以對臺“六項保證”為準繩大幅提升美臺政治和安全關系,*Peter Navarro, “America Can’t Dump Taiwan”, July 19,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cant-dump-taiwan-17040.(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5日)促使蔡英文在“臺獨”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國需要援引《反分裂國家法》展開具體行動,以震懾美臺。如果日本安倍政府在釣魚島或發展對臺關系上采取嚴重的挑釁性舉措,中國可以不惜測試《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迫使美國對日施壓。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和航道安全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但如果其他聲索方和美國大演雙簧挑戰中國底線,中國可以不懼美國的警告在所控島礁部署更多的防衛性武器。對于美國的威懾和脅迫,中國要做好承受壓力和付出代價的準備,相關的較量不僅關乎主權,更事關中國崛起和在亞太及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第二,廣交朋友,并做好與美國打“外交持久戰”的準備。美國兩黨的一些政策精英視中國為長期的戰略競爭對手,這種思維已經影響甚至主導美國對華政策。*“Remarks by Secretary Carter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May 25, 2016, http://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781499/remarks-by-secretary-carter-at-the-us-naval-war-college-newport-rhode-island.(上網時間:2016年7月10日)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中美外交博弈已超出地區層面,越來越在全球舞臺上展開。近年來,東盟、七國集團和歐盟已成為美國外交動員的對象。對美國開展多邊外交孤立中國的意圖和能力,中國要心中有數。為維持在相關議題上的“志愿者聯盟”,美國可能通過制造緊張局勢凝聚小集團。不過,開展集體脅迫是一個需要持續付出資源的過程,難以持久。中國對此要有耐心,以拖待變,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擊破美國的企圖。在強化中俄關系和提升上合組織影響力的同時,中國要致力于做好東盟、歐盟、阿盟和非盟的工作。可以說,中國朋友圈的人氣越旺,美國發起對華外交戰的動力就越小。
第三,增強反制和報復能力,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如果無需付出成本就可以成功實施脅迫,美國很難進行政策反思并改弦更張。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力量,未來將不同程度地體現在美國對華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經貿在中美關系中的潤滑劑或壓艙石作用減弱,華爾街、跨國公司等利益集團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影響力相對下降,似乎是大勢所趨。對于美國極端的貿易保護措施,中國在訴諸世貿組織的同時,要敢于和美國打貿易戰。對美國頻繁使用經濟或金融制裁實現外交目標的政策,中國也需要積極探索反制措施。*Zachary K. Goldman and Elizabeth Rosenberg,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 The New Face of Financial Warfar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6, pp.5-6.經濟戰是雙輸的游戲,但只有一定規模的經濟戰才能迫使對方謹慎,并反過來限制經濟戰的規模。
第四,增強對美國的軍事威懾力。美軍在釣魚島、黃巖島上對中國的威懾,是以其在亞太前沿部署及盟國軍力為支撐的。美國落實“空海一體戰”構想、推動“第三次抵消戰略”,力圖抵消中國反干涉或“反介入”的能力,增強美軍威懾力及威懾失敗后贏得戰爭的能力。反制美軍威懾的方式,主要靠提升己方威懾力,包括核威懾和常規威懾。在強化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揮地緣優勢、善用創新技術的同時,中國仍需不斷提升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和核潛艇的生存力,找到并持續發展自己的戰略凈優勢,以形成核心軍事競爭力。*童真:“美第三次‘抵消戰略’述評”,《光明日報》,2016年3月2日;郭瑞鵬:“第三次‘抵消戰略’的困境,《軍事文摘》,2016年第7期,第6頁。中國的目標不是與美國開展軍備競賽,而是不斷增加美軍介入的成本,平衡乃至削弱其威懾力。針對美軍維持其安全承諾可信性的言行,中國既可避其鋒芒,也可適時針鋒相對。如果選擇后者,就要更嫻熟地運用威懾和危機管理的理論,并借鑒美國的經驗與其斗智斗勇。
第五,發展自己,增強國內應對危機的能力以提高戰略韌性。大國博弈既在外交,也在國內。激烈博弈常演化為大大小小的危機,誰后院更穩,誰能獲得更大的國內支持,誰的勝算就更大。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實施了大量威懾和脅迫,在政策協調、力量運用、信息傳導、輿論塑造、國內動員等方面經驗豐富。在經歷30多年的和平后,中國國家安全決策機制、軍情部門的能力、社會大眾的承受力等既面臨考驗,也面臨重塑的機會。中國政府需要在維護國內穩定上投入更多資源,包括加強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更完善開明的民族政策等;民眾也需要增強心理承受力,習慣中美關系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新常態。相應地,中國的智庫也需要對全球化時代大國的威懾和脅迫戰略開展更多研究,為國家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以備不時之需。
鑒于中美經濟深度相互依賴和非對稱的核恐怖平衡,中美爆發大規模沖突的可能性不高,觸發激烈的外交戰和嚴厲的經濟制裁均是小概率事件。但國際政治充滿偶然性和戲劇性,重大的戰略變化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現出來。在西太平洋地區,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意志和美國維持安全承諾的決心均不容低估,因第三方挑起事端引發中美激烈博弈的可能性也不容低估。在涉及主權、榮譽、領導權等問題上,中美都可能做出誤判,兩國之間軍事威懾升級、外交爭奪加劇、經濟制裁“落地”的風險在上升,且不排除圍繞一些重大問題發生軍事脅迫的可能性。作為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避免戰略碰撞,防止亞太秩序和本已困頓的全球化進程遭受嚴重沖擊,符合中美和地區國家的利益。管控中美分歧和矛盾的一大途徑,應是加強戰略溝通和建立危機規避機制,以及在博弈中極為謹慎地運用威懾和脅迫。○
(責任編輯:孫茹)
* 本文得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協同創新中心”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