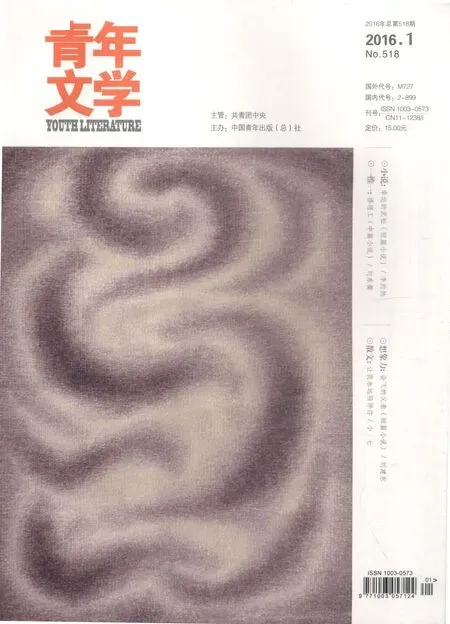關于同題小說與想象力
⊙ 文 / 李 浩
?
關于同題小說與想象力
⊙ 文 / 李 浩
虛構是古老的。文學的最初具有強烈的虛構性質,無論是《山海經》《周書》《荷馬史詩》及古希臘戲劇,虛構根深蒂固,其合理性不辯自明,不容置疑。正如,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強調文學是記憶、生活、歷史片段、閱讀中得來的材料以及幻想和夢的結合體;納博科夫則認為,好的小說都是好神話,大作家本質上是“大魔法師”;而巴爾加斯·略薩更為堅決,他說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說謊者”,文學本質上是在說謊,雖然在說謊的過程中道出的恰是我們一向“遮遮掩掩的真情”。——我們看到,作家們以各自個性的方式強調了文學(尤其是小說)的虛構功能,強調了“想象”在文學中的作用。可以說,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會輕視想象,反而他們會強調想象力是藝術創作的重要“誕生地”,由此,藝術得以獲得生長。
然而,在今天,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或者說那種模仿生活、復制生活,甚至低于生活的現實主義成了許多作家的創作原則,中國小說原創力匱乏與中國文學缺乏想象力的問題也開始顯現,以致有作家與批評家不得不重新為虛構和幻想辯解,以致對虛構的捍衛與強調變成了一個現代性話題。當然,我們強調虛構和幻想時可能更多地強調“虛構的魔法”和“再造一個不一樣的彼岸世界”的創造感。——在這里,我也希望對貌似“模仿著生活”的那類小說中的“想象”成分進行強調。比如說,契訶夫的《裝在套子里的人》中也有想象,否則,那個小職員不會有那么多的“套子”套在身上。這僅僅是一個例子。從生活到小說自然會“經歷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變動”。變動,變動的方法,就歸屬于想象力的一種。——我想,《青年文學》雜志設置這樣一個欄目,將“想象力”進行如此醒目的強調,本意大約是表達對已經前呈的現代性想象的重視,大約是表達對作家“再造一個更有魅力和陌生感的世界”的強調,當然似乎也表達了時下寫作沉溺現實、匱乏想象力的不滿。這,是我的個人猜度。
應《青年文學》編輯陳集益先生的“要求”,我們河北五位寫作者要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會飛的父親》的同題小說,作為這一欄目的開始。而且規定在完成作品之前,我們不許相互溝通創作內容,于是我們會暗暗猜測“別人會寫下什么”,然后“調整”自己不與“他者”趨同,這個創作過程本身就充滿想象力,當然更是對寫作者想象力的考驗。正如,“會飛的父親”必須要學習“飛翔”而且“飛得起來”。它很有趣。我和另四位同行愿意接受這一考驗。在這五篇同題小說中,讀者既可查看我們五位寫作者想象力的不同和對想象力的不同理解,也可見寫作者在想象力運用上的差異以及“再造真實”的區別……我不知道我們的寫作是否合乎陳集益先生要求的“想象”,它們有待檢驗。總之,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不同的“會飛的父親”吧。
(補充說明:我在此次以“會飛的父親”為題的寫作中,先后寫了兩篇風格不同的《會飛的父親》,另一篇將在另一刊物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