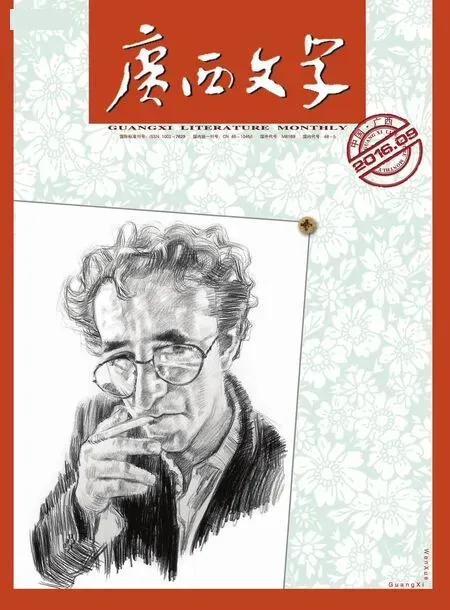散文新觀察之羅南篇
劉 軍/著
曹魏時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首倡“文以氣為主”之說。時隔不久,南朝的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了“氣韻生動”的美學命題。“氣韻生動”之說經過后世藝術家的不斷闡發,形成了古典美學精神的一個重要原點,同時也演變成古典繪畫、書法、音樂的一個美學標準。一個頗堪玩味的事實為,“氣韻生動”之說盡管乘風破浪,卻難以在古典文學(詩學)領域蔚然成風。細細思量之,卻不足為奇,一方面,作為辭章大國,古典時代文的概念多對應文化意義上的文章范疇,其中包含了許多非審美意義上的雜文體;另一方面,即使落定于詩文范疇,“氣韻生動”之說對于史傳體、論說體散文,對于重理趣的詩歌,似乎很難施展開手腳。比較而言,才性、氣質的理論話語能夠恰切地統攝詩文范疇內的各種體式。
本期《散文新觀察》欄目,迎來了廣西作者羅南的《藥這種東西》。作為長達萬言的敘事散文,在接受層面,這篇文章帶給我們最強烈的一個審美效果,即氣韻生動。按說,敘事散文開掘的方向為反映生活的深度、廣度,思想之力,以及細節、場景的駁雜性等因素上,與強調生命律動、情思流暢的“氣韻生動”之說形成了天然的排斥效應。那么,羅南到底依靠什么讓天塹變成坦途?在我看來,“氣韻生動”審美效果的發生來自以下三個要素。首先是敘事節奏的推進,作者的講述從容不迫,內外有序。四伯父作為一個鄉寨的草醫,自身的精神投射力量足夠強大,對他者是職業精神的專注、細致以及不計利害得失的施與,對四伯母則是情深義重,不離不棄,甚至臨終前對待藥物的奇特態度,皆彰顯出其異于常人的一面。作為鄉土靈魂式的人物,他的一生注定跌宕不平。作者在處理這個主題上,并非簡單地將對象異人化,恰恰相反,四伯父在故事架構中一方面是深深地扎根于“我們”之間,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我們”之上。這兩個方面在敘事推進上又構成了一個雙行線,相互呼應,相互支撐,如同琴弦上不同音符的會合,最終抵達一種獨特的韻律。其次是情思的提純處理得尤其漂亮。散文中的親情或者家族敘事,決定其基本品格的不是情感的濃度與真摯程度,而在于情感的提純程度。若距離太近,主體的情感很容易被情感的熱度所熾烤,以至于執情強物。羅南的這篇散文,采取了童年視角與他者視角交相使用的方式,進而獲取了審美距離的完成。在情感的凈化與提純方面,《藥這種東西》讓我想起喬葉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在情感的處理上,皆跳出了親情敘事通常的窠臼,以生命來觀照生命,激發生命本來的顏色,即王國維先生所言的“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基本原則。四伯父只是一個情感投射的基點,其背后則有一個縱深的空間,即鄉土世界中綿延至今的人倫秩序和文化關懷。最后是語言的豐茂。諸多詩性的詞語,具備爆發力的句子,如瀑布般嵌入文本之中,構成了錯落有致的語言景觀。
對照《散文新觀察》第四期推出的李穎的《虛幻的魚骨》,同樣作為家族敘事之一種,羅南的《藥這種東西》為讀者提供了如泉水噴涌般的表達形式。兩者所選擇的不同路徑,也在暗示我們,在找尋“熟悉的陌生人”的旅途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以及這可能性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