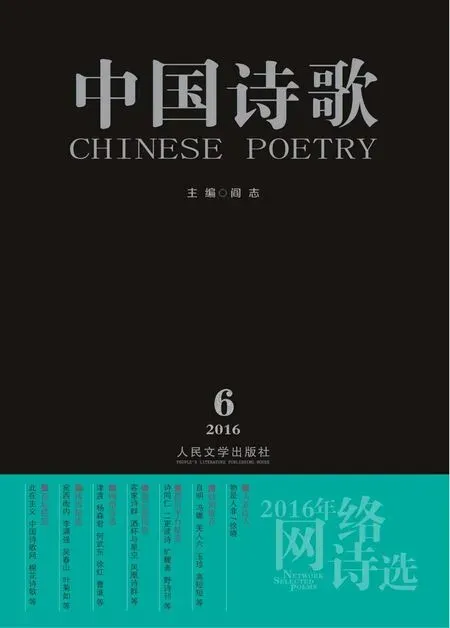蘇陌年的詩
蘇陌年的詩
石頭
黑色的極簡主義。幽閉
他有木紋的皮膚,仿佛已活得足夠漫長
“這一,不,那一”(他開始更隱秘地創造夢境
有時拿數張獸面比較)
他的職業是熱愛女性尸體。
為她們畫眉,打上鮮艷的罌粟
他看過不計其數的死狀(割腕、剖腹
和愛情)
他看過她們已經堅硬的胸部,
想象鏤空的針織衫套上鏤空的骨骼(這一定是
事物喪失的面孔之一)
她們將變成美麗的飛灰
這像初夜一樣珍貴,僅此一次
他仿佛已在蒙蒙細雨的窗外
看到自己被推進火葬場
變成一顆小小的石頭
母親
等炊煙斷了,稻草被野風收割的時候
你會回來嗎
如果不,那就再緩些
再緩些,直到春天把我吹出積雪的樣子
直到夜空
落滿你的骨灰,我的眼睛
我們會跟雨滴重新相愛,就像
和世界重歸舊好
當我們不再年輕
解開草木的禁忌,撬開夜晚的鎖芯
從體內取出一部分的毒液
一部分的同類
再也沒有一支口紅,可以拴住異性的目光
擋住蒼老和貧乳
你不是年輕的妻子,攙扶你的只是一支拐杖
到那時候,沒有人想起你的詩歌
連你的年輕也被遺忘
你開始失憶,像從未活過,從未,從未愛過
甚至我們臉上的皺紋那么深
也只是,虛無的假證明
我是罪無可恕的剽竊者
破體的老屋,夜晚硌手的牙床。光陰的潔白
很快墜落在我們漸漸蒙塵的面頰
我的父親,你曾經的丈夫
已經一無所有
我是罪無可恕的剽竊者,已擁有了他的五官和皮膚
甚至給他一生的勞碌都具備了充足的理由
芒刺在他的肩上不停壓彎腰身,多像你曾經
覆上的嘴唇
——甚至干涸的皺紋,都是相同的
這些年我一直像一只貪得無厭的書包,裝下了所有的親人
他們在里面相認,相愛,惡語相向
最后放任沉默吞并所有的白發和皮囊
他們老了,沒有再打架,爭吵,把精力
放在脫下自己一生樹立起的防備
“他們已經不需要骨骼和健壯的肉體
保護自己的兒女
而愛情,他們已經不再做任何的掙扎”
他們開始允許自己矮小和脆弱,允許我的體內
擺放越來越多的荊棘和潔白的肋骨
它們在里面相互指認彼此的罪行
“親愛的,你所稱的出路
是不是巨大的鏈口
而你背上的十字架
并沒有羅盤的效用”
幽藍與潔白
那時候我們赤腳冰涼
可以在一張床上擠壓彼此的肉體
證明夾竹桃的毒性,你說傷口幽藍
幽藍中陡生的暗紅
老去的胡須幽藍,在幽藍的火中
成為孤獨的根系。嘿,親愛
淬取我自傲的靈魂
請告訴這樣愚蠢的原木,火花的來歷
柵欄在你的身體以外,那么
野蠻就是我們
我們要像野獸一樣原始
當我們懷揣《圣經》念念有詞,我們
為彼此舉行天葬
彼此凝視對方的私密和丑陋
我們還可以托物言志:以潔白的牙齒
和我們不染塵垢的骨架
你選擇四月,選擇遺棄春天
我看到枝頭有越來越多的銀河衰竭
糧倉中的玉米開始在地底居住,就讓我來時
屬于天空,歸去屬于土地
魁梧的壽衣被金色的陽光雪藏,馬齒莧
被年輕的風吹紅雙眼。四月
我看到黎明歸屬黎明,月光的肉體腐朽
為何地面有墮落的面孔,為何春穿越柳巷,發出鈍痛的響聲
就像你所撫摸到的存在,只剩
繁復的水面
所有的閃電,今夜請你跟我促膝長談
談男人
和女人,接連流產的春風。四月,請你
憑空捏造梨花的乳房,請你
告訴它成熟,告訴一顆果實安穩的內心
我愛你(組詩)
我們流動的姿勢就已經是愛情
藍雪是一種清澈的花,天空的使命
導致它沉重。在風里不停徘徊
晃啊晃,晃啊晃,就晃疼了一滴露珠
她禁不住這樣的純凈。海還是河
難以篡改濫竽充數的部分,夢囈
神志不清地擊打著屋檐的水花,波紋里
安睡著原形畢露的隱喻,玉兔潮濕
撲倒一片落花時她才發出低語:我們不能相愛
你有你的清白,我有我的諱莫如深
我們流動的姿勢就已經是愛情。
被夢話放逐也好
你是遼闊無邊的莊稼地,我親愛的
我和孩子,都在你身上發出喘息
磕磕碰碰的田坎遇水即化,蕁麻草包裹成
初生之狀。水流里滲透的根源等待一把
鋤頭剪斷臍帶,獲得新生的方式與死并存
夜晚原野掖好了被子,就以月光的歌喉種一場夢
喂養我的百合啊,霸占我的井口
蝗蟲啃噬四季,野雞翻動苦難,不能
作為屈膝的草,也不要作為諂媚世俗的花朵
只愿意成為一顆小小的石子,被你私有
水滴石穿。千瘡百孔,不過是一種靜默的
永恒得到成全。我愛你,就要挖空心思
就應讓靈魂沉浮在一片光怪陸離里
被風驅趕也好,被夢話放逐也好。
我愛你
我能給你只是幾行情詩,幾日油鹽跟食物的混淆
葷腥是你,乏味是我
早晨在鏡子里可以聽到你胡茬掉落的聲音,下巴就會淡淡地癢
青春期,如水一樣動蕩
我的動蕩,是全世界的水
都會令我想到共同的起源,想到白云分裂出的眼淚,想到閃電與夜空的摩擦,想到呼吸艱難
你的淡藍色褲子
你眸子里遙遠而飄忽的水花
而現在,我更像脫水的植物,像一塊又老又皺的陳皮
像被拋棄的漸弱的雷聲,發出熱烈的呼喊又很快遁于茫茫的無垠
那些不連貫的波段,曾經震耳欲聾
至今無人明白
它們都選擇搖頭
左邊的蘋果,愛著右邊的蘋果
它們可以實現的浪漫
就是一起被成長的大雨淋濕
就是把青澀,都釀制出醇厚的甜
它們很輕
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們捉住
它們命很短
枯葉一死它們就活不長了
它們可以一起落地,然而
它們沒有那么做
風問它們,雨問它們
它們都選擇搖頭
你的潔白泛濫成災
暮色晚矣,破碎的花已被寒氣收割殆盡
到處茫茫然,你的潔白泛濫成災
仿佛不染纖塵。魚鉤
在水下抖了抖,線就抖了抖,我也抖了抖
魚兒肯定凍得厲害,我仿佛懷著善意的初衷
用盡全力,才把它釣了起來,凍瘡跟它一樣
開口哇哇地叫,這是你帶給我的思念
它罪孽深重。提桶,水晃著,垂暮之年
腳步在積雪之上心機深沉,我走遠
它就暈開淚花,磨滅。只有我的滿頭白發
看到了它的消失,天空布滿了陰影
殺魚,卸鱗。我就走入了你的幻象之中
白刀子,白房子,白夜晚
活著
在家鄉,金黃色的野菊花,叫糠垛
我吃著它的顏色,盡量向陽,人間的太陽
并不打算收留野性
收留一枝寂寞,波浪狀的牙齒咬破風聲
所以我,像成千上萬的野菊花那樣
把自己埋進泥土,風一走遠
就像米糠一樣地破碎
我活著,練習遠行,練習脫離堅硬的外殼
練習成為埋沒潔白的白,把舊跡
掛滿山頭。塵封的,死前
會把我灌醉
我活著,把自己曬干,拿身體燒開
眼淚,離別,愛情和信仰
把自己泡成苦茶
一邊死亡,一邊清醒
我活著,正在磨滅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