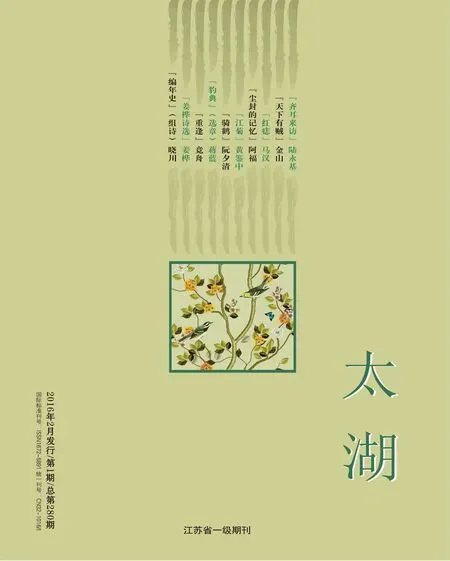守望奇跡
周明珠
?
守望奇跡
周明珠
翻開記憶的相冊,我的思緒被拉回到了2011年的年底。當時的我已經在病痛的邊緣苦苦掙扎了很久很久,精疲力盡的我愈發感覺恐慌,生怕自己再也支撐不住。我側躺在床上,雖然已是深秋,但我的額頭依然滲出一粒粒細密的汗珠。人們常用“小鹿亂撞”來形容對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怦然心動,多美好的感覺。可我卻恨極了住在心里的那頭狂亂折磨我的小鹿,自它不請自來,日日不定時地出來作亂折騰我,每日每夜心跳胸悶得喘不上氣,無數次想要把它狠狠地趕走,可每一次都是徒勞,于是我給它起了個名字——鹿妖!
唉,我深深地嘆了口氣。我感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力不從心,右肩肩周炎越發厲害,酸脹麻木,右手的手腕也使不上力,就連簡單的吃飯也不得不改拿勺子,頸椎痛得連頭都抬不起來。有天晚上吃餛飩,我吃得比較慢,媽媽就先去廚房擦灶具。我的頸椎痛得不受我控制地搖晃,右手也無力把勺中的餛飩送入口中,好幾次餛飩都從我的嘴邊掉入碗里,我感覺窒息的胸悶。我不想讓媽媽察覺我的異樣,更不愿讓她親眼目睹我病殃殃的樣子。顧不得是否干凈,放下勺子,直接拿手把餛飩胡亂塞進嘴里,又趕緊拿抹布擦干凈手,裝作一切如常地喊:“媽媽,我吃完了。今天的餛飩好鮮啊!”媽媽見我碗里的餛飩都吃完了,胃口不錯的樣子,滿意地夸我表現不錯。看見媽媽開心的樣子,我含淚笑了:媽媽,我要在你記憶深處留下的永遠是我的笑容。我不禁有些怨怪起老天的不公平,“全身性小兒麻痹癥”剝奪了我健全身體的權利,現在脊椎的嚴重側彎又已經影響到了我體內各個器官的正常發育,致使我日日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病痛的折磨。
我想到了爸媽,又是一陣錐心的疼痛。他們是我最難以割舍的牽掛,特別是我的媽媽。媽媽曾無數次說過她希望我能走在她的前面,她不想把我一人留在這世上,她害怕我會孤單,會沒有人好好照顧我。甚至有時開玩笑,她會說等到哪一天,她老得實在照顧不動我了,就帶我一起離開這個世界。無論如何她都不會留下我一人在這世上任人欺負,因為她不相信有第二個人能像她一樣愛我,照顧我。的確,媽媽是這世上最愛我的人,不會再有誰比她更愛我。同樣的,她也是我最愛的人。我不曾告訴她,假如沒有了她和爸爸,我也失去了活在世上的全部意義。我害怕沒有對他們的依賴,沒有他們陪伴的孤單,更害怕承受失去他們的痛,所以我自私地想要走在他們的前面。可如今當所想的或許將要變成現實,卻無法真正坦然面對,原來“想”和“面對”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境。
我終于明白其實死亡不可怕,而是你有太多無法割舍的牽掛,所不同的是有人無法割舍金錢權利,而我無法割舍的是對爸媽的情感。
我日日祈禱上天能垂憐我,多給我一些時間,可以讓我多陪陪爸媽,然而上天并沒有聽到我的祈禱,那場命中注定的劫難依然避無可避地降臨到了我的身上。2012年當農歷新年的鐘聲響起,迎接我的不是祥和的新年,而是一場生死劫難。
我做了一個夢,有許多我看不清面容的人在我眼前走來走去,我伸出手喊他們,但他們沒有一個人理我。后來,他們靠我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不停地呼喊我:“明珠,快醒醒……明珠,你已經睡了很久了,快醒醒……”我依著喊聲睜開眼睛,眼前迷蒙蒙的一片,白色的燈光照得我眼睛疼,我嘗試閉眼再睜眼努力適應耀眼的燈光。我轉過頭在我左邊的床上同樣是白色的床單和被褥,似乎還躺著一個人,周圍都是白色的。我使勁抬起雙手,原先細如竹竿的雙手此刻腫脹得猶如小饅頭,我渾身插滿了各種儀器的線,只聽身旁有人驚喜地喊道:“明珠醒了,明珠醒了……”還沒等我細細探究這到底怎么回事,我再次昏睡了過去。
等我再次醒來,病床周圍站滿了用欣喜和焦急的眼神看著我的人,他們都穿著一次性隔離服,戴著口罩。媽媽和我的摯友握著我的手,想要說些什么,最后都化作了無聲的眼淚和一句“明珠,別怕!我們都在你的身邊……”看著媽媽憔悴的面容,她的頭上多了好多白發,感覺突然老了好多歲,我心疼地快要窒息。想要開口說些什么安慰她,但嘴里插著呼吸機管,無法正常開口說話,只能在心里一次次喊“媽媽”,眼淚一次次順著眼角滑落。媽媽輕輕幫我拭去眼淚,安慰我不要哭,那些看望我的人看到這樣的情景也都跟著默默流淚。
我心中滿是疑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我拼命想要去回憶,但腦袋暈沉沉的,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后來才慢慢得知我因為呼吸衰竭,二氧化碳是常人的兩倍,在大年夜陷入了昏迷,被爸媽和摯友一起緊急送入無錫第三人民醫院搶救。我的病情已經嚴重到無法用聽診器聽肺音,拍了兩張胸片都無法看清我的肺部紋理。醫生得知像我這樣的情況從未進過大醫院,都大驚失色。短短幾分鐘,我的身上逐漸插滿了“呼吸興奮劑”、“心率穩定劑”、“血壓穩定劑”、“抗生素”、“心臟監護儀”……轉瞬間我枯瘦如柴的胳膊上掛滿各類儀器、插滿針頭。醫生每隔兩三個小時就開出一張病危通知單,一再要我爸媽做好最壞的打算,爸媽和一直陪在他們身邊的摯友都悲痛不已,不愿接受這個現實。與此同時,那些和我平日一同參加公益活動的志愿者朋友們得到我病危的消息后,紛紛趕到醫院探望我。他們通過媒體和網絡呼吁全社會關注我,在無錫城掀起了一股“救救明珠”的愛心熱潮。而我在彌留之際無意識地喊了八個多小時的媽媽,還不忘叮囑媽媽千萬別忘了我捐獻眼角膜的事情,更是感動了無數人。上至政府部門,下至志愿者、社會愛心人士絡繹不絕到醫院安慰傷心欲絕的爸媽,為我籌集醫療費,他們同爸媽一樣,只想把我從死神的手里拉回來。
我的病情一度陷入危急中,重癥監護室的黃偉主任對我會診后要我爸媽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把我送進重癥監護室插呼吸機管搶救,我若能平安度過七十二小時,就有希望醒過來,但按照我的身體狀況,也極有可能因為承受不了壓力而直接走掉;即使把我救活了,將來照顧我也會遠比現在辛苦!有人善意地勸媽媽不如選擇放棄,不要到時人財兩空。媽媽卻堅決地決定把我送進重癥監護室做最后一搏,她相信我那么愛她,一定舍不得拋下她不管,定會為了她醒過來。哪怕將來我只能躺在床上,她也心甘情愿照顧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畢竟我能活生生地陪在她身邊,對她來說就是活著的全部意義。當我即將被送進重癥監護室,心內科的病房擠滿了自發前來看我的志愿者朋友們。他們要一起送我去重癥監護室,為我壓陣,這樣死神就不敢過來把我帶走。浩浩蕩蕩的一群人把我送進了重癥監護室,這一幕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
我在重癥監護室開始了漫長而又飽受煎熬的治療過程。我被送進重癥監護室時已處于彌留之際,基本無自主呼吸,不得不插呼吸機管搶救。我的嘴里插著呼吸機管,臉頰兩邊各墊了一塊紗布,吸收不自覺流出的口水。起初并不覺得十分難受,當機體各功能恢復正常,逐漸感覺口干舌燥,非常渴望能喝水,可按照護理要求,護士是絕不能給我喂水的,一旦水嗆到氣管里后果不堪設想。護士們只能邊安撫我的情緒,邊用沾了水的棉簽涂在我干裂的嘴唇上,好緩解我的干渴。是媽媽每天懇求護士和護工帶給我的一張張充滿愛意和牽掛的小紙條給了我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撐我堅持了下來。就連我的主治醫生黃偉主任都說明珠很堅強,沒有表現出其他插管病人的煩躁,而是非常配合醫護人員的治療。
呼吸機插管半月有余,我的病情始終不樂觀,氧飽和忽高忽低,二氧化碳依然偏高,自主呼吸困難,我的情況已經不適宜繼續做呼吸機插管治療。針對我的病情,黃主任幫我制定了新的治療方案——為我做氣管切開術,再插入氣管套管,使用有創呼吸機輔助我呼吸和排除體內的二氧化碳,等我的病情穩定,各項指標全都達標,到時再考慮封管。
令我想不到的是氣管切開只不過是一個痛苦向另一個痛苦的過度。從年幼起,我經歷了大大小小八九次手術,其中的痛苦是外人難以想象的,手術給我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因此一聽說要做氣管切開術,不免又惶恐不安起來,但轉念一想,或許氣管切開,我就能離康復又近了一步,說不定我很快就能離開重癥監護室,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重回電臺主持節目呢?想到這里,我又對氣管切開后的治療多了幾分期待。五官科的周主任他們準備幫我實施手術的時候,發現我的頸椎側彎,很難找準氣管的所在之處,這無疑給手術增加了難度和危險性。萬一處理不好,就會割到大動脈,情況將會十分危急,并會有生命危險。他們不敢輕易冒這么大的風險幫我動手術。周主任把我的情況以及手術的風險性都如實告訴了媽媽,希望她重新考慮是否還要繼續幫我做手術。
媽媽的決定關乎著我的生死,她又急又懼,不禁渾身冒冷汗,手指冰涼。但她思量過后,依然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因為媽媽始終相信她的女兒舍不得離開她。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害怕,更不知道媽媽在重癥監護室外有多么的糾結,下了多大的決心才簽下自己的名字。媽媽賭的不是我的命,而是她的,因為無論生死,她都會陪著我。因為有這揪心、艱難的選擇,當我的手術順利平安結束,在場所有的人都一臉喜色,如釋重負。當周主任把手術成功的喜訊告訴媽媽,媽媽握著周主任的手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千轉百回,生死攸關之際,幸運之神又一次眷顧了我。
氣管切開有利有弊,氣管切開相當于我又多了一個出氣口,有利于自主呼吸的恢復,還能通過使用有創呼吸機排二氧化碳,但氣管處是敞開著的,細菌很容易侵入造成肺部感染,所以我的病房必須做到無菌,套管開口會生出許多的痰液,得及時吸掉,要不然會堵塞套管,呼吸困難。吸痰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根又細又長的管子通過頸部的套管深入肺部吸痰,時常會引起氣管痙攣,那種痛貫徹我整個身體。可我始終咬緊牙關,不吭一聲,因為我別無選擇,唯有堅強!
在重癥監護室,最難忍受的除了病痛上的煎熬,更多的折磨是來自精神上的。按照規定每天只有下午三點到四點這一小時的探望時間,起初并不覺得有什么,總認為自己很快就能康復,但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病情的反復,不被外人理解的胸悶,加之時常會聽到病友在昏迷中因病痛發出的叫喊聲,冷不丁在半夜熟睡中被家屬的哭喊聲驚醒,盡管醫護人員會幫我關上門,可依然能清楚地聽到,又永遠走了一個人。我每天都緊緊手握搖鈴,盯著白花花的天花板發呆,一點一點地熬時間,那種孤寂和惶恐感愈發強烈,我渴望爸媽能時時陪在自己的身邊,每次他們要離開,我都緊緊拽住媽媽的手,哭著懇求他們帶我回家。我總感覺我的身體里無時不刻不在跳躍著悲傷的細胞,心里似乎填滿了各種各樣訴說不盡的委屈,也越來越無法控制自己的眼淚。
爸媽見我的情緒不穩定,焦急如焚,他們和黃主任商量過后,媽媽最終決定帶我回家休養。媽媽的大膽決定一時激起了千層浪,醫護人員都勸媽媽放棄帶我回家休養的念頭,要知道這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簡單。我的氣管切開,對周圍所處環境的要求非常嚴苛,必須做到無菌,要不然一旦細菌侵入,很容易引起肺部的感染。重癥監護室是無菌病房,回到家里,很難做到真正的無菌。每天都必須換藥、吸痰、做霧化等,媽媽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回到家里,她能處理好這些看似簡單,實際卻非常需要專業素質的活嗎?況且重癥監護室里的醫療設備,對于現在的我來說缺一不可,家里要全部配齊,遠不是那么簡單的……把我帶回家這句話說出口容易,但擺在眼門前的困難不是一丁點。
媽媽并沒有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她說明珠現在病情不穩定,那是因為離開了我,只要讓她和我在一起換個環境,她就能好起來。假如我這個做媽媽的,再不想辦法帶她回家,這孩子可就要瘋了,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她的。需要的醫療設備,我會想辦法全部買齊,沒有錢哪怕我去借高利貸;吸痰換藥、做霧化這些護理工作我會跟護士們學,我工作那會,什么活一學就會,我想這些護理工作也難不倒我。為了明珠,我什么苦都能吃,我要守著她等待奇跡的出現!媽媽對于我的痛苦感同身受,她為了把我“救”出重癥監護室,可謂是熬干了心血。她想盡辦法幫我到處籌錢購買各類家用醫療設備和呼吸機,每天往返奔波跟醫護人員學習吸痰、換藥以及簡單的急救措施,媽媽的言行感動了許多人。
在媽媽的不懈努力下,終于我被“救”出了重癥監護室,帶我回家休養。照顧一個生活無法自理,氣管切開的病人豈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這需要24小時不間斷有人陪護,爸爸只得請了事假在家幫襯著媽媽一起照顧我。最辛苦的是媽媽,不僅白天要圍著我轉,晚上更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她常說自己是帶著耳朵睡覺的,從不敢讓自己進入深睡眠,只要我這邊一有什么細微的“風吹草動”,她立馬警覺地爬起來赤腳跑到我的房間查看情況,看到熟睡中的我安然無恙,她才放心回房間繼續睡覺。
在爸媽精心照顧下,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好,呼吸機脫機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媽媽為了鼓勵我重燃生活的信心,適時讓我坐在輪椅里,打開電腦讓我看網友們給我的留言和為我制作的視頻。視頻中滿臉憔悴的媽媽滿懷期待地扒在重癥監護室冰冷的大門上,透過小小的玻璃窗往里面張望,等待那僅有的一小時探望時間;瘦弱的我嘴里插著呼吸機管,處于深度昏迷中的我對于周遭的一切一無所知……先前只是聽媽媽和朋友聊起我病危時的場景,而通過視頻畫面直面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景,我感覺揪心的疼痛,淚水無法抑制同,一顆顆往下掉。是的,正如媽媽說的那樣,我的生命已經不僅僅屬于我自己,還屬于那些愛我幫我的人。
就在這時,《江南晚報”》的總編輯馬漢老師給我送來了我夢寐以求的電動輪椅,看著嶄新的電動輪椅,更堅定了我努力鍛煉自主呼吸的決心。我一定要把纏繞著我的氧氣管和呼吸機管拔掉,回醫院復診時我要把氣管內的套管拔掉,我要回電臺主持節目,我要開著電動輪椅外出散步,我要用清亮的嗓音喊“爸爸媽媽”……當心里有了這樣一份信念,身體里就充滿了無限的力量。
為了能達到鍛煉自主呼吸的最佳效果,我決定坐起來時不再在套管上戴呼吸機,而是在套管內插入氧氣。當然,使用氧氣遠沒有呼吸機擴張肺部來的舒服,總覺得悶悶的,坐一會額頭漸漸冒汗珠。每當我想放棄的時候,我會閉上眼睛想象自己坐在電動輪椅上自由“行走”的快樂,以此激勵自己堅持再堅持。
功夫不負有心人,從醫院回家休養兩個月后再回三院的呼吸科做復診,呼吸科王旭主任為我細心檢查,并針對我的身體情況制定了適合我的“拔管”方案。2012年6月13日,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王主任順利地把套管從我的氣管內拔掉的剎那,我呼吸平穩,沒有絲毫的胸悶,當我用嘶啞的嗓音喊了聲“媽媽”,我和媽媽都喜極而泣。治療過我的醫護人員都說我又一次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他們保守估計我得兩年左右才能拔管,沒想到我回家僅休養了兩個月就順利拔管了。是父母之愛、摯友之愛以及社會大愛讓我重獲新生,是“愛”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現在的我每天必須按時佩戴無創呼吸機排體內的二氧化碳,而且自重癥監護室出來后,我的雙手便出現了嚴重的功能性障礙,至今沒有痊愈,連最簡單的吃飯都需要媽媽幫忙喂……生活中有許多外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和艱辛,但我并不畏懼,因為有這么多愛我的人在守護我。盡管生活給予我許多的磨難,但我仍然在夢想的道路上艱難跋涉,堅持主持電臺節目、寫作,參與各類公益活動,我要綻放出最美的生命之花!
作者簡介:
周明珠無錫市作家協會會員。身殘志堅,筆耕不輟,發表各類作品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