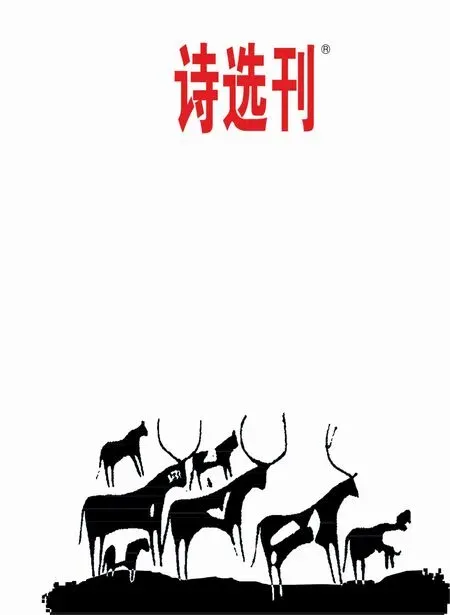薊草花開
吳素貞
薊草花開
吳素貞
低 處
我印象里的親人
如會繡花的小姑婆,和爺爺
老死不相往來的小爺爺
還有半輩子當村長,管著鮮紅族譜的七公
如今,他們都躺下了
我相信,村子老屋的每一片青灰瓦片上
村口每一棵楊楓樹以及
通向山頭田塍小路的每一株野草上
夜晚,都會跳出他們嘮嗑著方言的余音
那濃的,淡的,嘆息的……
村子門樓的房梁上,倒掛的粗大麻繩
記錄著躺在低處親人的最后一程
—— 嗩吶開路,麻繩裹棺,披紅進山
薊草花開
你甚至從沒注意,就在你
經常路過的屋檐下
薊草兩厘米長一葉,三厘米開一花
粉紫的花
有少女開啟絳唇的嫩紅
從屋檐里走出的女人,叫桑
—— 四十年守寡
她不繡花,總是綰著小小的發髻
穿梭田間老巷
這個五月,風撩起她的粗布麻衣
薊花繞檐一剎杳無蹤跡
她站在那兒
瘦干的身姿下有正縮小的影子
竹花開,楝花落
阿婆說,竹子開花,明年就會枯
楝花落了,阿公就又熬過一春
阿公沒看過楝花,瞎了一輩子
他歪靠在南坪嶺的竹林,聽懂了
“簌——簌——”
粉里外露的白,白里透紅的美
阿公說像極第一次進門的阿婆
迎娶的路。楝花的路。
竹花開,楝花落
阿婆說,緣生緣滅,緣生緣滅
他跟著枯萎的竹竿走了八十一年的路
今天,母親拿來一袋野蘑菇
山里,還是那么熱鬧
我可以從北山到南山數出蘑菇的名字
染上方言的蘑菇是沒有毒的
紅的叫紅片片,綠的叫綠片片
白的叫石灰菇,灰的叫錐頂菇
母親像拿出展覽品一樣,從袋子里取出
紅的要曬,綠的要漂
白的要撕開,灰的要趁鮮下鍋……
汲 水
青石的巷子
如往常一樣濕漉漉。天還未亮
井沿的水
“滴答——滴答——滴答”
一滴,草點頭;二滴,井面波未平
三滴,雞犬人聲沸
從村子四面擔著木桶趕來汲水的女人
發鬢低挽,藍底花色的廚裙圍成一臺戲
七個吊桶打水,老井清凌凌,不惱也不怒
給 祖 母
一別十年,奶奶
我們二十年相處的祖孫情份
想起來,曾經
我是多么奢侈的揮霍,不懂節制
我從未想過,那么快的一天
老屋就變得空空蕩蕩
甚至連最后
縈繞在房梁的一聲嘆息
我都沒能趕上
你的兒孫越來越像一群候鳥
你走了后
我們從山外飛回山里
從一個年頭飛到另一個年頭
時間長了,奶奶
你冷清了吧
沒人陪你嘮嗑,看你刺繡
這唯一的遷徙,是不是
讓你晚年的風眼又一次次落淚
奶奶,十年了
我們的心都患上了嚴重的風濕
村里的南風一吹
疼痛就在眼眶里打轉
倒一杯黃酒,添一抔新土
我們立定,深深鞠躬
奶奶,這儀式陳舊而緩慢,你要接受
因為你在,故鄉才在
與父親拆蛇皮袋
“身體上有著相同胎記的人
注定會延續同樣的一件事……”
父親沒有說話。一邊拆著
蛇皮袋的絲帶
一邊示意我把它們歸類扎好
從小到大
父親與祖父拆過無數個蛇皮袋
從小到大
我與父親拆過無數個蛇皮袋
本該丟棄的破袋子,祖父教父親
用拆下的蛇皮絲帶碼繩
甚至用碼好的繩狠抽過父親
幾十年了,父親手上的繭
如碼好的繩般堅韌
繩在母親的吊桶上,在耕地的牛鼻上
在祖父進北山的棺木上……
如今,父親手指痛風
關節越來越彎,碼繩的速度
一年慢卻一年
……我拾掇著絲帶,天已經黑了
一陣風吹來
散碎的絲帶混進柴火,被母親
填進灶膛里,冒出了一陣陣焦煳的味道
秋過籬笆
是的,小村的秋是先在稻子上停留一月
再翻過籬笆進村的
更多時候,它像孩子一樣貪玩
忘記把露水滴在
巷子的狗尾草上
我像蝌蚪一樣順著月色游回
在已是深秋的光景里
蝸居小村,享受生長的快樂
我也關心玉米、稻子的收成
會向秋天回來的親人打聽遠處的消息
薄衫閑讀,我會揣摩
母親菜地的那只蟋蟀
是不是跳進過我枕邊的《納蘭詞》
因為秋過籬笆時
我還翻著金縷曲
它還唱著:君不知,月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