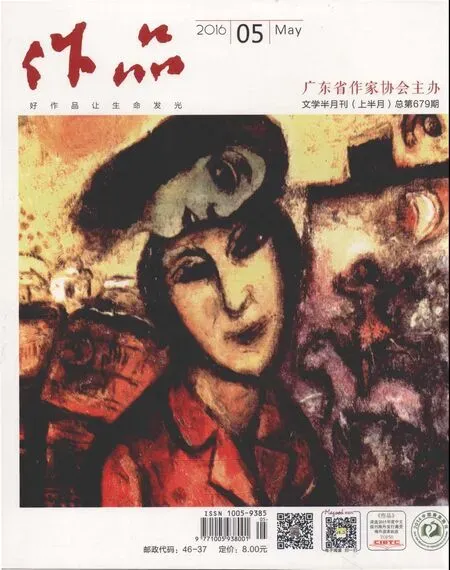101進(jìn)站
文/魏 姣
101進(jìn)站
文/魏 姣
魏 姣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已出版長篇小說《空港手記》、 《愛情看上去很偶然》、 《24小時約會》。
提前內(nèi)退一年后,邱蘭有了新崗位,在四通橋公交站當(dāng)交通協(xié)管員。社區(qū)給她配發(fā)了桔色涼帽,黃色體恤衫和黑褲子,還有一把小紅旗,上面寫著“做文明有禮的北京人”。
四通橋毗鄰兩所高校、一家醫(yī)院和兩個大型商場,高峰時段被喻為“腸梗阻”。這里的車站是個大樞紐,設(shè)有兩個站牌,共8條線路經(jīng)停,早晚排隊候車的人熙熙攘攘。初次上崗,邱蘭面對洶涌的人流不知所措。她默默注視著兩位久經(jīng)考驗的同事。一個是馬小翠,不到50歲的女人,瘦小精干。還有個男的叫孫力,60上下,高大魁梧。他倆的共同點是大嗓門。“101路進(jìn)站,請排隊候車,先下后上!”“遠(yuǎn)途的乘客請往車廂中部走!”“下車的乘客請別忘記刷卡!”渾厚的男音和高亢的女聲此起彼伏,穿透噪雜的車鳴,匯成一張無形的大網(wǎng),讓不堪重負(fù)的車站有了某種約束和秩序。
邱蘭和馬小翠共同負(fù)責(zé)東邊的站牌,不到半個鐘頭,嗓子就啞了。不遠(yuǎn)處的孫力瀟灑地?fù)]揮小紅旗,送走一輛滿滿堂堂的大公交,走到邱蘭身邊,塞給她一枚口哨。這神器還真有威懾力。邱蘭眼見車都要擠爆了,一個小伙子還扒著車門拼命往里拱,喊他也不理會,就鼓足腮幫吹了聲口哨。他回頭張望一下,悻悻地退下來。
吃晚飯時女兒驚呼:“媽你半天兒就曬黑啦!”
邱蘭拉起短袖一對比,小臂就像上了層釉。
邱蘭也沒想到,自己會干起這行兒。她本來滿懷欣喜等著照看外孫。女兒懷孕是她退休生活的最大慰藉。嬰兒床和小衣服都備齊了,她天天研讀育兒大百科。可四個月的時候,胎心停了。醫(yī)生說免疫排斥反應(yīng)遺傳基因異常,她聽不懂。女婿是列車員,東奔西跑顧不上家。女兒是機(jī)場安檢員,把這次慘痛經(jīng)歷歸咎于常年作息不規(guī)律加之輻射危害,一氣之下辭職了。邱蘭急得嘴上長泡,埋怨女兒魯莽丟掉鐵飯碗。女兒卻滿不在乎,說大不了開網(wǎng)店唄!邱蘭心里嘀咕,你個中專生不知天高地厚,以為謀生跟網(wǎng)購一樣簡單呢。
邱蘭想給女兒加強(qiáng)營養(yǎng),正發(fā)愁每月兩千元的退休金入不敷出,碰巧聽說社區(qū)招聘交通協(xié)管員,每天工作5小時,月薪1500元,既不影響照顧女兒,又能貼補(bǔ)家用,便欣然報名。
邱蘭的工作時間分成兩段,早上七點到九點半,晚上五點到七點半。早晚高峰如同打仗,馬不停蹄地指揮車輛進(jìn)站出站,引導(dǎo)乘客排隊候車,還得解答各式各樣的問詢。最夸張的時候8輛公交車同時進(jìn)站,乘客蜂擁而上,自行車七扭八拐,整條馬路車鳴混戰(zhàn)。到了下班前半小時,路況明顯好轉(zhuǎn),每兩三分鐘才會有車進(jìn)站。馬小翠便打開話匣子,跟邱蘭聊東聊西。
聊得最多的是孫力。他是老北京,當(dāng)過兵,退伍后在一家機(jī)關(guān)的保衛(wèi)處工作二十多年,退休后又當(dāng)協(xié)管,已經(jīng)干了七個年頭。他的種種光輝事跡經(jīng)過馬小翠聲情并茂的渲染,讓邱蘭聽得如癡如醉。僅徒手擒賊的故事就有六個版本。大致是在一個月黑風(fēng)高的寒夜,有小偷從101路公交車躥下,向西狂奔,孫力用旋風(fēng)般的掃堂腿把他踢了個狗啃泥,趁勢將他摁倒在地。不料那廝藏有兇器,一刀刺中孫力的右掌,剎時血流如注。圍觀者里外三層,竟無一人敢上前相助。兩人殊死搏斗數(shù)回,眼看刀子就要刺進(jìn)孫力的胸膛,女失主才哭哭啼啼找來警察擒獲了惡賊。
馬小翠每次敘述的細(xì)節(jié)都略有出入,那賊掏過匕首,也掏過剪刀,錢包是紅色真皮,也曾金光閃閃。邱蘭從不揭穿她,而是望著孫力健碩的側(cè)影,享受電影畫面般的浮想聯(lián)翩。他年輕的時候必然非常英俊,如今兩鬢斑白,眉目間仍英氣逼人。
孫力對馬小翠的嘰嘰喳喳不以為然,他筆挺端立,每個指揮動作近乎完美,音色如同廣播員,讓這煩瑣的崗位有了幾分神圣感。休息喝水時他偶然聽到馬小翠說掃堂腿,差點噴出來,說你把我吹成白眉大俠了,不過是急中生智絆了他一跤。馬小翠拉過他的手讓邱蘭看,溝溝壑壑的傷痕一閃而過。孫力抽開手,哪個男人沒幾道疤?
比起身上的疤痕,邱蘭更想洞悉他內(nèi)心的傷痛。馬小翠說他離婚十多年了,一個人把兒子拉扯大的。邱蘭想不通,這樣的男人怎么會被拋棄?
時常有乘客來問路,這讓邱蘭有點發(fā)憷。這些年,除了單位和超市,她基本上窩在家里,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她讓女兒找來四通橋這幾路公交車的線路圖和換乘站,裝訂成小冊子裝在口袋,閑了就背。
這天有兩個女人問她雙秀公園怎么走,邱蘭答不上來。她倆兒手挽手走了,議論聲傳回邱蘭的耳朵:“傻了吧唧的!”邱蘭愣了,從小到大還沒被人這樣數(shù)落過。
馬小翠說:“坐101到馬甸橋西就是雙秀公園了,你光背站名沒用,得熟悉景點和標(biāo)志性建筑。”邱蘭恍然大悟,原來功課還差得遠(yuǎn)呢。馬小翠給她支招,下次遇到問路的就推給孫力,他簡直一活地圖。
邱蘭也發(fā)現(xiàn),幾乎沒人能問住孫力。他總是胸有成竹地給他們指明方向,附加最佳出行方案:您到金旺福呀?甭坐地鐵了,夠擠的,出來還得走一大截兒呢,不如坐79路到十院,原地?fù)Q乘308,兩站地就飯店到門口。西單羊肉胡同?您坐地鐵4號線到西四站,出C口右轉(zhuǎn)就是。問路者臉上的疑惑往往煙消云散,連聲道謝。
邱蘭羨慕他記性好,他說一個人嘛,在家閑不住,喜歡走街串巷瞎溜達(dá)。周末經(jīng)常騎車出游,從后海繞到前門,從南城飆到奧林匹克公園。如果不是樓蓋得太多,路修得太快,他對北京城會更加了如指掌。
邱蘭上班滿兩周,孫力提出跟馬小翠調(diào)換位置,由他和邱蘭共同負(fù)責(zé)東站牌。理由是車都從東邊過來,需要更加有力的疏導(dǎo),而且東站牌的101路最擁擠,可以讓邱蘭專職協(xié)調(diào)。
馬小翠說:“您是站長您說了算。”臉色卻暗沉下來。
邱蘭看得出,馬小翠對孫力很殷勤,三句話必然提到他,早上常給他帶包子。有一回孫力早早把水喝光了,馬小翠指著馬路對面的海悅大酒店,說那里面有飲水機(jī)。孫力遲疑了片刻,說進(jìn)那種地方不自在。馬小翠一把搶過他的杯子,說我正好活動活動筋骨。馬小翠家里有三套房,以前做過生意,不差錢。她在家悶得慌,便出來當(dāng)協(xié)管員。她說過,這活兒費力不討好,但跟著孫力就有干勁兒。
晚上回到家,女兒迫不及待地告訴邱蘭有好消息。原來她逛街時遇到一個中學(xué)同學(xué),在街道辦事處上班,說可以幫邱蘭調(diào)換到家門口的地鐵站當(dāng)協(xié)管員。“不用換!”邱蘭慌忙問她,“你還沒跟同學(xué)說吧?”女兒很納悶:“你在公交站風(fēng)吹日曬,地鐵站多舒服呀!”邱蘭說:“年紀(jì)大了,曬曬太陽還補(bǔ)鈣。”女兒說:“昨兒你還抱怨脖子曬爆皮了,衣領(lǐng)天天都是黑的。”邱蘭說:“跟同事都混熟了,懶得換地兒。”女兒從鼻子發(fā)出笑聲:“啥同事呀,一老頭兒一老太太。”
就是這個常人眼中普普通通的老頭兒,讓邱蘭突然感到生活有了一絲盼頭。他們的崗位距離將縮短十米,幾乎并肩作戰(zhàn)!早上出門前,她照鏡子的時間延長了,從未如此嫌棄自己寡淡的眉毛和鼻尖上的雀斑。她把頭發(fā)梳得一絲不亂,抹上防曬霜,撕掉嘴角的一塊小干皮。見女兒還在酣睡,她偷偷打開她的化妝包,挑出一只眉筆在眉毛上蹭蹭,左看右看不自然,又趕緊用毛巾擦掉。
邱蘭比平時早到十分鐘,孫力已經(jīng)來了。他把杯子掛在車站鐵欄桿上,從挎包里掏出小紅旗抖落平展,順手撿起一只易拉罐丟進(jìn)垃圾箱。
在聲如洪鐘的孫力面前,邱蘭對自己的蚊子聲更為自卑。車來了,幸好孫力連珠炮般幫她接話:“后面還有一輛101,上不去車的乘客別著急!”“門口的乘客不要擠,讓抱小孩兒的先上車!”“抬腳——關(guān)門兒——走嘍!”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既能監(jiān)測遠(yuǎn)處的車輛,又能注意到每個乘客的細(xì)節(jié),還讓邱蘭往馬路牙子里側(cè)站站,說當(dāng)心自行車剮著你。
“邱蘭不是101專員嘛,你怎么攬人家的活兒?”馬小翠不知從哪兒蹦出來。
“我這叫傳幫帶。”孫力說。
“當(dāng)初怎么沒帶過我呀?咱倆兒一東一西,獨擋一面。如今來了朵蘭花兒,還得捧著供著。”
孫力躬身給馬小翠作揖,她才抿著嘴去了,馬尾辮在腦后左右搖擺。
孫力扭頭對邱蘭說:“你喊不出來別勉強(qiáng),要學(xué)會用氣,一口氣吸到丹田,然后放松胸腔,像自來水似的慢慢呼出來。”他用手在腹部比劃著,給她做示范。
邱蘭乖乖地跟著他深呼吸。
孫力并沒她印象中那么嚴(yán)肅,有空也跟她閑聊。他最發(fā)愁兒子不找對象。兒子在外企工作,忙時不要命,閑時瘋狂玩,提起終身大事就打馬虎眼兒。他說那臭小子想找漂亮的,還不能矯情,這不自相矛盾嘛。
在邱蘭眼里,乘客是個龐雜而陌生的群體,來去匆匆,不留痕跡。而對于駐守在小小站臺長達(dá)數(shù)年的孫力來說,不少路人已成熟人。他們熱情地跟孫力打招呼,拉家常,逛完早市的大媽有時會塞給他幾個水果。不少公交司機(jī)和售票員會在短暫的停歇時刻跟孫力搭訕,他們親切地叫他孫大哥。
有時,孫力望著川流不息的車輛,臉上似乎有絲惘然若失的神情。邱蘭便揣測他惦記著某位乘客。
有些日子不見小秦了。孫力曾自言自語,回過神兒來跟邱蘭解釋:挺文氣一小姑娘,就在路口那個火鍋店當(dāng)服務(wù)員。她住在通州,傍晚老在這等323。她跟我說在北京活著太累,路上太疲憊,想回湖南老家,可男友在房產(chǎn)公司打工呢,說什么也不肯離京。
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家住車站附近的小南莊,每周四下午坐33路去廣渠門看中醫(yī),五點左右返回。三年了,孫力雷打不動地護(hù)送她從車站走到小區(qū)門口。她的兩腿因嚴(yán)重風(fēng)濕成拱形,一手挽著孫力,一手拄著拐杖艱難移步。腿疼發(fā)作時,孫力便直接背她回家。
這天老太太剛下車就迫不及待地抓住孫力的手:“哎,上回跟你介紹的那個孟大夫怎么樣啊?”
邱蘭的心提起來。
孫力低頭笑笑:“挺好,可我一人自在慣了,不想受管束。”
“不是管束,是照顧你。再硬朗的身子也有失靈的時候。人家是心腦血管專家,越老越吃香。家有醫(yī)生,如有一寶啊!”
“我可不想連累人家,動彈不了就去養(yǎng)老院唄。”
“胡說八道!”老太太嗔怪地拍了他一把。
他們走遠(yuǎn)了。想到自己也將孤獨終老,邱蘭陷入一股莫名的憂傷。
有多少人喜歡孫力,大概就有多少人討厭他,因為他管得太寬了。
只要車站出現(xiàn)小廣告,他便怒不可遏地從挎包掏出小刀刮掉。碰到頑固的膠漬,他還備有一瓶風(fēng)油精,灑上幾滴,拿抹布沾上熱水擦凈為止。那些貼廣告的往往在夜里行動,白天還真讓孫力逮住一回。兩個小青年腳下生風(fēng),眼疾手快,邊走邊從挎包里掏出小廣告,靠近車站時嗖地貼上雙面膠,藏在掌心,趁人不備往站牌和宣傳欄上拍幾下,頓時歪歪斜斜冒出一串廣告。
孫力用旗子指著他們高聲呵斥,小伙子我給你臉上貼塊膏藥好看嗎?車站就是城市的臉你懂不懂啊?年輕力壯的干點啥不好啊?光天化日之下毀市容你害不害臊?
兩人倉皇溜走。此后,四通橋車站的小廣告比周邊車站都要少。
孫力不允許候車乘客在高峰時段抽煙,如果勸說無效,就給他背誦《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直到他掐掉煙為止。
有人往垃圾箱吐痰,孫力也要干預(yù):您這一口痛快了,保潔員得用雙手掏垃圾!
每當(dāng)這時候,邱蘭都有些提心吊膽,因為孫力難免會遭到白眼、諷刺和謾罵。可他總是面不改色,四處出擊。
孫力也攤上過麻煩。有人在車站附近停車,孫力讓他趕快離開,他眼珠一瞪,破口就罵:“你他媽一破協(xié)管,裝什么交警?”
馬小翠挺身而出:“你非法停車!”
那人轉(zhuǎn)而攻擊馬小翠。邱蘭從沒聽過那么骯臟、下流的語言,如同把人當(dāng)街扒光了拿皮帶抽打,簡直是赤裸裸的暴力。她一句也插不上,只覺得血往頭上涌,胸口劇烈起伏快要爆炸了。可孫力無動于衷地站著,甚至還阻攔馬小翠:“別吵了,回到你的崗位! ”
馬小翠發(fā)起飆來也不要命,嘴比刀子快,刀刀見血。那人急紅眼了,揮拳要打她,被孫力一把擋開。旁邊幾個男乘客合力把那人抱住,他兩腳亂踢。
直到邱蘭大喊警察來了,他才掙脫身子,惡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開車走了。
孫力疏散開人群,責(zé)問馬小翠:“為什么不聽指揮?”
馬小翠的發(fā)絲濕漉漉貼著額頭,梗著脖子盯了他一陣,鼻翼開始抽動,豆大的淚珠噴涌而出。她轉(zhuǎn)身攔下一輛出租車,絕塵而去。
孫力摘下帽子,灰白的頭發(fā)被汗水浸透,額頭上留下紅色的勒痕。
邱蘭突然對這份工作充滿了質(zhì)疑。為什么不老老實實在家呆著,要冒著酷暑在這個鬼地方跟三教九流碰撞?為什么要以位卑權(quán)輕的角色去管控那些低劣的違規(guī)?為什么非要對野獸詮釋文明的定義?
孫力說:“小翠是委屈,可穿著工作服,你就是不能吐臟字兒。自己不講文明,怎么要求別人文明?”
第二天馬小翠沒來上班。孫力在西站牌替她值班,邱蘭算是第一次獨立上崗。時值秋季,他們已換上夾棉工作服,不出一個鐘頭便汗如雨下。她覺得孫力離她很遠(yuǎn)很遠(yuǎn),只能偶爾瞟他幾眼。他看到她,就會打出一個勝利的手勢。
傍晚,不時有些男女學(xué)生在車站纏綿,有一對格外忘情。男孩瘦高,靠在廣告欄上,戴副黑框眼鏡。女孩貼在他懷里,齊齊的劉海擋住眼睛。他們穿著松垮的校服,背紅藍(lán)熒光情侶書包。天色逐漸暗下來,他們摟得更緊,品嘗佳釀般沒完沒了地親吻,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孫力黑著臉忍了很久,終于在收工前大喝一聲:“嗨,那兩學(xué)生該回家了!”女孩扭頭剜了孫力一眼,繼續(xù)揪著男友的衣領(lǐng)竊竊私語。孫力喊:“你家的菜涼了,你媽的心也涼了!”引得四面路人注目。女孩羞憤難當(dāng),拽著男友匆匆離去。男孩回頭沖孫力豎起中指。
邱蘭說:“你又狗拿耗子。”
孫力振振有詞:“就是管閑事的人太少了,社會風(fēng)氣才這么敗壞。”
邱蘭把水杯和旗子收進(jìn)繡花手袋里。孫力說:“小包兒夠精致的。”邱蘭讓他猜猜多少錢,他豎起兩個手指頭:“二百?”邱蘭樂了,那是她邊看電視邊做的小活計。她最新的作品是個暗紅色的布藝錢包,一針一線格外用心,完工后感覺稍有點單調(diào),便打算在拉鎖下方繡只小猴子。
孫力說:“今兒我沒騎車,跟你溜達(dá)到四季青坐車去。”
兩人并肩而行。孫力一改往日大步流星,慢悠悠地陪她走。邱蘭問:“小翠怎么樣了?”孫力說:“還慪氣呢,你勸勸她。”邱蘭說:“解鈴還須系鈴人呀。”孫力嘿嘿一笑。
路過“食八方”,孫力突然停下腳步說:“咱順便把晚飯解決了吧,省得回家開火。”
邱蘭有點不知所措,支支吾吾說女兒一人在家呢。
孫力說:“一大活人還能餓著?到了咱這歲數(shù),也該為自己想想了。”說罷,推開餐館玻璃門。
他們選定里側(cè)靠墻的座位,點了魚香肉絲和香菇雞飯。孫力要了瓶青島啤酒,盡管邱蘭直擺手,還是堅持給她倒了半杯。邱蘭悄悄給女兒發(fā)短信:我到你馬阿姨家坐坐,你煮點面條吃吧。
一有顧客進(jìn)來,邱蘭就惴惴不安地往門口張望。幾口酒下去,燈光的色澤似乎更加柔和,邱蘭也慢慢放松下來。
孫力說:“家門口的館子早就吃膩了,以后咱開發(fā)一下四通橋附近的美食。”
邱蘭喜歡聽他說咱,帶著北京味兒的干脆和溫暖。
兩人東拉西扯了一陣,邱蘭小心翼翼地把話題引向她最好奇的領(lǐng)域,你怎么會一個人?
孫力沉默了片刻,說:“那家伙有模樣兒,還能唱兩嗓子,在歌舞團(tuán)干過幾年,跟他們書記好上了。我一直蒙在鼓里,書記老婆鬧上家門才知道。離唄。她在單位呆不下去,跑廣州做生意去了。那時候兒子才六歲,頭幾年她還給孩子寫寫信寄些玩具,后來就沒音了。”
邱蘭問:“你不恨她?”
孫力笑了:“我他媽氣吐血了,估摸少活十年。后來我才想明白,那家伙就算給你生八個孩子,也不會跟你踏實過日子。她就是那樣一種女人,眼睛永遠(yuǎn)瞅著窗外,心里跟有盆火似的。”
聊完那家伙,難免談起邱蘭那口子。
“他脾氣好,結(jié)婚28年沒跟我紅過臉,還做得一手好菜。五十歲生日剛過,他嗓子疼得厲害,吞咽困難,一查就是喉癌,拖了半年,受盡折磨。他走了以后,我做的飯女兒吃不慣,所以營養(yǎng)跟不上,孫子也沒保住,我真是沒用。”邱蘭哽咽了。
孫力悶頭喝了一口酒。
消失一周后,馬小翠神清氣爽地回來了,辮子上扎了朵玫瑰花,腋下夾著本歌譜。原來她加入了葵花合唱團(tuán),每天上午十點在玉淵潭公園排練。
“我們指揮特有氣質(zhì),以前是音樂學(xué)院的教授!我給他露了一嗓子,他立馬讓我站到高音聲部第一排!”馬小翠興奮不已。
孫力說:“有空我和邱蘭給你捧場去。”
馬小翠說:“擇日不如撞日,明天是周六!”
孫力悄悄問邱蘭:“我一高興就答應(yīng)她了,明兒你能去不?”邱蘭笑而不語。孫力說:“到時給你閨女烙張餅掛脖子上。”
“討厭。”邱蘭說,“你自個去吧,加入低聲部,你倆兒一對金嗓子。”
孫力說:“人家都有著名指揮家了,我得帶個伴兒,不能當(dāng)燈泡啊。”
邱蘭說:“帶個心腦血管專家多提氣呀!”
孫力一愣,笑道:“蔫兒壞!”
邱蘭很多年沒跟人逗貧了。女人撒嬌的天性似乎在體內(nèi)悄然復(fù)蘇,帶著微微發(fā)癢的歡樂,讓清冷的秋風(fēng)有了一絲醉意。
他們約好明天上午九點在公園門口見面。接下來的時間,她一邊指揮車輛,一邊思忖著該穿哪件衣服。網(wǎng)眼衫太單薄,新買的棉服太厚,風(fēng)衣又做作。鞋子同樣讓人頭疼,皮鞋走路多了腳疼,運(yùn)動鞋不好配衣服。她決定晚飯后拉女兒去逛商場,買雙坡跟休閑鞋。
匆匆趕回家,邱蘭覺得不對勁兒。屋里沒開燈,地上扔滿紙團(tuán)。女兒躺在床上,臉輕微浮腫。拉著她問了半天,女兒才說老公有相好了,一個四川女人。她發(fā)現(xiàn)他用支付寶給那女的買過首飾。
邱蘭問:“他承認(rèn)嗎?”女兒說:“我們剛吵完,我說離,他說好。”
邱蘭傻了,不相信這種電視劇和八卦雜志上的事會發(fā)生在自己家里。她給女兒拿了條毛巾,把她摟在懷里,真希望她又變回小小的嬰兒,可以用自己的臂彎為她抵擋一切傷害。女兒哭累了睡去,睡醒了又哭,不知道怎么熬過的一夜。天蒙蒙亮?xí)r,邱蘭收到孫力的短信,說今天風(fēng)大,囑咐她出門穿厚點,戴上帽子。她心里一陣酸楚,這是她人生中最無奈的爽約。
邱蘭買了女兒最愛吃的基圍蝦,做了一桌菜叫她起床。女兒懶懶地靠在椅背上,不動筷子,開始追溯老公出軌的種種跡象。上個月給同事替班去了兩趟成都,好幾個晚上沒接她的電話,回來后行李箱里多了新的睡衣……她斷定是因為沒有孩子,他精神空虛,才會漸漸離她遠(yuǎn)去。回到這個沉重的話題,她又淚水漣漣。
邱蘭理不出頭緒,只覺兩肋脹痛,對女婿充滿了怨忿。無論如何,他不該在女兒最虛弱的時候叛離。墻上的鐘表發(fā)出單調(diào)的滴答聲,正午十二點。這時候,馬小翠應(yīng)該已經(jīng)練完歌了,孫力還在公園嗎?
家里電話響了,邱蘭接起來,是女婿。他說到廣州了,剛下火車。邱蘭恨不得劈頭蓋臉責(zé)罵他一番,嘴里卻客客氣氣地說了句注意身體。女婿抬高嗓門,讓你女兒找點事兒干,省得吃飽了撐的胡思亂想!即使他用教訓(xùn)的口吻對她講話,邱蘭仍然無法還擊,一方面源于她骨子里的軟弱,一方面她在試圖維系他和女兒的感情。畢竟,這不是她的兒子。兒子罵完還是兒子,女婿罵完可能就是仇人了。如果女兒婚姻破裂,她們就真成了一對孤兒寡母。
城市越大就越脆弱,一場突如其來的秋雨幾乎讓路面陷入癱瘓。公交車姍姍來遲,且輛輛超載。天黑了,冷風(fēng)颼颼,小小的站臺積壓了很多乘客,還不斷涌入避雨的行人,彌漫著煩躁不安的情緒。
在這樣的夜晚,連孫力和馬小翠的大嗓門也被淹沒在滂沱的喧囂中。只要來一輛車,人們便蜂擁而上,拼死拼活也要擠上去。被傘尖兒戳痛的,踩著腳的,衣服蹭濕的,罵罵咧咧,連推帶搡。
孫力闊步走出站臺,立在一輛被層層圍堵的101前門口,舉起大黑傘,給一位正在奮力登車的男子遮住了雨。邱蘭也走下站臺,用打蔫兒的小旗子指揮大家排隊。路面上積水很深,她的膠鞋濕透了,冰冷的襪子纏著麻木的腳趾。乘客們陸陸續(xù)續(xù)排成一條長隊。
孫力指揮車輛盡量靠邊停,這樣乘客就可以從站臺直接邁入車廂,而他一直給他們撐著傘,半個身子浸在雨中。有人上車后把自己的雨披送給他,他轉(zhuǎn)身就給邱蘭套上。像一個突如其來的擁抱,邱蘭還沒反應(yīng)過來,身體就被裹住了,連帽子都嚴(yán)嚴(yán)實實的戴好了。雖然只是薄薄一層塑料,但是擋住了刺骨的寒風(fēng)。再定神看他,還是撐傘的動作,胳膊舉得那樣高,嘴唇微青,竟然有點英勇就義的感覺。她想哭。
七點半,馬小翠的老公開車來接她,讓邱蘭一起搭車回家。她執(zhí)意不肯。她知道像這樣的天氣,晚高峰會持續(xù)到八點半以后,而孫力不等到站臺寂靜是不會離開的。他那股認(rèn)真勁兒讓她無奈,也讓她心疼。馬小翠意味深長地看看邱蘭,又看看孫力,細(xì)聲細(xì)氣地說那你倆兒相依取暖吧。
幸虧天黑,邱蘭的臉燒到耳根。孫力倒沒在意,跑去吆喝伺機(jī)停靠的黑車了。
雨停了,天空變得舒朗,站臺的人也漸漸少了。孫力宣布收工,陪著邱蘭走到家門口。她一點都不冷了,濕透的雙腳微微發(fā)脹。她把雨披脫下來,用袖子擦掉上面的水珠,折成小方塊,塞進(jìn)孫力的挎包里。他們面對面站著,說了好幾聲再見,可誰也不動。
孫力說:“你回吧,好好睡一覺,明早不用著急上班。”
邱蘭揮揮手,就上樓了。女兒在洗澡,從浴室里傳出歌聲,看來心情轉(zhuǎn)好。邱蘭走到窗邊,發(fā)現(xiàn)孫力還在樓下,坐在小區(qū)的石凳上歇著呢。她有種預(yù)感,這時候她再下樓,她暗淡的生活就會改變。她涌起十八歲的沖動,但沒有那時候的勇氣。她揪著窗簾,陷入低燒般的恍惚中。
“媽,幫我拿浴巾!”女兒清脆的聲音將她喚回現(xiàn)實。
“你們到什么程度了?”馬小翠逮空盤問邱蘭,一面上下打量著她,“原來你是悶騷型的。”
邱蘭無從解釋。誰會知道,她目前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孫力逛一次公園。
前一陣?yán)嫌徐F霾,后來又陰雨連天。好不容易天兒好了,又感冒了。下周吧,下個周末去玉淵潭走走,瞧瞧馬小翠唱歌去。從深秋到嚴(yán)冬,她跟孫力一次次約定著。陽光好的話還可以劃劃船,公園北門新開了家巫山烤魚,據(jù)說味道不錯。孫力不斷充實著計劃,讓她充滿期待。
元旦前夕,邱蘭破天荒一個人到崗。
七點鐘,乘客明顯增多。邱蘭兩個站牌來回跑,氣喘吁吁。孫力平日一向來得最早,難道今兒病啦?馬小翠遲到幾分鐘不奇怪,她兒子元月結(jié)婚,現(xiàn)在正忙乎著呢。邱蘭和孫力早就收到了婚宴請柬。邱蘭跟他商量份子錢,孫力說咱倆兒還用分著給?說得她臉紅心跳。可惜她精心縫制的布藝錢包被女兒搶去了,要給女婿當(dāng)新年禮物。孫力的本命年生日怎么辦呢?她決定給他織條紅圍巾。
過了七點半,馬小翠從過街天橋上走來,步履有點凌亂,不像往日那么輕快。奇怪的是,她還戴著一副茶色眼鏡。
邱蘭的胸口被箍住了。
走近了,馬小翠眼瞅著別處對她說:“老孫沒了,心肌梗。昨晚跟幾個哥們喝點酒,到家就不行了……”
邱蘭突然想起丈夫去世的情景,醫(yī)生默默摘下伴隨他痛苦掙扎數(shù)日的呼吸機(jī),他平靜得像一條冰柜里的魚。耳邊似乎又傳來女兒流產(chǎn)后的哭聲,說孩子沒了。沒了,就是徹底隔絕,沒有溫度,也沒有回音。無論你如何抗拒,這一頁從你生命之書中翻過去了,天知道再翻幾頁就到頭了。等自己沒了,那些重重疊疊的悲傷也就隨之煙消云散了。日頭已經(jīng)升高,街道上依舊車水馬龍,人們行色匆匆。
一輛不堪重負(fù)的公交車緩緩駛來,邱蘭舉起旗子:“101進(jìn)站,請大家先下后上,不要擁擠!”
(責(zé)編:楊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