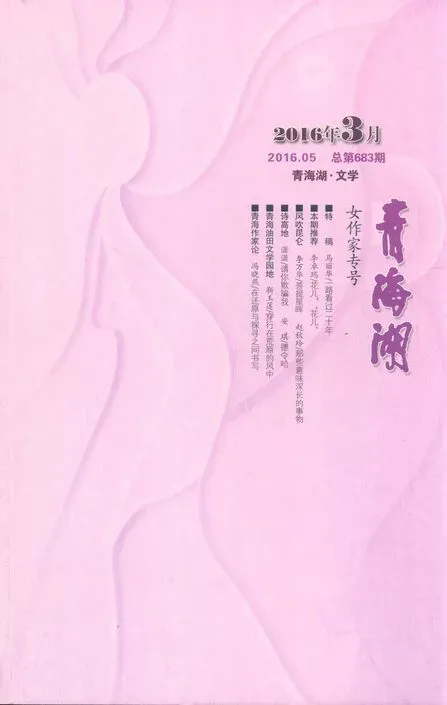坐在菩提樹下聽雨(散文)
古岳
?
坐在菩提樹下聽雨(散文)
古岳
老家宅院里有三棵樹,一棵是丁香,另兩棵也是丁香。只是一棵是紫丁香,另兩棵是暴馬丁香。暴馬丁香在青海也叫菩提樹,此菩提非彼菩提。它應(yīng)該不是當(dāng)年釋迦牟尼坐在樹下覺悟成佛時(shí)的那種菩提樹,那種樹原名叫蓽缽羅樹,因釋迦牟尼在樹下證得覺悟而得菩提之名。在植物學(xué)分類上,那是一種常綠闊葉喬木,在青海這等高寒之地絕難成活。不過,暴馬丁香的確也叫菩提樹,塔爾寺就有一棵這樣的菩提樹。塔爾寺原本是宗喀巴大師的出生地,他被佛界譽(yù)為第二佛陀。如此說來,又當(dāng)是,此亦菩提,彼亦菩提。
乙未年四月,母親病重,醫(yī)院告知已無良方。期間,好友提供信息,說云南有良醫(yī),便急赴昆明求醫(yī)問藥。回到西寧,遂護(hù)送母親至故土老宅,整日陪伴左右,煎藥熬湯,希望能出現(xiàn)奇跡,母親轉(zhuǎn)危為安。三年前,比這個(gè)季節(jié)稍晚些時(shí)候,父親也病重,醫(yī)院也曾告知已無良方,我也將父親護(hù)送至故土老宅靜養(yǎng)。一個(gè)星期后,他居然能下地走路了,之后,一天天好將起來,我感覺是故土的滋養(yǎng)起了作用。所以,護(hù)送母親回去時(shí),我絲毫沒有猶豫過。
其時(shí),芒種剛過,夏至將至,正是百花盛開的季節(jié),老宅庭前屋外,也是一派繽紛艷麗。這使我想到了母親,由母親又想到了一個(gè)聽來的故事,說的是一個(gè)俄羅斯盲人乞丐,正坐在莫斯科大街上乞討,身前擺放著一塊牌子,上面有一行文字,只字未提乞討的事,卻寫著一句詩一樣的話:雖然已是百花盛開的季節(jié),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所有行人都被這句話吸引,便停住腳步,向他伸出友愛之手。母親雖然眼不盲,但因?yàn)橐恢碧稍诓〈采蠠o法起身,也看不到百花盛開的樣子。所以,一天午后,我們把母親小心地抱到一張輪椅上,推到門外,讓她看花開的樣子,曬曬太陽。在一塊開滿油菜花的地邊,還稍稍停留了一會(huì)兒。再次回到屋里躺下后,母親告訴我,現(xiàn)在她一閉上眼睛,眼前全是油菜花,一片金黃。之后的幾天里,只要天氣晴好,我們都會(huì)推著她到田野上轉(zhuǎn)轉(zhuǎn),有時(shí)候,也會(huì)在院內(nèi)的花園前坐上一會(huì)兒。直到有一天推她回來之后,她好像很累的樣子,才停了一兩天。
老宅門前,除了綠樹花園就是莊稼地;庭院里面,除了一小塊水泥地坪就是一座花園。房前屋后的綠樹少說也有二十幾種,大都是喬本類開花植物,其中也有多棵菩提樹,有兩棵還在開花,其香仿佛紫丁香,卻遠(yuǎn)比紫丁香沉著幽遠(yuǎn),清雅耐人。花園里也有十幾種植物,都是草本和木本類觀賞花卉。這些綠樹花草是父親與我共同經(jīng)營培養(yǎng)的結(jié)果,父親栽種的大多是中用的品種,而我栽種的那些幾乎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所有綠樹花草,平日里都由父親照看,而我只在回到老家的時(shí)候才有機(jī)會(huì)打理它們。所以,在老家陪伴母親的這些日子里,除去守在慈母身邊的時(shí)間,其余時(shí)間,我大多在這些樹木花草跟前,給它們松土澆水。
忙完了這些事,而母親也正好睡著的時(shí)候,我就會(huì)靜靜地坐在花園前的那棵菩提樹下,喝茶歇息一會(huì)兒。幾乎每天,我都會(huì)有好幾次坐在那菩提樹下的空閑時(shí)間。第一次坐到那菩提樹下時(shí),幾滴雨落了下來,打在樹葉上發(fā)出沙沙的聲音。我抬頭看了看天,天上幾乎沒有云彩,初夏的陽光照徹山野。側(cè)耳傾聽,已經(jīng)沒有了雨聲。就那么稀稀拉拉地落了幾滴之后,雨再?zèng)]有落下來,但我依然在靜靜地聽,希望能聽到雨聲,可是沒有聽到。再聽,又似乎聽到了,雨聲好像并不在近旁,而是在很遠(yuǎn)的地方——感覺在一個(gè)很遙遠(yuǎn)的地方,正有大雨滂沱。
我忽然想到了兩個(gè)字:聽雨。近一段時(shí)間里,這是我第二次想到這兩個(gè)字,第一次想到這兩個(gè)字是在一個(gè)人的葬禮上。那天,當(dāng)人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剛挖好的地穴里,準(zhǔn)備填土的時(shí)候,我突然想到那地穴深處或許有一扇門,那扇門隔開了兩個(gè)世界。一扇門特地為一個(gè)人打開了,從那里進(jìn)去之后,他就去了另一個(gè)世界。地穴所在的山坡上哭聲一片,淚雨紛飛。這時(shí),“聽雨”兩個(gè)字就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雨聲來自另一個(gè)世界。故鄉(xiāng)有一種說法,一個(gè)人亡故之后,送葬的隊(duì)伍里最好沒有哭聲和淚水,說生者的每一滴眼淚都會(huì)化作冰冷的雨點(diǎn)打在亡者的身上,那是凄苦的雨。可是,頃刻間骨肉分離,生者無法擋住眼淚。
不知道為什么,我感覺亡者正在一個(gè)門洞里,回過頭來望著我們微笑。一束陰冷的光從那門洞的另一側(cè)照進(jìn)來,很刺眼。那光芒塞滿了整個(gè)門洞,以至于他看上去就像是被那一束光托舉著。那門洞很深,像一個(gè)隧道——抑或是時(shí)光隧道吧。很顯然,那門洞的這邊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gè)世界,那么,門洞的那邊又是一個(gè)什么樣的世界呢?他或許已經(jīng)看見了那個(gè)世界,所以,才回眸一笑。可是,除了那一束光芒和那個(gè)門洞之外,我們什么也看不到。當(dāng)然,這只是我的憑空想象,也許那光芒的實(shí)質(zhì)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它擋住了一切,阻隔了一切,使我們無法看到里面的真相——那也許就是死亡的真相,也是生命的真相。
我很清楚,這只是一剎那間閃現(xiàn)在腦海中的一個(gè)景象。佛經(jīng)上說,一念之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又有九百生滅。生生死死的輪回隨時(shí)都在進(jìn)行,須臾不曾停歇過。而在那一剎那里,我甚至想到過,站在那門洞里回頭微笑的那個(gè)人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gè)孩子,而是我自己。我在我自己的葬禮上。我聽到了雨聲。雨季如期而至,雨鋪天蓋地,大大小小的雨滴落下來,我在無邊無際的雨中艱難前行。那個(gè)世界里沒有動(dòng)物,沒有植物,甚至沒有泥土,沒有你曾熟悉的任何物質(zhì)——那個(gè)世界里的物質(zhì)看上去更像意識(shí)。雨落下來,卻不知道落到哪兒去了,沒有在地上濺起水花,也沒有漂起水泡,它們好像直接鉆進(jìn)地縫兒里,穿越而過,落進(jìn)了另一個(gè)世界里。雨滴不停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那其實(shí)并不是真的雨,而是另一個(gè)世界里人們的眼淚。它穿越時(shí)空,紛飛而至,飄落在另一個(gè)世界里就成了雨。它從我的身內(nèi)穿過去,像子彈那樣,我甚至能聽到它從我身體里呼嘯而過的聲音。
可能與自己的年齡有關(guān),感覺一過了五十歲,生活中的葬禮一下就多了起來,好像剛剛從一個(gè)葬禮上回到家里,又聽到另一個(gè)葬禮要舉行的消息。這當(dāng)然不是現(xiàn)在亡故的人比以前多了,以前也一定有人從這個(gè)世界上不斷地離開,而是因?yàn)槟氵€年輕,從你身邊離開的人還不是很多。即使有,也是隔了足夠長的時(shí)間,會(huì)讓你有一個(gè)從悲傷中走出來的間隙。可是,這兩年不一樣了,好像隨時(shí)都有一個(gè)葬禮在等著你。于是,雨聲不斷,生命中的雨季已經(jīng)來臨。
宅院里有兩排木頭房屋,一排朝南,一排向東。坐在菩提樹下時(shí),我面朝向南的屋子,背靠花園。花園中間有一棵碧桃長得茂盛,它先開花,后長葉子,花早已敗去,現(xiàn)在只剩葉子了。還有六棵牡丹,三棵芍藥,一棵野生皂角,兩棵野生核桃,五六棵大麗花,兩棵荷包花,一棵圓柏和一棵大葉杜鵑。點(diǎn)綴其間的是幾棵菊花和一溜金銀花。有幾棵牡丹是今年新栽的,剛長了新葉子,其余幾棵牡丹,花也早已開敗,最后的一兩朵牡丹也在那兩天敗落了。所有開花的植物,現(xiàn)在只有那幾棵芍藥。剛回到家時(shí),它們才開始打花骨朵,只幾天時(shí)間,都已競(jìng)相開放。花園的墻上爬滿了一種藤類植物,有十幾株,是我從城里買回來種在那里的。當(dāng)時(shí),我是能叫出它們的名字的,現(xiàn)在卻都已經(jīng)忘了。它們有五片像花瓣樣很大的葉子,厚厚地覆蓋著磚墻。菩提樹冠如傘蓋,再強(qiáng)的陽光都照不到樹下。樹下放了兩塊平整的石頭,正好當(dāng)茶幾,抬一把椅子、端一杯香茶坐在樹下,就可以安靜下來了。
從四月底到五月初的好些天里,都會(huì)落下幾滴雨來,卻一直沒有像樣地下過。只有兩次,淅淅瀝瀝地下了不到半個(gè)時(shí)辰。我都站在那菩提樹下聽過雨,仔細(xì)聽過之后,我發(fā)現(xiàn),它落在不同的地方所發(fā)出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在那樹下,我所聽到的其實(shí)并不是雨聲,而是樹葉的聲音。雨滴落在水泥地上時(shí),一開始,一落下就干了,慢慢的,水泥地都被淋濕了。再后來,竟然積了薄薄一層雨水。而落在花園泥土里的雨滴,一落下就鉆進(jìn)泥土里不見了。因?yàn)榫煤滴从辏屈c(diǎn)細(xì)雨對(duì)土地來說起不了什么作用,半個(gè)時(shí)辰之后,那泥土也才泛起一點(diǎn)潮氣。
有一次下雨時(shí),我還走出院子,到前面的田埂上去聽過雨聲。一走出門前的花園和菜地,就是大片的莊稼地,大部分種著麥子,也種了幾塊油菜。麥子正在抽穗,油菜剛進(jìn)入花期,金燦燦的油菜花開得正艷。我俯身麥田,將耳朵伸到麥子地里細(xì)聽,聽到的是很輕柔的雨聲。雨滴順著麥稈滑到下層的葉片上,結(jié)成了露珠。少頃,又側(cè)身油菜花地傾聽,聽到的卻是很清脆的雨聲。雨滴先落在頂端的花瓣上,而后從那里輕輕滑落,落到下層寬碩的葉片上,汪在那里,像一顆顆珍珠,晶瑩剔透。想來,那雨滴落下來時(shí)一定非常細(xì)碎,因?yàn)椋湓谀且黄吨榇笮〉幕ò晟蠒r(shí),那花瓣只是輕微地顫抖了一下,不仔細(xì)看,甚至看不出它曾顫動(dòng)過。
從田野上回到院中,再次站在那棵菩提樹下時(shí),雨已經(jīng)停了。望著花園里的那些開花植物,我想到一句青海“花兒”的唱詞:花開花敗年年有,人身才有幾遭哩?這是一個(gè)設(shè)問的句式,但它并無意追問,而是在慨嘆人世間的聚散何其珍貴。它提醒人們,對(duì)蕓蕓眾生而言,無論你經(jīng)歷過多少次的生死輪回,人生都可能只有一次,轉(zhuǎn)瞬即逝。還不如那些開花植物,無論時(shí)間過去多久,只要到了開花的季節(jié),它們都會(huì)如期開放。由此想到母親,想到父親,想到一家老小十幾口人,今生今世能聚在一個(gè)小小的院落里是何等樣的奇緣和造化呢?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們一大家子要在一起生活一輩子,這該是怎樣漫長的修煉才能得來的緣分和福報(bào)呢?
我是個(gè)俗人,俗人總是放不下各種煩惱。母親病中,守在病榻前,回想母親一生的經(jīng)歷時(shí),感覺她的煩惱要比快樂多很多,為饑荒、為兒女、為家庭、為年景和收成,甚至為牛羊和天氣煩惱。可是,我相信,在她生命最后的這些日子里,她一定感覺到了正是這無盡的煩惱才構(gòu)成了她珍貴的人生記憶。如果把這多煩惱一下從她的記憶中抹掉了,她會(huì)更加煩惱,而不會(huì)只剩下快樂。對(duì)一個(gè)肉身俗人來說,沒有任何煩惱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能放下一切煩惱的人也能放下一切快樂。我想,那就是覺悟了的人,而覺悟了的人就是佛了。
當(dāng)然,我并沒有像佛祖一樣一直坐在那菩提樹下。每天,我還有一小段時(shí)間是坐在自己屋里的。這一小段時(shí)間里,一般我都會(huì)做同一件事,就是用一管小楷毛筆在一張?jiān)缫巡煤玫男埳铣瓕憽缎慕?jīng)》,至少每天一遍,有時(shí)候也會(huì)多抄一遍,有一兩幅抄好以后就貼在墻上了。《心經(jīng)》上說:“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shí);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shí)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很多時(shí)候,快樂就是煩惱,煩惱亦是快樂。沒有煩惱何來快樂,沒有快樂又何來煩惱?
這樣下來,一天當(dāng)中的閑暇時(shí)光已經(jīng)所剩不多,我就利用這點(diǎn)有限的時(shí)間觀察花草樹木、鳥蟲飛絮。一天午后,我看到一朵盛開的粉白色芍藥里有一只很小的蜜蜂,想必是去采蜜的。它先是向縱深探尋而去,后又在花蕊中間穿行,之后又在一片花瓣上向上攀爬,幾經(jīng)努力,均無功而返,跌落在花心里。它顯得很緊張,像是要急著逃出來的樣子。我決定幫它一下,便拿一根很細(xì)的樹枝伸到它的面前,它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樣,一下就抱住了小樹枝,我輕輕地取出樹枝,剛一到外面,它就飛走了。看來,它真是在逃命。可我不知就里,蜜蜂采蜜應(yīng)該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怎么會(huì)心生恐懼呢?過了一兩個(gè)時(shí)辰,再去看那一朵芍藥時(shí),我仿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朵盛開的芍藥所有的花瓣已經(jīng)再次閉合,將花蕊深藏在里面。也許它會(huì)再次盛開,也許這是敗落的一個(gè)前兆。如果那只蜜蜂還在里面,它肯定是逃不掉了。于是,對(duì)它心生敬畏,它竟然在幾個(gè)時(shí)辰之前就能預(yù)知危險(xiǎn)之降臨,我對(duì)此卻一無所知。后來的幾天里,我才發(fā)現(xiàn),一朵盛開的芍藥,每天傍晚來臨前就會(huì)重新閉合,至次日早上太陽出來時(shí),又會(huì)重新綻放。很顯然,蜜蜂們?cè)缭谖抑熬鸵焉钪O其中的奧妙。
也是在這天下午,我剛坐在那棵菩提樹下,便被幾聲悅耳的鳥鳴聲所吸引,確切地說是兩只鳥的鳴叫,一只是布谷鳥,另一只是喜鵲,它們的鳴叫聲均來自屋后那一排高大的白楊。那幾天,每天的某一個(gè)時(shí)刻,它們總會(huì)站在中間的那棵楊樹上叫個(gè)不停。那棵樹上有一個(gè)喜鵲窩,好幾年前就已經(jīng)在那里了。當(dāng)布谷鳥站在一根樹枝上開始鳴叫時(shí),又總會(huì)聽到喜鵲的聲音。我猜想,喜鵲可能正在孵小鵲,而布谷鳥說不定已將自己的蛋偷偷產(chǎn)在了鵲巢里,盼著孵卵的喜鵲替自己孵出一只小布谷來——這是布谷鳥一貫的習(xí)性和做法。喜鵲則不知所以然,還以為布谷鳥眼饞它的鳥蛋——其實(shí),布谷鳥偷梁換柱、貍貓換太子的陰謀可能早已實(shí)施完畢——于是,喜鵲在自家門口叫罵,讓布谷鳥離遠(yuǎn)點(diǎn),布谷鳥卻裝出一副被冤枉的樣子大呼小叫,無論喜鵲怎么威脅,它就是不肯離開。
我可能有十幾年沒有聽到布谷鳥叫了,這次回老家再次聽到布谷鳥叫,感覺是一個(gè)吉兆,我希望與母親的安康有關(guān)。這些年因?yàn)榉馍接值纫幌盗泄こ痰膶?shí)施,故鄉(xiāng)的山野又一派蔥蘢,曾經(jīng)砍伐殆盡的樹木重新又長滿了山坡。加之,農(nóng)田里施用的農(nóng)藥比以前也有所減少,一些記憶中的鳥兒又回到了故鄉(xiāng)的山野。除了麻雀沒有以前那么多之外,鳥的種類和數(shù)量甚至比我小時(shí)候還要多。其中有好些長著五彩羽毛的鳥兒,以前,我只在深山老林中才見過的,現(xiàn)在卻在房前屋后飛翔著,鳴叫著。一種俗名野雞的雉鳥,甚至常常飛到人家的院子里咯咯地叫著。有一天,我還看到兩只胖嘟嘟的布谷鳥就在門前的空地上悠閑地漫步,我跟在后面走了好遠(yuǎn),它們只是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而后依然不緊不慢地徑自走去,直走到一塊油菜地邊上,才晃晃悠悠地鉆進(jìn)了油菜花叢中。無論是對(duì)故鄉(xiāng)的山野,還是對(duì)那山野以外的大千世界,這都稱得上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將目光從屋后的白楊樹上收回時(shí),又被庭院中飛來飛去的一群小精靈給截住了。便側(cè)目望向庭院上方,這一看卻令我大吃一驚。那個(gè)小小的庭院中竟然飛舞著無數(shù)個(gè)幼小的生命,這還是肉眼所能看到的——而肉眼所無法看到的一定會(huì)更多。這些飛行者大都是一些飛蟲,但也有一些楊絮之類的飛行物,其中有一只像蜻蜓那么大的黑色蚊子,它是小院飛蟲中的獨(dú)行俠。楊絮如果漫天飛舞,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它們會(huì)落得到處都是,像雪花,卻遠(yuǎn)沒有雪花那樣討人喜歡。但是,如果只有幾點(diǎn)楊絮在半空中輕輕盈盈地飛舞,那卻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它居然也能自由地飛翔,甚至在落到地面之后也能重新飛舞起來。
坐在那棵菩提樹下時(shí),不斷有五顏六色的飛蟲落在你的手上、臉上、鼻子上,甚至直接飛進(jìn)耳朵里,發(fā)出轟隆隆的聲音。有的甚至?xí)RВ屇愀械捷p微的疼痛。這天下午,無意間,我還看到一條足有三四米長的蜘蛛拉的絲線,從一棵丁香樹直接拉到了對(duì)面的屋頂上,看上去就像是一絲流云,令人嘆為觀止。且不說它拉這樣一條直線有什么用——也許是一座蜘蛛用的高架橋吧。我驚訝的是,它是怎么做到的,難道它能凌空飛渡不成?要么它們一定也有遠(yuǎn)距離高空作業(yè)的特殊裝置了,要不,以人類的常識(shí)而言,這是絕難做到的。
很多時(shí)候,坐在那菩提樹下的并不是我一個(gè)人,還有其他人,有老有少。但大部分時(shí)間里,除了我,只有父親。與他坐在那樹下時(shí),他只默默地坐著,不說話。我能看出來,他很擔(dān)心母親的病,但并不表現(xiàn)出來。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樹下對(duì)他說,你去看看母親唄。他先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像是沒有聽見。我看了他一眼,他才輕輕點(diǎn)了點(diǎn)頭,之后向母親的屋子方向望了一眼,便不做聲了,我也沒再說什么。我知道父親的秉性,他能把天大的事都裝在心里,而不露出半點(diǎn)神色。沉默。再沉默。這是他不變的神態(tài)。任世界風(fēng)云變幻,潮起潮落,他自巋然不動(dòng)。
五月初的一天,又下了一點(diǎn)雨,前后也不到半個(gè)時(shí)辰,下得也不大。我又坐到那菩提樹下聽雨,直到雨過天晴。雨停的時(shí)候,一只小蜜蜂一直停在我眼前,飛快地拍打著一對(duì)小翅膀,好讓自己能保持飛翔的狀態(tài)而停留在半空中。如果你不細(xì)看,根本看不出它是在飛,而更像是被一根看不見的細(xì)線吊在了半空中。它朝著我發(fā)出輕柔的嗡嗡聲,兩只小眼睛一直定定地盯著我看。我覺得,它就是幾天前我?guī)椭鴱幕ㄐ睦锾由哪侵恍∶鄯洹:髞恚也虐l(fā)現(xiàn),它也并非一直停在一個(gè)地方不動(dòng),只要有什么蚊蟲飛近它的領(lǐng)空,它會(huì)立即作出反應(yīng)予以攻擊。那反應(yīng)之敏捷、攻擊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攻擊之前,它幾乎不做任何準(zhǔn)備,需要攻擊時(shí),直接彈射出去,像一支箭。它所攻擊的對(duì)象,有些我是能看見的,有些我是看不見的。所以,它在我面前停留飛舞的那一會(huì)兒里,其他蚊蟲皆不得靠近。只有一只黑蚊子在它下方超低空飛行——那可能是一種隱蔽方式——它比前幾日看到的那一只黑蚊子稍小一點(diǎn),但也有一只小蜻蜓那么大了。
足足有半個(gè)多月時(shí)間里,盡管很多天的天氣預(yù)報(bào)都說次日有雨,但是,雨一直沒有下下來。我想,它可能落在了遠(yuǎn)方,譬如法蘭克福或巴黎,譬如巴西高原或智利山地。這使我想到,智利有一種民間手工藝品或者說是一種民間樂器,它有一個(gè)好聽的名字:聽雨。它是用仙人掌的枝干做成的,里面裝有細(xì)沙,兩端封死之后,拿起來置于耳邊,使其傾斜,便會(huì)發(fā)出沙沙的聲音,那聲音就像是雨點(diǎn)落在樹葉上發(fā)出的聲音,美妙至極。那年去上海看世博會(huì),在智利館巧遇此物,很是喜歡,買了一根把玩,至今愛不釋手。有它在,即使看不到雨,即使在沒有雨的季節(jié),我也能聽到雨聲了。
直到端午節(jié)前一日,一場(chǎng)像模像樣的雨才下了起來,從大清早開始到午夜時(shí)分一直在不停地下,雖然不大,卻也細(xì)密。臨睡前,我還煞有介事地到那菩提樹下站了一會(huì)兒,聽雨。因?yàn)橛衅刑針涞膫闵w,雨滴不會(huì)直接落在身上,落到身上的是菩提樹葉上的雨水。這時(shí),我所聽到的雨聲已不那么清脆悅耳了,因?yàn)闃淙~都被淋濕了的緣故,雨滴落在菩提樹上所發(fā)出的聲音,多了些零亂,而少了些韻致。
人生苦短,行色匆匆,難得有專門聽雨落、聽雪落、聽風(fēng)過、聽花開、聽鳥鳴的時(shí)間。久而久之,我們已然忘懷了雨落、雪落的聲音,也想不起風(fēng)吹、花開和鳥鳴的聲音了。可是,也許這些才是生命里最值得聆聽的聲音。
我無法預(yù)知,母親能否過得了這個(gè)坎兒——也許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一個(gè)坎兒,也不知道日后,我還會(huì)不會(huì)坐在那棵菩提樹下聽雨,但可以肯定的是,父親、母親,還有我自己,最終都會(huì)走進(jìn)一場(chǎng)如期而至的雨,消失在綿綿不絕的雨幕中,無影無蹤。那么,誰還會(huì)坐在那菩提樹下聽雨呢?誰又會(huì)站在那雨幕中回眸,拈花微笑呢?好在那棵菩提樹一直會(huì)在那里,只要有人坐在那樹底下,就會(huì)聽到雨聲自遠(yuǎn)方紛紛而至。
責(zé)任編輯唐涓
作者簡介:古岳,又名野鷹,本名胡永科,藏族,1962年生人。高級(jí)記者,青海省作協(xié)委員,全國宣傳文化系統(tǒng)“四個(gè)一批”人才,國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近百萬字文學(xué)作品發(fā)表出版,作品散見于《民族文學(xué)》《散文》《散文選刊》《新華文摘》等刊物,并收入多種選集和滬教版初中語文課本,出版《誰為人類懺悔》《寫給三江源的情書》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