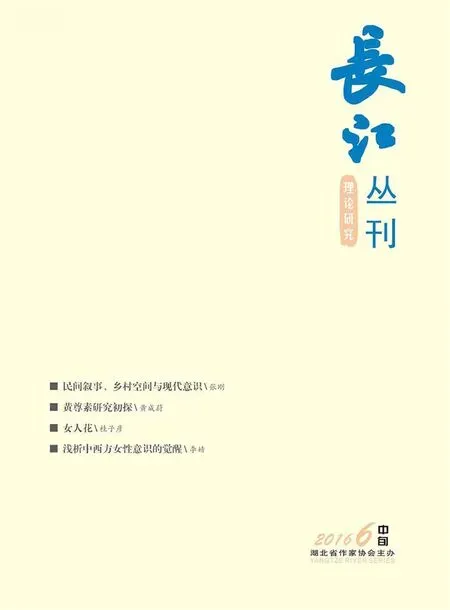黃尊素研究初探
黃成蔚
?
黃尊素研究初探
黃成蔚
【摘 要】黃尊素是晚明東林黨重要成員,因彈劾魏忠賢等閹黨成員被害,與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等人稱“東林七君子”,明代儒學大師劉宗周更是贊揚:“凜正色于蘭臺,抗直聲而如矢”、“與日月爭光,允矣!”然而對黃尊素研究的論著尚屬空白,對其作品集,三百年來也未曾經人整理。本文即以黃尊素的作品文本為依托,較為深入地研究黃尊素的政治思想與文學成就,及其思想行為對他兒子黃宗羲等和后世的啟迪,力圖還原黃尊素應有的歷史地位與學術貢獻。借此拋磚引玉,以引起學界對黃尊素這位浙東名賢的重視。
【關鍵詞】黃忠端公文集 黃尊素 政治思想 文學成就 黃宗羲
一、《黃忠端公文集》的版本考辨與文獻整理
2015年夏,應浙江古籍出版社之邀,參與整理點校《黃尊素集》的工作。黃尊素是晚明東林黨的重要成員,同時他又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的父親,明代儒學大師劉宗周更是贊揚:“凜正色于蘭臺,抗直聲而如矢”、“與日月爭光,允矣!”可以說,他在浙江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小覷的。
由于黃尊素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與歷史地位,他在被閹黨迫害致死之后,雖然在崇禎朝迅速得到了平反,但他生前的著作并沒有在當時立即被系統整理并公諸于世,我們現在所能得知的最早關于黃尊素作品集的信息,是清康熙年間甬上后學李文胤的一段回憶性質的文字:“文胤亦嘗得登公(黃尊素)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愾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宗羲命文胤序之。”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李文胤曾經到過黃尊素家中,彼時黃尊素雖早已去世,但他的兒子們尚在家中,甚至很有可能,黃尊素的長子黃宗羲正在家中,并將黃尊素的遺集給李文胤看。可見,從黃尊素去世的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到李文胤從黃宗羲家看到黃尊素遺集的康熙初年,在這半個世紀里,黃尊素的遺集一直是秘藏于其家中,被他兒子妥善保存著,但并未刊刻行世過。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當時海寧知縣許三禮因有感于黃尊素的忠烈,“故刻公之集以救之”。這就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刊刻最早的黃尊素的作品集,即清康熙清遠堂許三禮刻《黃忠端公文集》本。而且,前引李文胤所撰一段文字中,黃宗羲“待公集新出”,讓李文胤為此集寫序,而恰恰李文胤的這篇序,被列在許三禮刻清遠堂本之首,可見許三禮在正式刻印《黃忠端公文集》之前,已經接觸到了李文胤這篇受黃宗羲之托而寫的序。李文胤為之寫序的這部黃尊素的“新出之集”,就是許三禮所刻的清遠堂本《黃忠端公文集》。從而我們更可得出以下關于黃尊素作品集的流傳脈絡的結論,即清遠堂本《黃忠端公文集》,是最早被刊印發行的黃尊素作品集,在這之前,黃尊素的遺集一直未刊印發行過,是被其子秘藏于家族里,直到許三禮見而刊之。
如前所述,由于黃尊素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與歷史地位,他的作品集在清代并沒有被廣泛傳播開來,《四庫全書》也未著錄。從現有版本情況來說,除了前文論及的清遠堂本外,只有清道光中《乾坤正氣集》里所收錄的《黃忠端公集》,而且我們知道,《乾坤正氣集》是選錄本,即并非全本收錄的,這里的《黃忠端公集》是三卷本的,僅是清遠堂本的一半,而且由于《乾坤正氣集》之前除了清遠堂本之外,并無其他流傳于世的黃尊素作品集,因此有理由推斷,《乾坤正氣集》中的《黃忠端公集》,很有可能就是清遠堂本《黃忠端公文集》為底本選錄的,在后期校勘中,也進一步印證了這種可能。在有關明代別集比較權威的版本目錄學書籍中,如《中國叢書綜錄》著錄《乾坤正氣集》之《黃忠端公集》三卷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清康熙清遠堂六卷本《黃忠端公文集》;《千頃堂書目》著錄《黃忠端公集》六卷本,當是作者黃虞稷在黃尊素家族中所見到的黃尊素的遺集,或者就是清遠堂本;《明別集版本志》中亦著錄的是清康熙清遠堂六卷本《黃忠端公文集》。因此,《黃尊素集》整理可資利用的本子僅有清遠堂本和《乾坤正氣集》本。雖然如此,清遠堂本由于出于黃尊素家藏,并流傳有序,版本質量是較高的,所以整理工作即以清遠堂本為工作本,參校以《乾坤正氣集》本,再綜合各方面史料進行參考。
二、黃尊素的生平介紹與當代研究現狀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明代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初授南直隸寧國府推官。按其后人黃炳垕所撰《黃忠端公年譜》記載:“殿試,第三甲一百八十二名。”以明清科舉慣例,殿試中成績最優者會被授以翰林院官職,次之者則被安排在京城各部中擔任官職,再次之者才被外放做地方官。尤其在明中后期,要進入帝國權力核心之內閣,則必須有翰林的出身。所以說,黃尊素雖然在中年考中了進士,但無論是科舉名次,還是政治前途,都不是非常有利。可即便如此,黃尊素本著一名士大夫的良知與擔當,上任后就顯示出了其清正操守與機智干練,“時湯賓尹為宣黨魁,聲焰懾天下。官其地者,必受牽挽。尊素至,賓尹輒自斂飭。有大姓置私獄殺人,尊素黥其僮客六七人,一郡股栗。”天啟二年(1622年),由于在地方上政績突出,升任山東道御史,當了御史之后,黃尊素恪守御史之責,一年上疏十三次,論軍國大事。其后魏忠賢閹黨集團逐漸得勢,黃尊素為此深憂國運,于是他竭力維持東林黨人的團結,將勇氣與智慧并用,與閹黨進行不屈斗爭,但還是難逃魏忠賢閹黨集團的忌恨和迫害,于天啟五年(1625年)被削籍,次年被魏忠賢矯旨系獄,在獄中,黃尊素被拷掠備至,但他始終堅強不屈,與同時被捕的東林黨成員互相吟詠砥礪,最后于當年從容就義。史載:“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朔日也,年四十三。”錚錚鐵骨,道德文章,標炳千秋!史稱“東林七君子之獄”。崇禎帝繼位之后,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得到了應有的清算,黃尊素被平反昭雪,贈太仆寺卿,南明福王時追謚忠端,再贈兵部左侍郎,公死后,其子黃宗羲繼承了他愛國遺志。
到目前為止,所知的專門針對黃尊素的研究論著領域尚屬空白,同時黃尊素作品集一直以來也未嘗經人整理點校,我有幸值此整理點校《黃尊素集》之際,在對黃尊素作品進行細致閱讀與思考的基礎上,以文本為依托,深入研究黃尊素的政治思想,文學成就以及他的思想行為對其子黃宗羲及后世人的啟迪,力圖還原黃尊素應有的歷史地位與學術貢獻,在此領域進行初步研究,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學界的重視。
三、黃尊素的政治思想
黃尊素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秉持一顆正直之心的忠君愛國思想,茍利朝政,奮勇自諫;其二是充滿智慧與大局意識的政治斗爭策略,在團結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閹黨集團展開的斗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首先是他一心為公的忠君愛國思想,具體從三疏表現出來。明熹宗繼位之后,隨著魏忠賢的蒙蔽日益加重,熹宗亦越來越不思朝政,朝臣們懾于魏忠賢淫威,往往不敢直言,而黃尊素不忍視朝綱敗壞而不顧,先上《請用講學名賢疏》:“群奸之推刃,不遺余力;大冶之真金,只此數人……今求所謂宿儒大人者,寧能舍此諸臣乎?且今日之乏才,亦已甚矣……伏唯皇上毅然剖斷,收天下之老成,主持國是,除天下之頑鈍,維挽世風,國家其庶幾有起色乎!”勸熹宗愛惜人才,親賢臣而遠小人。但是,奏疏上后并未引起熹宗的注意,到了天啟四年(1624年)二月,京城“十日而晦風,經旬一日而地震三次也。”黃尊素抓住這次進諫的時機,上《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以為迂,浸淫不止,異日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此中隱禍,尚未敢深言也。廷無謀幄,邊無折衡,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于此時兼聽并觀,進賢退不肖,徒事唯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仇,皇上獨不為社稷計乎……今當災異初警,人心未有不惕。”用災異來警醒熹宗,注意自己為政之失,更重要的警惕魏忠賢閹黨集團的禍國亂政。不久繼上《劾奏逆閹魏忠賢疏》:“皇上不于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于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余力。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群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可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凈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繼將以皇上為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黃尊素是熟讀經史的,他深知宦官專權對國家的巨大危害,在此直言警上,非有大道擔當者不敢為此。諫言已經說得很懇切了,甚至將可能導致的可怕災難也擺在了熹宗面前,同時,也將矛頭直指魏忠賢的命門。果然,這三疏遇到了魏忠賢的極大忌恨,最終自己慘遭削籍罷歸。
其次,黃尊素對閹黨的斗爭是充滿智慧的,懂得把握斗爭的時機和輕重緩急,團結東林黨內部,盡力從全局上把握形勢,而不是一味拼死抗爭。
此處即以與楊漣等三人的交往為例。首先是楊漣,楊漣是東林黨魁首之一,為人中正不阿,但與閹黨的斗爭卻只顧一味剛烈而不講究策略,楊漣上《二十四大罪疏》欲置魏忠賢于死地,在楊漣將要上此疏彈劾之前,黃尊素就已產生了隱憂說:“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果然上疏之后,魏忠賢從中作梗,不但熹宗未得實見此疏,反而楊漣將自己置于危機之中,此時黃尊素勸楊漣趕快辭官抽身:“以為在今堂翁唯有一去……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然而楊漣不以為然,最后果被黃尊素料中,楊漣被魏忠賢下獄迫害慘死。
第二位是魏大中,魏大中借機彈劾閹黨骨干魏廣微,而彼時魏廣微只是私下交通魏忠賢,并未公開倒向閹黨陣營,黃尊素由此分析:“南樂(魏廣微)以閹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一經論到,則南樂之羞不可復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為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為青天白日之魑魅矣。”但身為好友的魏大中此時正義憤填膺,哪里肯聽黃尊素的勸告,毅然彈劾魏廣微,結果又確如黃尊素所料,魏廣微馬上給魏忠賢一份東林黨人的名單,從此魏忠賢就開始以此名單迫害東林黨人,流毒不淺!
第三位是阮大鋮,他與黃尊素私交很好,起初阮大鋮也是東林黨人的一份子,但東林黨內其實并不十分團結,黃尊素敏銳地察覺到了不團結內部所可能帶來的危害,告誡阮大鋮:“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后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自兄之長吏垣也,邀弟與魏廓園、章魯齋、陳岵月四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膽。酒未寒而終養之疏已出矣,于是疑者四起,謂兄與同事諸君子不合。”阮大鋮受到東林黨內部斗爭排擠而上疏辭官,黃尊素深為之痛心和隱憂,果然其后不久,阮大鋮亦公然投入閹黨陣營,南明時甚至成為閹黨魁首。從這三件事中,我們不難看出黃尊素在政治上的深謀遠慮,然而黃尊素如此苦心勸友,并非怯懦,而恰恰是經驗與智慧的表現,用他自己的話就是:“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事,有一畏死之心固為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為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
四、黃尊素的文學成就
許三禮在序文中這樣評價黃尊素:“文章節義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疊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公者不過數人而已。”許三禮的評價是否存在溢美之詞,我們都可保留自己的看法,不過接下去許氏對黃尊素詩文還有一條更為客觀的評價:“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前文已經領略了黃尊素的道德思想,而且從他奏疏行文來看,的確“理明而辭達”,那么。“文如其人”,道德高尚的黃尊素,其詩文也確實頗有韻致,并且亦飽含思想。從《黃忠端公文集》文本來看。最能體現黃尊素文學成就的部分就是他的詩賦,這些詩文體現著黃尊素的志趣與情感,讀來動人心魄。
許三禮上文中以“平淡”二字歸結黃尊素詩文的風格,的確平淡雅趣風格之詩文在黃尊素文學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亦絕對不止于此。先就黃尊素的詩而論,明顯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尚未與魏忠賢閹黨集團展開激烈斗爭前的詩作,這個階段內的黃尊素,主要是在詩中流露著文人士大夫恬淡的雅趣與抒發自己的抱負。如其早年所作之《馬上》:“層冰積雪逗村家,半去春光柳未芽。一日鳴驄南陌上,黃鸝已鬧杏頭花。”文人游春之閑趣躍然紙上。再如《水陽舟中》一詩:“敬亭朝發隔重岑,詩卷相隨度水濤。雜羽竟投春樹密,孤竿自釣晚蒲深。才舒望眼波光白,恰送輕舟月魄臨。時序漸移炎氣近,快風蘋底正開襟。”一派初夏舟中的瀟灑神態,如可親見青年黃尊素閑逸的文人風采。還有《再渡晼上懷虞九階二首其一》:“江頭五月片帆過,汩汩連天岸亦波。彈指寒崖唯落木,使行重到聽漁歌。”將對好友的懷思寄托于一片深秋江景中,淡泊曠遠而思韻深沉。總之,閑淡是黃尊素這一時期詩作的主基調,再加上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詩亦作于這個階段,難怪許三禮會將黃尊素詩風概括為“平淡”二字,但他這一階段的詩風絕不局限于此,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抒發自己的志向抱負,如《寄眺軒漫興八首其五》:“只愁用劫長安局,應笑施顰優孟兒。海內豈無匡濟者,漫將霄漢費人推。”將自己比作時局的匡濟者,一抒抱負。在為官之后,也是將自己的志向抱負寄托在為民之上,如《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三首其一》:“疏林葉盡晚香清,落日征塵一騎輕,快睹至尊親召對,民風採取上瑤臺。”雖非黃尊素親自上京面圣,但他亦將自己關心民瘼,為民請命之志寄托在了同僚循吏身上。當然,當黃尊素看到百姓受到欺壓時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在《早發山中》指責朝廷對百姓增稅剝削:“況逢缺餉增輸日,天意將何慰蔀居。”當他看到遼東戰局失利,則又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憤,一吐報國雄心:“力盡供毛穎,名稀到帝疆。馳駈愁拙計,樸訥恥時籹。壯士誇如虎,雄心欲掃狼。愿言各努力。昂首向云驤。”這是一位有著良知的士大夫對祖國的一片赤誠告白!
第二個階段是黃尊素參與東林黨,對魏閹集團進行激烈斗爭的時期,這一時期其詩作的風格很明顯,即對國事日非深憂與對奸佞的痛憤!他的詩句時常對那段黑暗時光進行鞭笞:“漫道三綱與五常,卻來個個說黃粱。”“見運知軍苦,逢官欲淚涔。江南民力竭,憂國思難禁。”當然,黃尊素更是借古諷今,對閹黨進行了深刻批判:“悠悠時事不忍言,獨立長吟《出塞》篇。君不見靖康末、紹圣前,壞人家國總諸‘賢’。往事下場殘史在,洛陽流涕亦徒然。”他痛恨魏閹奸佞:“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自推萬里城。只恐階前鞭檜者,此身半是鐵熔成。”將魏忠賢直接比作秦檜,但又悲嘆扳倒他的困難與無奈。同時,他對被魏閹所害的正直同僚則飽含嘆惋:“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閽。于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他只能一邊痛斥著魏閹集團,與他們作堅決斗爭:“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嬉。”一邊激勵東林黨同僚,不畏艱險:“壯士于今須努力,醉看寶劍血嘗丹。”
黃尊素被閹黨迫害削籍到就義獄中,是他詩作的第三個階段,此階段詩作有對官場與安危的曠達,同時也對人生多了幾分禪意的理解。被削籍之后,他并不眷戀官位:“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蚤,白云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射鷹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顯示出了一種道在我而無所懼的曠達之情,當得知閹黨迫害日深,禍將不遠時,依然保持著這種精神:“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鴻何所思。”然而,在黃尊素削籍后的詩作中,我們亦看到了此前從未出現過的,充滿著禪意的詩句:“廢興有命須參破,驢背明朝再詠詩。”“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韻一般禪。”“耳旁除絮語,醉里學逃禪。”似乎詩人已厭倦世事,開始流連詩酒了。這雖有受明末士大夫普遍好禪之風的影響,但亦可從黃尊素詩這前后反差中看出他削籍后內心的落寞,他希望借助禪來使自己忘卻憂國,然國已不堪,他只能用曠達與禪意來掩蓋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最后,當他不免于被害之時,他終于得以一泄胸中的浩然之氣:“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目,唯取忠魂泣鐲鏤。”由此可知,黃尊素并未放下過憂國憂民之心,當他賦此絕命詩時,他得以用厚重的生命直刺閹黨的罪惡,此時的黃尊素更無所畏懼,他與道同在并快然自足!
黃尊素的文學成就,除了詩外還有賦,這里舉他最精彩的一篇《浙江觀潮賦》加以說明,這篇賦,不僅層次分明,韻律精到,而且生動地描繪了浙江觀潮大會的盛況,可謂從古至今寫錢江潮不可多得的佳作。首先他寫出了八月十八觀潮大會之盛:“油璧接軫,繍镼盈途,員冠峨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虛。”接著,他用生動的筆觸描繪了潮水從遠處而來的過程:“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挲目睛,指點云煙,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擊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潮水如約而來,進入高潮:“及其兩山迫肋,沙潬中垾,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蕩而似判。吳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潮過之后,漁民又“潮上漁捕,波澄如故。”一切恢復平靜。能將錢江潮全程盛況寫得如此生動傳神,亦足見黃尊素在文學上的造詣。另外,他的《清景賦》和《兩游剡湖記》等,或氣勢磅礴,聲韻鏗鏘,驚心動魄,或鋪采摛文,情致悠遠,佳句迭出,展現出黃尊素文筆的變幻多端,極富才情與文采,將之列入中國古代優秀詩文之林,亦是當之無愧的精品。
五、黃尊素對黃宗羲的影響及給我們后人的啟迪
許三禮對黃尊素思想的結語為:“公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的確,從黃尊素生前之所為來看,他是一位用實際行動踐行理學思想的君子。因此《明儒學案》也將他收錄其中,對他這樣評價:“先生以開物成務為學,視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茍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為硁硁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疏,以通記為粉本,不復留心于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即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明末受王學左派流鄙,文人大多空談心性,空疏誤國,而以黃尊素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卻倡導程朱之學,提倡格物致知,同時將其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系,呼吁經世致用之學,學問一本乎經術道義與現實政治,這對其子黃宗羲后來的治學路徑有很大的影響,而黃宗羲后來那部經典名作《明夷待訪錄》中那種對現實政治傾注強烈關注,充滿著社會責任感的精神,有理由相信,在較大程度上是繼承了其父黃尊素之思想的。同時,對于黃尊素的學問,其子黃宗羲也是很佩服的:“公精典故,故言事皆有原委。”黃尊素不僅精通理學經術,對歷史掌故也頗有研究,往往考證得當,發明精深。如他的《宋科目考》、《宋賦考》與《說略》中對明代掌故的考證與評論,都能看出他治學的功底與思考的深度,這一切也對黃宗羲后來所開創的以嚴謹著稱的浙東史學派影響深遠。另外,黃尊素的另兩子黃宗會和黃宗炎,亦是一代經學與詩文名家,與黃宗羲并稱“浙東三黃”,應該說與黃尊素的言傳身教是密切相關的。
前人留給我們數量極其龐大的文化遺產,別集更是在其中占有極大的比重,整理這些別集,往往能讓我們發現很多尚未受到關注卻富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們去探究!
參考文獻:
[1](清)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清)陳鼎.東林列傳[M].揚州:廣陵書社,2007.
[3](清)查繼佐.罪惟錄[M].濟南:齊魯書社,2014.
[4](清)黃宗羲.明儒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6](明)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7](明)劉宗周.劉宗周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8](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10]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2](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崔建英.明別集版本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4]張永剛.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活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作者簡介:黃成蔚,男,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