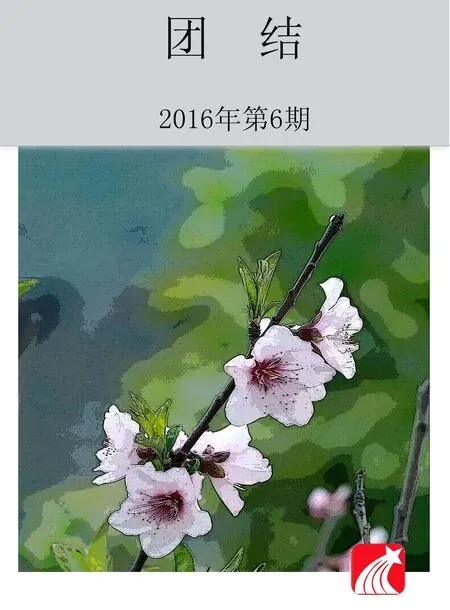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甄別難”現象須引起關注
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甄別難”現象須引起關注
隨著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推向深入,社會組織的活力得到不斷激發。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各地社會組織管理部門對于新登記社會組織是否屬于直接登記范疇存在“甄別難”的現象,須引起關注。
根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和相關文件的要求,目前各地社會組織管理部門均執行“新成立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的規定。而包括政治法律類、宗教類、涉外類等在內的其他類型社會組織的登記仍根據傳統的登記方式,由業務主管單位和民政部門雙重管理。但在實際操作中,一些社會組織管理部門面臨著社會組織類型“甄別難”的現象。以寧波為例,目前全市存量的直接登記社會組織約占到登記社會組織總量的4%-5%,而新成立的社會組織中大約17% -18%屬于直接登記的范圍。而隨著政策門檻的不斷降低,直接登記社會組織的數量將不斷增長,并逐步在新登記社會組織中占據“大頭”。這就對社會組織管理部門的分類、識別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原因是:
一是社會組織管理部門力量有限。基層社會組織管理部門作為民政部門的內設機構,編制數量偏少,很多縣級社會組織管理機關只有3-4人,一般工作人員僅2-3人,且既要承擔政策制定工作,也要參與社會組織的有關具體事務。以寧波市為例,市一級登記社會組織總量大約在1000家左右,專職管理人員僅4人,人均管理達250家。人員力量的缺乏使管理機構難以深入了解登記的社會組織,對其真實性質的甄別存在困難。
二是社會組織的類型判斷客觀上存在難度。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相關材料由其自行提供,而上述材料存在不盡不實的可能。另外,部分將自身性質往行業協會商會、科技、公益慈善、城鄉社區服務等類別“靠攏”的社會組織中,也不乏個別“掛羊頭賣狗肉”、從事法律禁止活動的情況,以合法的外衣掩蓋非法的目的。
部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的規定落實后,社會組織管理部門對于直接登記社會組織的責任由間接變為直接。在目前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社會組織發展良莠不齊的情況下,一旦直接登記的社會組織出現問題,就必然要追究主管部門和人員的責任。對于未來被問責風險的擔憂使社會組織管理部門也不敢放手做事,導致改革政策時效性大打折扣。
鑒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推進登記管理工作的社會化。建議通過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四大類直接登記社會組織的前期申報材料委托專業社會機構進行審核并提出意見,以紅、黃、綠三色分別對應不予登記、暫緩登記和予以登記三個評級,為社會組織管理部門決定是否準予登記提供參考。在此基礎上,建立預審中不予登記社會組織的權利救濟渠道,提升政府部門的甄別效率。
二、通過部門協同強化社會組織的后端管理。建議改變過往社會組織評級中重登記、輕管理的情況,通過統一的社會組織動態管理信息平臺,由同級各政府部門將職權范圍內發現的如違法運行、超越登記的活動范圍等社會組織的有關信息及時加以標注,為社會組織管理部門的管理、處罰和清理提供堅實的保證。(姚福波,民革寧波市委會鄞州區二支部黨員)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