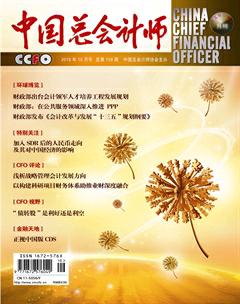人民幣加入SDR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為了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我國經濟年均增長必須保持在6.5%以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需要達到60%。但是,現階段我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結構性和深層次問題,存在不容忽視的內在脆弱性。略微的外部擾動,都會給這一過程帶來不確定性影響。那么,人民幣加入SDR會對我國的實體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下文從兩個方面來論述。
一、人民幣加入SDR的實體經濟背景
人民幣加入SDR,恰逢我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的實體經濟面臨不少挑戰。
(一)實體經濟脆弱性凸顯
以前大家都講我國經濟的韌性好,但是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國際范圍內產業升級加快,我國實體經濟的脆弱性日益顯現。
1.創新能力薄弱長期制約中國實體經濟發展
長期以來,多數中國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較弱,科技成果轉化乏力,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出口產業多屬于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較少的研發投入反過來又制約了企業吸收新技術的能力,如此形成了惡性循環。中國出口商品多利用國內綜合要素成本低的優勢采用低價策略占領市場,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長期居于全球生產鏈條的底端。美國經濟增長中科技的貢獻達到70%,中國卻不到30%。科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低,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2.貿易大而不強
從“量”上看,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占世界總額的八分之一左右,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企業占90余家,中國成為毫無爭議的貿易大國,但從“質”上看,中國距離成為貿易強國的目標仍任重道遠。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單一、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強、價格敏感性高、關鍵技術和元器件多來自國外,不僅生產受制于人,而且利潤率較低,缺乏貿易談判定價能力。另一方面,我國知名品牌企業數量不多,競爭力不強,中國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跨國企業多集中于能源公司和大銀行,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科技創新型企業。
3.經濟結構失衡
實質性供給不良與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制約了經濟發展。不少沿海企業仍從事傳統加工工業,沿用低效的生產技術和方式,導致市場空間被大量廉價易淘汰的產品占據,造成實質性供給不良。我國長期的“需求引導供給、供給改善需求”的發展策略,過多注重“量”上的滿足,過少強調產品的質量和品牌。一旦收入水平提升,需求檔次提高,或者來自國外的低端需求數量減少,國內很多行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產能過剩,以及出現不得不到國外或通過代購方式購買高質量產品的現象。
市場機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小企業發展艱難。由于思想觀念以及體制機制存在問題,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失衡,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居于一個次要的地位,中小企業無法進入一些盈利較高的、新興的行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在中小企業金融支持方面鮮有作為,導致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融資困難等現象長期得不到解決。中小企業發展過程因多元化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而缺乏活力,給新型城鎮化帶來如何解決就業問題、如何保持中國經濟的柔韌性和彈性等巨大挑戰。
(二)國際環境出現不利于我國轉型升級的苗頭
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至今未能恢復,國外重新開始重視制造業也對我國實體經濟構成了不利條件。
1.外部需求仍然低迷和不足
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仍處于金融危機后的溫和復蘇階段,經濟增長乏力,距離徹底走出危機陰霾還有一段時間。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雖快于發達國家,但因其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經濟的對外依賴性較強,抵御外部沖擊的風險管理能力較差,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資本外流加劇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普遍放緩。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外部需求的下降,必然給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帶來下行壓力。
2.中國制造面臨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
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著手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反思金融“脫實就虛”現象,要求金融機構去杠桿,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同時,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再制造業化”戰略回歸實體經濟、尋求產業轉型、大力促進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提升本國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美國的“重振制造業計劃”“高端制造計劃”,日本發展機器人、新能源汽車、三維(3D)打印和信息技術(IT),德國推出高科技的“工業4.0”計劃,法國提出“工業真行新計劃”。主要工業國家的這些制造業計劃提高了中國進入高端制造市場的門檻,有可能進一步拉大我國與主要工業國家在高端制造方面的差距,對于我國發展創新技術和產業升級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
(三)國際產能合作面臨供需兩端的壓力
從需求端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首當其沖。新興經濟體發展主要依靠低價格、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中國向這些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很有可能遭遇東道國設置的各種壁壘。從供給端看,發達國家逐漸加強對東南亞地區、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轉移和直接投資的力度,與中國相比,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具有明顯優勢,產品替代性弱,較少遭遇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進入壁壘,這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無疑會產生較大沖擊。
二、人民幣加入SDR對實體經濟的潛在影響
人民幣加入SDR后,短期內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有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潛在影響不可小視。
(一)短期資本流動容易造成實體經濟資金鏈斷裂
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中國為全球提供了一種儲備資產,必然增加全球資產管理機構對人民幣的持有和交易需求,進而要求資本流動更加自由。而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幣資產價值的匯率敏感度,容易引發大規模的套利短期資本流動。從國際經驗看,短期資本受心理預期的影響較大,具有非理性,短期資本的快速流動常常會擾亂外匯市場的正常秩序,并傳染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既帶來利率、匯率的大幅波動,影響實體產業的融資成本、外債和并購活動,又滋生股票、房地產、衍生品等資產泡沫。一旦泡沫破滅,就會爆發金融危機,降低實體經濟的貸款獲得性,甚至出現資金鏈斷裂,造成企業破產倒閉。
(二)加大資源錯配和經濟泡沫化風險的概率
目前,從對外投資增量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了,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額已經超過了引進外資額。人民幣加入SDR,強化了人民幣的國際計價與結算功能,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對外人民幣貸款、發行人民幣債券等方式投資收益率更高的地區和多樣化的國際金融產品,有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如果中國優秀的制造企業在全球資源配置驅動下大規模“逃離本土”,形成類似于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經濟“空心化”,將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結構穩定性和持續發展能力。
目前國內第二產業的平均投資收益率不高,容易導致資金流向回報率更高的股市或金融交易產品,發生資源錯配現象,加大金融資產擠壓實體經濟資本需求的風險,使得實體經濟發展“缺血”,得不到必要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