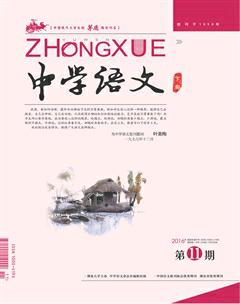根植想象傳情達意
陳鶴
“虛實”,原是中國畫中的傳統技法,是指圖畫中筆畫稀疏或空白部分與勾畫出的實物、實景以及筆畫細致豐富的地方。化用到詩歌中,“虛”即指直覺中看不見摸不著,卻又能從字里行間體味出的那些虛像和空靈的境界。而“實”,就是寫眼前所見所聞。虛實相生,相輔相成,就能避免方法上的刻板平直,更能準確地傳情達意。
“重團聚,傷別離”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感情。千百年來,故國鄉土之思、骨肉親人之念、摯友離別之感,牽動了多少人的心弦,“別離”自然成為我國古典詩歌中的重要內容。虛實相生,作為一種常見的表現手法,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運用范圍很廣,尤其表現在離別詩中,它更有其獨特的內涵和作用:
一、景物相連,虛遠實近
在那十里長亭、南浦渡口,“執手相看淚眼”,揮不去的是滿腔的離愁。眼前的景物都染上了哀怨,這些景物就成了離別詩中情景交融的實景。但這些還不足以代表詩人心中所有的哀愁,詩人更擔心在漫漫長途中,友人會踏上什么樣的坎坷之路呢?所以,詩人想象友人在離別后一路上所經之地、所見之景,仿佛自己的靈魂都隨同一路的清風明月、高山流水,陪伴在友人的身邊,依依不忍分離,這些想象之景構成了詩中重要的一部分:虛寫之景。
如王昌齡的《送魏二》:“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舟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里長。”前兩句是實寫,交代了該詩是送別詩,點明了宴別的地點“江樓”,季節是橘柚飄香的秋季。在秋風瑟瑟、秋雨連江之時,詩人把友人送上了船。后兩句轉為虛寫,詩人想象和朋友分別后,朋友在遙遠的瀟湘之上,愁聽猿猴清幽的啼聲,夢里也無法排遣。這些虛想的情景,既是詩人對朋友旅途寂苦的擔憂,也表達了自己對朋友的留戀之情。虛實結合,相輔相成,擴大了詩歌的意境。
再如杜牧的《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心懸旆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頷聯的前一句虛寫裴坦前往舒州時必經的佛教名山九華山,后一句實寫眼前兩人依依惜別的送別地點清弋江村,都表現了對友人遠行的關切和依戀之情。
所以,想象友人前行所經之景并加以虛構描寫,成為離別詩內容的一大組成部分。這種虛實結合手法的運用,既抒發了那深厚的友情,更豐富了詩歌的內涵,使得詩歌意蘊無窮!
二、情感物化,虛情實喻
在離別詩中,詩人為了抒發自己的一腔深情,又覺得難以把那說不清、道不盡的情感表達得清,便選取那有形的、具體的事物來與自己的情感作比,在比較中突出自己的情意之深。這種化虛為實的手法,也是虛實相生手法的一個組成部分,目的是為了使詩歌的內容更為生動形象。
如唐李頎的《絕句》:“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后兩句即表達自己的愁情,詩人選用東海之水來和自己的離愁相比較,看哪一個更深,目的是為了突出自己的愁意之濃,連東海之水都比不上。這樣,無形的愁,成了有形之物,可測可量。
又如李商隱的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人思念那離別的意中之人,用虛幻的喻象,互為對比,把那受時空限制的愛情的痛苦之情和彼此之間心靈默契的喜悅之情表達得生動細致、深情動人。這兩句的虛像與整首詩的實景描寫,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完美組合,使全詩既情思濃烈,又迷離隱約。
三、以己推人,虛你實我
在離別詩中,詩人抒發自己思念家鄉、思念親人情感的時候,不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撇開自己,反從思念的對象著筆。如同清人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所云:“不說我想他,卻說他想我,加一倍凄涼。”此類虛想往往被描繪得細致生動,情景栩栩如生。詩便有虛有實,情景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如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一聯詩人從正面直寫自己作為一個異鄉客在佳節之時格外思念家鄉親人的感情,后一聯詩人卻別出心裁,他不去寫自己,卻反從家鄉的親人寫起,想象兄弟們登高時,思念起遠在異鄉的自己,尤其是“遍插茱萸”這一細節描寫,使得想象的情景真切動人,詩歌的內涵就更為豐富了。
又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該詩是杜甫被安史叛軍擄到長安時所作,本是表達詩人望月思家的心情;但全詩都是從對方落筆,無一字寫自己思家,卻字字表現家人對自己的思念,尤其是妻子對自己的思念,更用小兒女不懂得思念自己來反襯那唯一懂得思念的只有望月的妻子。用“濕”“寒”二字,表現妻子在月下佇立良久,更體現出妻子對自己的情意綿綿,也從反面烘托出自己思家的心切。如此精妙的用筆、真摯的感情,正是此詩流傳千百年的奧秘所在。
四、移情于物,虛物實己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李白在《勞勞亭歌》中寫道,天下最傷心的地方,就是在那送別的勞勞亭,不僅使人肝腸寸斷,就連春風也為之動容,不忍見那離別的場面,所以不讓柳條變青,讓送別之人無枝可折。這是詩人的奇想,他把離別與春風這兩樣毫不相干的事物聯系在一起,賦予沒有知覺、沒有感情的春風以人的知覺、人的感情,使它成了詩人的情感化身,這就是托物言情、移情于物、虛物實我,表現了詩人豐富的想象能力,展現了詩歌無限的想象空間。
如唐張說的《蜀道后期》:“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在這首歸思詩中,詩人歸家的心情可與日月相爭,但卻因有事耽擱而未能及時返回洛陽。詩人不直接抒寫這一延期之恨,而是把秋風擬人化,怪它不等待自己先回了洛陽。這種虛寫秋風、實寫自己的手法,使得詩歌別具情趣,既不落于俗套,又顯得自然巧妙。
最典型的莫過于杜甫《春望》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兩句,表面上寫面對離別,花也濺淚、鳥亦驚心,其實詩人移情于物,以花鳥擬人,表現詩人憂傷國事、眷戀家人的殷切情意,同時也使詩歌的含蘊更為豐富了。
“虛實相生”,作為中國古代詩歌中常見的藝術手法,已為大家熟知。特別在古代離別詩中,它表現的內容更為豐富;但它根植于“想象”的特點卻是不變的。正因為詩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才使得詩的內涵不止于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更可以飛越廣袤的空間,穿越悠長的歷史,打破形體的約束,給讀者帶來更真切、更細致、更深遠的獨特藝術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