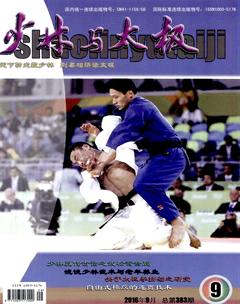俠義江湖中的英雄特質
龔鵬程

《花月痕》第一回說:“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隱。”在俠義小說里,一般總稱俠客豪杰為英雄,而這些英雄則是在社會心理普遍追求向往正義的情況下才被民間普遍崇仰的,所以他們代表了一種正義天使的形象,專門紓人急難。
然而,英雄崇拜本身也是個復雜的問題,可以說由于人間的不公平,我們總希望能出現英雄予以救濟,但英雄的意義遠超過這些。每個民族,無論在遠東、在非洲、在北歐,也無論是中世紀、是上古、是現代,英雄總在人群中出現。從圣經中的英雄參孫、波斯的英雄魯斯丹、巴比倫的英雄吉爾伽美什,到美國漫畫及電影中的超人,均是如此。對英雄本身的向往,是每個民族和時代的夢——英雄夢。
在這個夢里,英雄必定帶著他超人的力量降生,很早就顯出他與眾不同的神力,如嬰兒時期的赫拉克勒斯殺死兩條巨蛇,年輕的亞瑟王抽出石中劍,哪吒打死龍王三太子,等等。然后,他常常有一位強而有力的保護人、導師來幫助他,以使他能執行許多困難的任務。而且,他也常有一些能力也很不錯的朋友輔翼他,并補償英雄所顯露出來的弱點。他常獲得寶馬神矛等神兵利器,這也保障了他在未來與邪惡勢力搏斗時能夠成功。然而,經過一連串勝利之后,超人的英雄終于也常常因為某些因素,例如天生的弱點、神的旨意,或驕傲、不經心而失敗,并以“英雄式”的犧牲結束生命。注意,近代武俠小說也在重復此模式。
但是,為什么每個人都崇拜英雄,都有點幻想自己就是英雄呢?為什么每個英雄故事都不脫以上這樣的模式?這不是渴望社會壓抑獲得補償所能解釋的,它必然有著更深刻的心理因素深入于人存在之處境及意識發展的過程里。
榮格(CarlG.Jung)曾解釋,英雄式神話的根本作用是發展個體的自我意識。他認為,在每個人意識心靈中都各有其陰邪面,其中含有邪惡、有害和破壞性的成分。而在人格成長的過程中,自我必然會跟陰邪面發生一些意識的沖突,與“黑色的禽獸”搏斗。在人從原始到意識的奮斗歷程里,這種沖突就常由原型英雄跟宇宙邪惡力量互相爭抗來表現。所以,在個體的意識發展中,英雄意象即是顯示自我征服潛意識心靈的象征。
自我終究必須沖出潛意識和不成熟的束縛,因此英雄便也必須跟巨龍、怪獸、奸臣、惡霸等格斗。而這種格斗又是沒有必勝的保障的,英雄雖然天資神武,但也常被鯨魚怪獸吞食、被奸臣陷害、為國捐軀,這就是英雄的祭儀,表現在死亡與再生之間,以自己做犧牲,強化了英雄的意識。
這才是英雄之所以出現的心理因素。我們當然也不否認,英雄之創造與崇拜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然而榮格此說實在替我們找到了一條很好的解釋途徑。例如,英雄救美是大部分英雄故事中很被強調的一環。這種救美的行動通常都表現了英雄的氣魄與勇力。他能對抗邪惡,從水深火熱的困局中救出弱女,令人敬佩:而此女又為美女,則更令人欣賞。雖然這些英雄后來不一定會與此美女結為鴛侶,但在搭救的過程中英雄必然是貞定剛毅、毫無邪念的,充分表現出敬重守禮的美德。從話本小說《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警世通言》卷廿一)、章回小說《粉妝樓》里《粉金剛千里送蛾眉》(五一回)、《三國演義》里《美髯公千里走單騎》(廿七回)護送二位皇嫂,到歐洲中古的騎士、現代漫畫的超人,無不如此
但是,在許多故事里,英雄也是憎厭女人的人。如俠盜傳統中有所謂“陰人不吉”的說法。而《水滸傳》里,宋江是何等英雄,但除了吃過閻婆母女的虧,又曾被劉高老婆恩將仇報而陷身縲紲。第二好漢盧俊義也差點兒讓妻子賈氏害死,史進與安道全被姐妓出賣,雷橫被歌女白秀英害苦。潘金蓮鴆死武大,武松若德行武功稍差也會毀在她手里;同樣,若不是石秀機警,潘巧云就送楊雄一頂綠帽還會害了他的命。宋江說得好:“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卅二回)其他各種英雄故事里,英雄雖然不見得皆如《水滸傳》這樣,但也必然是不好女色、不放縱情欲的。
中古歐洲騎士那種不近女色、保持發乎情止乎禮的風范,主要是受到對圣母瑪麗亞崇拜的影響。同樣地,十五世紀的歐洲騎士的盾牌上也畫著武士跪在心愛的女人前面,雖然身后即是死亡。但是,歐洲中古社會在崇拜女人的同時,也產生了對女巫的信仰和迫害。
為什么會出現這么矛盾的現象呢?榮格解釋說:女人即是陰性特質(Anima)的人格化,救出美女,暗示他已成功地解放了陰性特質,使自己得到安心。利用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說,因為陰邪面必須壓抑或克服,唯有不被女色所迷惑、不被陰邪面所擊倒,才能成為一位真正的英雄。
這一類英雄當然并不僅限于俠,像關公、岳飛、秦瓊這些人更符合這種英雄性質并受到英雄般的崇拜,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比任何俠客都更受歡迎、更受崇拜,一般俠義故事也很少像描寫這些英雄一般詳述其出身、天賦,神矛寶馬之類配備,朋友與教師之類輔助,失敗與死亡的悲壯歷程等等。
俠只部分吻合一個真正英雄的條件,雖然許多俠義故事以“英雄”稱呼俠,如《兒女英雄傳》,但他們畢竟不是一個民族心目中真正完美的英雄,他們沒有像關公那樣過關斬將、義薄云天、死后復活、降神于玉泉山一套完整的記錄,自然激不起人們對英雄的向往。
然而,俠是把英雄的某些特質發揮到淋漓盡致的人。例如英雄必然具有超人的能力,俠也強調這一點,而且愈來愈夸張,由擅長拳勇而逐漸成為劍仙,充分展示他具有超人能力的一面,這些引起人們的好奇與驚嘆。
英雄必定要跟邪惡勢力搏斗,俠客亦然。這種搏斗充滿了危險,隨時可能會喪命,這類情節既緊張刺激,又能帶來因罪惡消除后道德得直的寬慰,也非常吸引讀者。另外,俠與英雄一樣,都面臨一個死亡的儀式,但是俠客特別強調這一點,俠義故事塑造出了比一般英雄更壯烈更奇異的形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那是一幀永恒的劇照,《史記》寫荊柯刺秦,祖道易水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流。又前而為歌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嗔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站在理性的角度看燕太子丹和荊柯,此舉可謂大愚。然而慷慨悲歌足令后輩掩袂流涕者,正是這昂揚激烈的情意生命之表現。這種表現,絕對不是道德理性所能規范的,它純屬感性生命的抒放。它面對死亡,選擇了死亡,也借由死亡來完成生命的價值。他們隨時表現出輕于一死的氣概,“輕身一劍知”,死亡對他們來說仿佛就是成就俠士形象的一道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