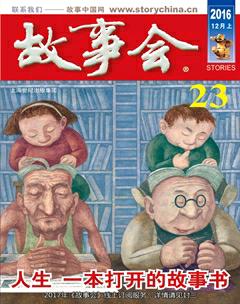15年的牽掛
2001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一封寄自廣西的信,是一個壯族女中學生寫的。我捏著那張從作業本上撕下的信紙,心里隱隱作痛,這孩子寫封信要多大的勇氣啊,還要花8角錢的郵票,能拒絕嗎?就是這一善念,有了彼此15年的牽掛。
從通信中看出,她那個地方,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由于母親事事偏袒弟弟,她與母親產生了嚴重的對峙。而她又處于青春叛逆期,稍有不慎,即會鑄成大錯。一念至此,言辭之間便謹慎起來,總是善言相勸,一開始這孩子還有點倔,但漸漸地,口氣明顯軟了下來。終于有一天,她說,顧伯伯,我知道錯了。我很想來看看您!
平允而論,這孩子頗有些才氣,給我的信寫得文從字順,想象豐富。可惜的是,她讀完初中便不能再讀下去了。主要是父母不喜歡她讀書,家里也不富裕,弟弟又在讀。于是年紀輕輕的她,便離開朝思夢縈的課堂,南下打工去了……
后來女孩也做了母親,與丈夫同在深圳打工,而與我的聯系卻一直未斷。她有時打電話,有時發郵件,傾訴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我呢,以一個“過來人”的口吻,不厭其煩地開導她。她很感激,說聽了我的話,心里亮堂許多。這讓我頗有成就感……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2015年秋,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說是人已到長春了。我一驚之下,忙問清地址,跟妻子一起尋了過去。
見了面,她顯得異常興奮,忙不迭地告訴我:“伯伯,你知道嗎?自從15年前,我們通了第一封信,我就發誓這輩子要見你一面。”又說,這些年疾病總是不斷地折磨她,攢下點錢,全都送給了醫院……現在孩子剛離手,婆家又嚷著要二胎,她好不容易擠了點時間……我和妻子四目相對:也太難為她了!
“伯伯,您不問當年我是怎么找到您的?”
我搖頭。那時來信的很多。
她說,當時她與母親簡直不共戴天。有段時間竟胡思亂想,等哪一天長大了,拿把刀把母親給捅了……直到有一天,她從同學那里借到一本《故事會》,讀到上面一篇故事,不禁心生愧意。故事中說,有個少年不慎掉在一處懸崖上,繼父歷經艱辛把他救了下來。她想,連繼父都有那份愛心,何況血濃于水的母親呢?從此,她便牢牢地記住了“顧文顯”這個名字。事有湊巧,不久她意外在另一本雜志上看到我的地址,就冒昧地給我寫了封信。她回憶說,接到回信的那一刻,人都差點飄起來!
“后來我有能力訂《故事會》了,遇到您發表的故事,我都反復讀。我一直活在對伯伯的感恩和信仰中,您說什么我都信。這些年,我跟母親的感情特別深,往事不敢回首啊!”女孩眼圈紅了……
分手頭一天,女孩神秘兮兮地叫我別轉身,等我回過頭,大約兩米長的《八駿圖》,豁然展現在眼前,為這幅畫,她整整繡了13個月!
女孩說:“感謝伯伯……”我糾正:“感謝《故事會》。”
“對,感謝《故事會》,它讓我認識了您……”女孩說,“我必須訂閱一輩子。伯伯,還能看到您的故事嗎?”
能!為了喜歡我的讀者們,我封筆的聲明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