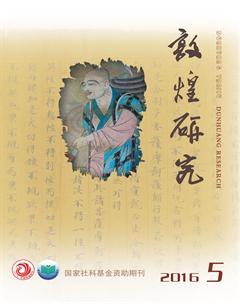西夏時期敦煌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
陳光文
內容摘要:西夏占據敦煌后,在瓜州、沙州建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并委派豪酋大族實行統治。瓜州和沙州位于西夏邊陲,軍事作用突出,因此,西夏在二州分別設立監軍司,負責當地的軍事與行政事務。同時在二州分別設立刺史、轉運司。沙州單獨設立經制司。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通判、習判、承旨、都案、案頭等自上而下構成了瓜、沙二州的職官體系。
關鍵詞:西夏;敦煌;行政建制;職官設置
中圖分類號:G256.1,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6)05-0084-08
Abstract: After having occupied Dunhuang,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established a complete administrative and official system and appointed a local noble family to govern Guazhou and Shazhou. Because the two frontier towns were of significant military importance in the Western Xia, a military office named Jianjun-si was set up in both Guazhou and Shazhou to take charge of local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eanwhile, other offici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i-shi and Zhuanyun-si,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the two towns in addition to the Jinzhi-si, which was particularly set up for Shazhou. The official system in Guazhou and Shazhou was thus composed of various ranking officials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Dutong-jun, Futong-jun, Jianjun-shi and Tong-pan.
Keywords: Western Xia; Dunhua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ficial system
西夏(1038—1227)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建立于中國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全盛時期的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余里”[1]。而敦煌即處玉門關內,漢唐時期一直是溝通中西經濟、文化往來的樞紐。20世紀初,因敦煌文獻與黑水城文獻的發現,產生了以出土文獻研究中古史的兩大顯學——敦煌學與西夏學。西夏時期的敦煌史則屬這兩大顯學的匯聚、交叉領域。關于西夏時期敦煌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劉玉權先生[2]、陳炳應先生[3]曾分別撰文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湯開建先生[4]、魯人勇先生[5]對包括沙州、瓜州監軍司在內的西夏諸監軍司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李昌憲先生則著眼于整個西夏,利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下文簡稱《天盛律令》)對西夏的地方行政制度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6]。日本學者佐藤貴保先生透過榆林窟供養人畫像與題記,對西夏在河西走廊的官僚設置進行了探討,頗多啟發[7]。2012年,著名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先生專門撰文探討了敦煌學與西夏學的關系,指出西夏時期的敦煌是敦煌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同時他結合《天盛律令》的相關記載,對西夏時期敦煌的行政建制進行了簡要的梳理[8]。總體來看,結合文獻史料及莫高窟、榆林窟西夏供養人畫像與題記,對敦煌一地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情況的專門性研究還有待深入。有鑒于此,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探討,希望能拋磚引玉,進一步推動該課題的研究。不當之處,敬請識者不吝指正。
一 瓜州監軍司、沙州監軍司
監軍司是西夏時期設立的兼具軍事與行政性質的地方建制。西夏建國初年元昊在全國設置十二監軍司,《宋史·夏國傳》記載: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啰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9]
《宋史·夏國傳》記載元昊“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眾”[9]13994,《續資治通鑒長編》(下文簡稱《長編》)卷120“景祐四年(1037)”則記載元昊“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10]。湯開建先生根據《范文正公年譜》和在日本發現的司馬光《日錄》均記載元昊時期為十八監軍司,指出二書與《長編》記載相合,認為元昊時期應設置了十八監軍司而非十二監軍司,并指出在宋夏戰爭頻發的元豐、紹圣、元符年間西夏全國監軍司數量最高時至少有二十五個,到仁宗天盛年間變為十七個,西夏后期又裁撤五個而變為《宋史·夏國傳》末記載的十二個監軍司[4]440-449。湯開建先生對西夏監軍司的分期考證,符合西夏根據戰情時局進行調整、增設、裁撤的實際情況。但西夏元昊時期的監軍司數量究竟是《宋史》記載的十二監軍司,還是《長編》記載的十八監軍司,筆者認為應以十二監軍司為是。雖然《長編》景祐四年(1037)記載時期為十八監軍司,但在其后的熙寧四年(1071)、元豐四年(1081)、元祐二年(1087)均記載為十二監軍司。《長編》記載北宋熙寧四年(1071)二月丁巳朔宋神宗批曰:
近諸處覘西賊聚十二監軍司人馬及取齊地名,皆有考據。詳此乃是大舉,慮諸路不大為備,賊至有失支梧。可令陜西、河東宜撫及諸路經略司早為清野之計,毋得輕易接戰。[10]5336
這段記載表明至熙寧四年,西夏仍為十二監軍司之設。同書元豐四年(1081)十月丙寅,鄜延路經略副使種諤報稱:
捕獲西界偽樞密院都案官麻女喫多革,熟知興、靈等州道路、糧窖處所,及十二監軍司所管兵數。已補借職,軍前驅使。[10]7680
表明至少在元豐四年時,西夏仍舊保持了十二監軍司的設置。同書元祐二年(1087)八月戊戌日記載:
已而夏國主乾順盡召十二監軍兵屯會州天都山西南,國母與梁乙逋等率之,對蘭州、通遠軍而營,欲與鬼章連謀入寇。[10]9841
“盡召十二監軍兵”反映出此時西夏監軍司數仍為十二,數量上并未發生改變。這表明至少在元祐二年(1087)八月以前,西夏仍舊保持了十二監軍司的設置{1}。需要提及的是,西夏建國初年瓜、沙二州只有瓜州監軍司而無沙州監軍司,但在《天盛律令》中,共出現十七個監軍司:
十二種監軍司當全部派二正、一副、二同(通)判、四習判等九人:石州、東院、西壽、韋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龐嶺、官黑山、北院、年斜。
五種監軍司均一正、一副、二同(通)判、三習判等遣七人:肅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11]
這表明原有的十二監軍司在西夏天盛年間或之前又有增設。除了原有的瓜州監軍司,在西夏西陲增設了沙州監軍司、肅州監軍司。瓜州榆林窟第29窟出現的“沙州監軍”題名,也印證了《天盛律令》關于設立沙州監軍司的記載。至于在西夏西陲增設沙州監軍司和肅州監軍司的原因,應與北宋紹圣四年(1097)二月喀喇汗王朝攻破沙、瓜、肅三州有關。《宋史·于闐傳》載:
紹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9]14109
《西夏書事》也記載北宋紹圣四年(1097)二月,“于闐國破瓜、沙、肅三州”[1]341。上引《宋史》記載的“甘州”應作“瓜州”。西夏立國之初,宋夏雙方爆發了數次激烈戰爭。北宋聯合吐蕃、回鶻、韃靼及其他部族共同對付西夏,采取各種措施使這些部族對西夏后方形成牽制。而西夏為入侵北宋,不惜舉全國之兵力,如北宋元豐五年(1082)西夏“點集河南、西涼府、啰龐界、甘、肅、瓜、沙,十人發九人,欲諸路入寇,人馬已發赴興州”[10]7848,導致西夏西陲兵力空虛。雖然西夏意識到了喀喇汗王朝的軍事動向,進行了備戰,如《西夏書事》記載:“(元祐八年)二月,以兵備于闐。”[1]335但北宋紹圣四年(1097),瓜、沙、肅三州仍陷落于喀喇汗,表明西夏西陲兵力已不足以防御喀喇汗。喀喇汗王朝在攻下西夏西陲三州后雖然未能長期占據,但已經對西夏河西地區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必然引起西夏方面的重新重視。筆者推測,正是在此背景下,西夏于1097年后重新加強了西陲對喀喇汗王朝的防范,將最西面的沙州升格為甲類的沙州監軍司,同時將原來的甘州甘肅軍司西移肅州設立乙類的肅州監軍司,這樣由西向東構筑了沙、瓜、肅三監軍司的駐軍體系。
按照《天盛律令》的劃分,沙州監軍司和瓜州監軍司均為中等司,其司印為銅上鍍銀十二兩。《西夏書事》關于監軍司的職設記載云:“諸軍并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貴戚豪右領其職,余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數十,不分蕃漢悉任之。”[1]142盡管在以皇帝為首的西夏統治階層里面黨項人居多,但漢人也被任用而委以官職[12]。根據《天盛律令》記載,沙州監軍司設二正、一副、二通判、四習判共九人,瓜州監軍司設一正、一副、二通判、三習判共七人。各監軍司的首長為正監軍使,下設副監軍使、通判、習判,防區的各支部隊,則由“豪右”擔任正副行統[13]。“通判”、“習判”以及《西夏書事》記載的“指揮使、教練使”等職,為監軍司的中級職務,黨項人和漢人均可擔任。根據《天盛律令》記載,沙州、瓜州監軍司分別配有三名都案和兩名都案,二司俱屬于地邊監軍司,因此都配屬十二名案頭。都案和案頭主要處理文書等具體工作,要求必須熟悉文書工作和國家典章律法,而且要頭腦靈活。都案、案頭在監軍司中職位較低,應即《西夏書事》記載的“左右禁官”,此職可由黨項人和漢人共同擔任。同時,根據《西夏書事》敘述語境,除了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等職黨項人和漢人均可擔任外,由貴戚豪右領職的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等監軍司的高級別官員應只能由黨項人擔任。
根據《西夏書事》記載,都統軍和副統軍才是監軍司中的最高長官,要高于監軍使。這在《天盛律令》中也得到了印證。該書第四“邊地尋檢門”中記載:
若正、副統歸京師,邊事、軍馬頭項交付監軍司,則監軍、習判承罪順序:習判按副行統、監軍按正統法判斷。[11]211
正統即正統軍;副統,在“邊地巡檢門”中亦作“副行統”,即副統軍。值得注意的是,《番漢合時掌中珠》記載有正統司和統軍司[14],二司在中書、樞密和經略司之后,但在殿前司、監軍司之前。《天盛律令》記載正統司之司印為銅上鍍銀二十兩,次于經略司銀重二十五兩,但高于作為中等司的監軍司之銅上鍍銀十二兩,表明其司階排序與《番漢合時掌中珠》記載相符,但此外未再見到正統司記載,因此對于正統司職能還不甚清楚。而統軍司,《天盛律令》中未見記載,但上引《天盛律令》中有正統軍和副統軍的記載。史金波先生根據宋夏交戰中,西夏“洪、宥、韋三州總都統軍賀浪啰率眾迎戰”之記載,指出根據《天盛律令》可以推定統軍司是在經略司之下,高于監軍司的軍事指揮機構,其正副將領應是正統軍和副統軍,并認為都統軍可能是正統軍[15]。但這里似乎出現了難解之點:既然都統軍和副統軍是監軍司的最高長官,為什么又同時是統軍司的正副將領?統軍司除了高于監軍司,它們之間還存在什么關系?關于這點未見有學者進行更深入的鉤索,因而對于統軍司具體所指以及與監軍司的關系、區別解釋得不甚清晰,容易引起混亂。
統軍司之名正式出現于乾祐年間(1170—1193)成書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中,但其作為一個機構成立應較早。由上引《天盛律令》第四“邊地尋檢門”記載可知,正統軍與副統軍回京師后,作為軍事事務的“邊事”和“軍馬”要交付給監軍司處理。如果出現問題,習判按副統軍、監軍按正統軍之法處理。《天盛律令》第十三“執符鐵箭顯貴言等失門”記載:
又應派遣執符中,正副統、州府使、刺史、監軍司等俱在,原語同,則彼亦勿分別派執符,當總合一齊派之。[11]472
這表明,正統軍、副統軍雖然是監軍司的最高官員,但仍與監軍司有別。作為統軍司將領的正、副統軍同時兼任監軍司的最高官員,并且高于監軍司之正職監軍使。統軍司與監軍司既有緊密聯系和交叉性,又有所區別。統軍司與監軍司在駐地和轄區范圍上應一致,主要負責監軍司范圍內特別是邊境地區的軍事防御任務,正統軍、副統軍是監軍司部隊的最高統兵將領。如在《天盛律令》第四“棄守營壘城堡溜等門”中記載:
一諸副行統率軍馬防守,住于邊境,在任時期日未滿,及雖日滿但其地上敵人不安定,及聞知有疑,未得局分指示擅自放棄軍寨,并令所率防守軍馬等散去時,住滯出不出,一律與邊檢校、營壘主管、州主等放棄軍溜相同判斷。一正統人住邊境軍寨,無指示放棄軍寨,并令所率防守軍馬等擅自解散時,審計有無住滯、語情輕重,依時節等奏計實行。[11]196-197
除了平時防守邊境、維護治安外,統軍司在戰時還負責帶軍打仗,此時統軍地位仍高于監軍使。如《長編》記載北宋元豐四年(1081)冬十月宋軍與夏軍之戰:
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諜者以謂環慶阻橫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賊界堪哥平十五里,遇賊三萬余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賊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賊小卻,我軍乘之,賊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啰臥沙、監軍使梁格嵬等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侄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我軍通行無所礙。[10]7677-7678
由以上記載可知,此次戰斗中西夏的統軍、監軍使均為黨項人,西夏軍隊的人數達到三萬人之多,有多位統軍和監軍使。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中提到宋軍獲“偽銅印一”,應是西夏機構的司印,該印肯定不是經略司印。《天盛律令》中只記載正統司為銅上鍍銀二十兩,中等司銅上鍍銀十二兩,那么該印只可能是正統司印或監軍司印。遺憾的是,上文并未記載銅印重量,難以具體判斷是哪個司的。由引文還可知,西夏其中一位統軍為國母弟梁大王,即梁太后之弟梁已埋。梁已埋身為國相,雖被宋人記載為統軍,但絕非一般統軍。在此戰中梁已埋身為戰時最高統軍首領,統領和節制各地統軍司統軍、監軍司監軍使等大小將領進行作戰。
陳炳應先生認為統軍司之統軍任命頗多,有作為一個監軍司主官的,有作為幾個監軍司、幾個州、幾個路的統兵官的[16]。筆者則認為,統軍應為一個監軍司的主官。至于作為幾個監軍司、幾個州的,都是西夏根據戰爭規模和需要而調集多個統軍司進行聯合作戰,這時會有臨時設立的總都統軍,統領和指揮各個統軍、監軍等大小首領進行戰斗。如北宋紹圣四年(1097)宋軍攻打宥州:
(八月)丙戌,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差將官王愍破蕩宥州,并燒毀族帳等不可勝計,斬獲五百余級,牛羊以萬數。詔賜出界軍兵特支有差。(惠卿家傳云:七月遣副總管王愍統制諸將入界,二十九日至宥州,其洪、宥、韋三州總都統軍賀浪啰率眾迎戰。愍等擊,大破之,追奔二十余里,斬首五百余級……)[10]11623-11624
韋州、宥州均設監軍司。但宥州監軍司后來裁撤,與洪州并屬于東院監軍司防區[5]86。以上記載也說明,統軍司與監軍司在駐地和轄區范圍上應一致。此外,陳炳應先生還引用《長編》中西夏有“六路統軍”之記載,認為統軍還有作為幾個路的統兵官的[16]13。但根據《番漢合時掌中珠》記載,統軍司在經略司、正統司之后,在監軍司之前。統軍司與經略司之間還有正統司,無法與路一級的經略司相對應。“六路統軍”或可以理解為,西夏根據戰爭規模和需要,調集多個路下的統軍司、監軍司兵力進行作戰,在作戰中,軍隊的調動和統軍的設立具有很強的臨時性和戰時體制特點。
舉凡政制、兵制都有根據形勢而不斷調整變化的特點。陳炳應先生曾指出,西夏后期樞密要通過經略司、正統司、統軍司來調兵,主要是為了分權,是吸收權臣任得敬專政、分裂國土的慘痛教訓的結果[16]13。此誠為得的之論。這一變化也標志著西夏兵制走向復雜化和成熟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軍雖然早在西夏前期就已經出現,但統軍司設立卻應在西夏后期。由上文論述,我們大體推測統軍司應為地方性的統兵機構。統軍司與監軍司彼此區別但又有密切聯系。其聯系是,統軍司與監軍司均司職同一片區域,同屬于地方軍政系統,但統軍司要高于監軍司,統軍司最高將領正統軍和副統軍同時兼任監軍司最高職務,高于監軍司之正職監軍使,因此《西夏書事》有監軍司“諸軍并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的記載。其區別是,統軍司主要負責監軍司轄區內特別是邊境地區的軍事防御和戰備以及戰時作戰。監軍司則管轄監軍司內多重事務。統軍司向正統司負責,正統司向經略司負責;而監軍司主要向一路的經略司負責,經略司則依據民事或軍事分別向中書或樞密負責。經略司和監軍司的職權范圍很廣,舉凡人事、軍事、邊防、司法、畜牧,無所不管[6]243-245。但正統司、統軍司則應專事軍事,特別是統軍司具體負責邊防和作戰。
由此可知,沙州監軍司、瓜州監軍司的最高官員為正統軍(或稱都統軍)和副統軍,同時正統軍、副統軍也是統軍司的正副將領。沙州、瓜州監軍司的正職為監軍使,職位次于正統軍和副統軍。榆林窟第29窟窟門南側繪制有多位西夏男性供養人畫像,并旁書帶有職名的西夏文題名,對研究西夏職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關于榆林窟第29窟的營建年代,劉玉權先生考證為西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屬西夏王國之后期[17]。該窟內室西壁門南側上層供養人像第一身“真義國師信畢(西壁)智海”之后的第二身男性供養人題名“……沙州監軍攝受趙麻玉一心皈依”,表明趙麻玉擔任沙州監軍使之職,但他還不是監軍司的最高官員。下層第一身題名“……瓜州監軍……座…名每納……”、第二身題名“施主長子瓜州監軍司通判納命趙祖玉一心皈依”[18],可知趙麻玉之子趙祖玉擔任瓜州監軍司通判,屬于監軍司中級職務。榆林窟第29窟中的供養人像及其題名,反映出趙姓家族擔任了沙州監軍司、瓜州監軍司的多個職務。佐藤貴保先生認為榆林窟第29窟的趙姓供養人是與河西走廊地區的瓜州、沙州的軍事管轄區有著深刻關系的當地漢人集團[7]5,并進一步指出“在河西走廊,西夏無疑會利用當地的漢人勢力來推行統治……說起來,身為漢人的發愿者們,其官名和人名不是用漢文而用西夏文書寫,這一點表明他們掌握了西夏語”[19]。但佐藤氏觀點恐欠妥。榆林窟第29窟的男供養人像,雖然由于頭戴起運鏤冠而看不清發式,但根據畫像男性人物均“圓面高準,兩腮肥碩”的面部特征以及典型的西夏武官服飾特點,當為黨項人。且在該窟上部第三身和第四身男性供養人之間畫一孩童,旁用西夏文書寫“孫沒立玉一心皈依”,并上部最后三身侍從,皆為黨項人典型的禿發發式。元昊時期頒布了著名的禿發令,并在全國推行開來,成為黨項民族的一種象征[20]。再者,據前文對《西夏書事》敘述語境的分析,正副統軍、監軍使等監軍司高級職務應只能由黨項人擔任。因此,榆林窟第29窟的趙姓家族應為黨項人,他們在西夏后期擔任著沙、瓜二州監軍司的多個官職,表明當時兩司俱在黨項趙氏家族的實際領導之下。
二 瓜州刺史、沙州刺史
西夏漢文本《雜字》“司分部十八”中有“刺史”一職[21]。《天盛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門”中,西夏五級職司中未有刺史,表明刺史并非職司。但在職官配屬中,向瓜州、沙州派遣刺史各一人:
二十種一律刺史一人:東院、五原郡、韋州、大都督府、鳴沙郡、西壽、卓啰、南院、西院、肅州、瓜州、沙州、黑水、啰龐嶺、官黑山、北院、年斜、南北二地中、石州。[11]369
上文包含全部17個監軍司名,表明是向監軍司派遣刺史。沙州刺史、瓜州刺史俱屬于中等司,并且享有與中等司平級傳導的權利,《天盛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門”記載:
一諸邊中刺史者,與中等司平級傳導。[11]365
監軍司位列中等司,則刺史亦享有與監軍司平級傳導的權利。《天盛律令》第十三“執符鐵箭顯貴言等失門”又載:
又應派遣執符中,正副統、州府使、刺史、監軍司等俱在,原語同,則彼亦勿分別派執符,當總合一齊派之。[11]472
這表明統軍司的正副統軍、州府使、刺史、監軍司是相對獨立的幾個職設。《天盛律令》第十四“誤毆打爭斗”又載:
邊中:經略司,府、軍、郡、縣,刺史,監軍司,城、寨、堡。[11]485
此處亦清楚表明,經略司,刺史,監軍司是相互獨立的幾個職設。沙州、瓜州監軍司俱屬于中等司,并且沙州、瓜州刺史還各配屬一名都案,位于末等司,也表明刺史有某種職司的特點,具有相當的獨立性。邊境刺史應向經略司負責,《天盛律令》第九“諸司判罪門”載:
刺史人當察,有疑誤則棄之,無則續一狀單,依季節由邊境刺史、監軍司等報于其處經略,經略人亦再查其有無失誤,核校無失誤則與報狀單接。[11]323
李昌憲先生結合《天盛律令》記載,對刺史的職責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勾勒出刺史的幾種職責,如負責監督賦稅登記造冊、庫糧發放;負責調配修造糧倉、搬運糧食所需之“笨工”;負責治安,刺史同監軍司、地方巡檢一樣有實行抓捕;在審刑方面,刺史擁有復審權;參與軍事,擁有兵權。他同時指出,相對于監軍使,刺史職能明顯有民事官色彩[6]245-246。根據《天盛律令》記載,筆者認為刺史職能更多體現了監察的特點,監察內容涵蓋了民事、刑事、軍事等方面,例如對監軍司領取糧食進行監察,《天盛律令》第十五“納領谷派遣計量小監門”記載:
一諸邊中有官糧食中,已出于諸分用處,監軍司諭文往至時,當明其領糧食斛斗者為誰,刺史處知覺當行。計量小監由監軍習判、通判等輪番當往一人。領糧食處臨近,則刺史當自往巡察,若遠則可遣勝任巡察之人,依數分派。[11]512-513
對收租入庫的整個過程進行巡察,“納領谷派遣計量小監門”記載:
一納種種租時節上,計量小監當坐于庫門,巡察者當并坐于計量小監之側。納糧食者當于簿冊依次一一喚其名,量而納之……管事刺史人中間應巡察亦當巡察。[11]513
對租戶種地與耕牛之數字,轉運司等負責登記造冊,而刺史等則負責檢校,“納領谷派遣計量小監門”記載:
一邊中、畿內租戶家主各自種地多少,與耕牛幾何記名,地租、冬草、條椽等何時納之有名,管事者一一當明以記名。中書、轉運司、受納、皇城、三司、農田司計量頭監等處,所予幾何,于所屬處當為簿冊成卷,以過京師中書,邊上刺史處所管事處檢校。[11]514
刺史對刑事審理進行監察。《天盛律令》第九“諸司判罪門”記載:
一國境中諸司判斷習事中,有無獲死及勞役、革職、軍、黜官、罰馬等,司體中人當查檢,明其有無失誤。刺史人當察,有疑誤則棄之,無則續一狀單,依季節由邊境刺史、監軍司等報于其處經略。[11]323
刺史對獄中犯人的非正常死亡和非人待遇也要進行監察。“行獄杖門”記載:
一等囚人染疾病不醫,不依時供給囚食,置諸牢獄不潔凈處,及應擔保而不擔保等,疏忽失誤而致囚死時,依四季節,諸司所屬囚亡若干,刺史司體等當依次相互檢視。[11]334
如果有人對刑審不服,則先告訴刺史審查,如果確實是冤枉,則轉交監軍司。“越司曲斷有罪擔保門”記載:
一諸人因互相爭訟而投奔地邊,經略使上職管者因種種公事當告原先所屬監軍司。其中謂己枉誤而不服,則告于刺史,敢只關則當取文而視之。實為枉誤,于局分爭訟者當引送監軍司……[11]338
刺史還有軍事監察的職責。如對于監軍司所屬印、符牌、兵符等,平時置于監軍司大人處,當調兵時需在刺史面前開合符牌[11]474。
由上文分析可知,沙州刺史、瓜州刺史應與監軍司有一定的獨立性,其職責較多,但職能偏向于監察,監察內容包括民事、刑事乃至軍事等等。沙州刺史、瓜州刺史各配屬一名都案,負責協助刺史行使職權。榆林窟第29窟內室西壁門南側上層第二身供養人像,為第一身供養人沙州監軍趙麻玉之子,其西夏文題名,陳炳應先生譯作“內宿御史司正、統軍刺史”,同時依據該身供養人在沙州監軍趙麻玉之后,指出他不是正統軍使,而是職務較低的官員,刺史之職可與其地位相當[18]22。
三 瓜州轉運司、沙州轉運司
西夏在瓜州、沙州還設立轉運司,《天盛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門”載:
六種轉運司二正、二承旨:寺廟山、卓啰、肅州、瓜州、沙州、黑水。[11]370
轉運司之設亦當是仿自宋朝。《宋史·職官七》“都轉運使,轉運使,副使,判官”載:
掌經度一路財賦,而查其登耗有無,以足上供及郡縣之費;歲行所部,檢查儲積,稽考帳籍,凡吏蠢民瘼,悉條以上達,及專舉刺官吏之事。[9]3964
宋朝設立此職主要執掌一路或數路的財政。李昌憲先生認為西夏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受宋制影響,大致可分兩大系統,即經略司路與轉運司路[6]249。值得注意的是,西夏除在瓜州、沙州設立轉運司外,其余轉運司設于寺廟山、卓啰、肅州、黑水、西院、南院、大都督府、官黑山。除了都轉運司位處中等司而與監軍司平級外,其余10個轉運司俱為下等司,在監軍司之后。這表明西夏的轉運司不應設于路一級,而是設置于監軍司,為監軍司下屬機構。瓜州轉運司、沙州轉運司下還分別設立兩名都案,位于末等司。李昌憲先生利用《天盛律令》記載對轉運司職能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基本廓清了轉運司之職能,指出轉運司的職責比較單一,大體可歸納為催租和維護水渠兩項,另外,“與地租相關的閑田復種、生地開墾、田地毀壞、土地買賣,也都歸轉運司管轄”[6]247-249。榆林窟第29窟內室西壁下層第五身供養人題名“……承旨……”,但監軍司、刺史均不設承旨,只有沙州轉運司和瓜州轉運司各設立兩名承旨,沙州經制司也設立兩名承旨,因此這名承旨可能是沙州、瓜州轉運司之承旨,也可能是沙州經制司之承旨。
四 沙州經制司
西夏設有兩個經制司,一個在西院,一個在沙州[11]371。宋代職官設置中,設立有經制邊防財用司。在《宋史·職官七》中,“經制邊防財用司”也恰在轉運使之后設立:
經制邊防財用司:掌經畫錢帛、芻糧以供邊費,凡榷易貨物、根括田地及邊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9]3972
西夏經制司應是仿宋制而設,作用應同宋朝經制邊防財用司一樣,其目的是加強邊防而設置的理財機構。沙州位于西夏國境最西端,邊防作用重要,故于此設立經制司。該司屬下等司,在“轉運司”之后。
西夏時期要求各地諸司將官畜、谷物的借領、供給、交還、償還、催促損失等情況,按照距離京城遠近,自三個月至一年不等向中書、樞密所管事處報告。由于沙州、瓜州位于西夏最西邊,距離最遠,因此按一年一次向中央報告,一年一報告的僅有的兩個地方[8]55。
五 瓜州、沙州以下鄉的基層建制以及
作為民間組織的社
關于西夏時期瓜、沙二州之下的基層行政建制,由于史料記載缺略還難以詳知。曹氏歸義軍初期敦煌縣有11個鄉:敦煌、莫高、神沙、龍勒、玉關、洪池、洪閏、效谷、平康、慈惠、赤心[22]39-50,以及為通頰、退渾兩族編設的10個蕃部落,在這蕃部落使之下,又設有兩個通判五部落副使管理通頰、退渾兩族。曹元德上臺后對基層行政建制進行改革,首先廢除部落制,將通頰、退渾部落改設為鄉,轄下鄉由11個變為10個[23]。由于曹氏歸義軍末期回鶻與西夏互相攻戰,因此鎮、鄉的設置必然遭受到沖擊。雖然曹氏歸義軍中后期的十鄉未必全然悉數保留,但鄉作為基層建制在西夏時期得到了延續。如1972年在武威張義公社發現的西夏漢文文書中有“依中□各鄉以屬行遣”的記載[24]203。《天盛律令》中亦有鄉的記載:“前述當遣人數,京師界附近鄉里當遣之。”[11]437
社是唐宋時期敦煌極具特色的基層民間組織,敦煌文書保留了大量社的記載。而敦煌莫高窟第363窟西夏供養人漢文榜題記載:“社戶王定進□(永)□一心供□(養)。”“社戶安存遂永充一心供□(養)。”[25]這表明西夏時期敦煌仍然保留了唐宋時期社的基層民間組織。
六 小 結
以上根據有限史料對西夏時期瓜、沙二州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進行了勾勒。由于瓜州、沙州位于西夏國境西陲,軍事作用重要,因此在兩地均設有監軍司。監軍司是西夏時期兼具軍事與行政的地方建制,向一路的經略司負責。沙州監軍司、瓜州監軍司即向設在涼州的西經略司負責。西夏后期隨著兵制的不斷成熟,經略司和監軍司之間又增加了作為統兵機構的正統司和統軍司。統軍司正副將都(正)統軍和副統軍,兼任監軍司最高主官,高于監軍使。統軍司主要負責監軍司邊境和城池的軍事防御以及戰時作戰,監軍司則兼管民事與軍事。沙州和瓜州各設刺史一名,主要負責監軍司轄區內的監察事務。西夏還在沙州和瓜州分設轉運司,負責處理催租及與水渠、田地相關的事務。同時,沙州位于西夏最西陲,因此在沙州設立負責邊防地區理財的機構沙州經制司。瓜、沙二州應延續了鄉的基層建制以及作為民間組織的“社”。榆林窟、東千佛洞中黨項趙姓家族供養人像的集體出現,并且擔任著各級官職,表明趙姓家族曾是瓜、沙二州的實際統治者。總體來看,西夏在瓜、沙二州建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對敦煌實行有效的管轄和統治。
參考文獻:
[1]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145.
[2]劉玉權.西夏時期的瓜沙二州[J].敦煌學輯刊,1981(2).
[3]陳炳應.西夏與敦煌[J].西北民族研究,1991(1).
[4]湯開建.黨項西夏史札記[G]//黨項西夏史探微.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5]魯人勇.西夏監軍司考[J].寧夏社會科學, 2001(1).
[6]李昌憲.西夏地方行政體制芻議[C]//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屆年會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討會論文集.蘭州,2002.
[7]佐藤貴保.榆林窟第29窟男性供養人像に見る西夏の官制——官僚登用制度を中心に——[C]//西夏時代の河西地域における歷史·言語·文化の諸相に関する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課題番號:19520598),2010.
[8]史金波.敦煌學和西夏學的關系及其研究展望[J].敦煌研究,2012(1).
[9]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14029.
[1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5:2845.
[11]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69-370.
[12]佐藤貴保, 赤木崇敏, 坂尻彰宏, 吳正科.漢藏合璧西夏“黑水橋碑”再考[J].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2,2007:27.
[13]李范文,主編.西夏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438.
[14]骨勒茂才,著.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番漢合時掌中珠[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29.
[15]史金波.西夏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6.
[16]陳炳應.貞觀玉鏡將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13.
[17]劉玉權.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營建年代考論[C]//敦煌研究院,主編.榆林窟研究論文集(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362-364.
[18]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12.
[19]荒川慎太郎,佐藤貴保.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題記再考[C]//蘭州大學法藏敦煌文獻輪讀會報告,蘭州:2013:53.
[20]湯開建.西夏“禿發”考[J].西北民族研究,2003(2).
[21]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C]//中國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184.
[22]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J].敦煌研究,1989(3).
[23]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411-414.
[24]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發現一批西夏遺物[J].考古,1974(3).
[25]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