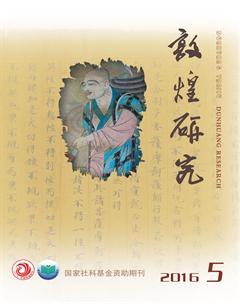敦煌寺院會計憑證考釋
郁曉剛
內容摘要:會計憑證是敦煌寺院會計文書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與諸色入破歷、入破歷算會牒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告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會計文書體系。敦煌寺院的會計憑證種類多樣。本文對判、施舍疏、取抄署、契據等幾種會計憑證的形制特點及其在會計核算活動中的使用狀況進行了具體辨析,指出敦煌寺院十分重視會計憑證的制作、整理、審核與保管。會計憑證發揮了記錄收支、控制出納和為編制賬簿、會計報告提供依據的重要作用,是敦煌寺院進行會計核算的基礎,體現了敦煌寺院財產管理和會計核算制度的嚴謹性。
關鍵詞:敦煌;寺院;會計憑證
中圖分類號:K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6)05-0092-09
Abstract: Accounting vouchers are an important type of document in Dunhuang temples, which together with account records and reports form a complete accounting system. Accounting vouchers of Dunhuang temples come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Pan(判), Shisheshu(施舍疏), Quchaoshu(取抄署), as well as contracts and other related pap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original documents in detail and points out that Dunhuang temple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uditing, organ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se documents, which record and control transaction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pkeep of the temples. These voucher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ccounting books and working out financial reports in the temples and illustrate the strictness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system in Dunhuang temples.
Keywords: Dunhuang; Temples; Accounting Vouchers
敦煌文獻中的會計文書大量為河西都僧統司和敦煌寺院所有。這些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會計文書,對解讀中古時期敦煌佛教教團的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財產管理和會計制度等都具有重要價值。
就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的形態和分類研究而言,研究者或根據文書的計會內容,將其區分為常住斛斗歷和常住什物歷兩大類;或按照文書形態,將其區分為賬、歷、牒、狀、疏、帖等;或借鑒現代會計學的概念,將其區分為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告。眾所周知,會計憑證是記錄經濟業務發生和完成情況、明確經濟責任的書面證明,也是組織經濟活動、傳輸經濟信息、實行會計監督的重要依據[1]。原始憑證又是會計憑證中的重要類型,是反映經濟收支和交易活動的第一手材料,為登記賬簿、進行會計核算提供了最原始的依據。敦煌寺院會計文書包含多種不同形式的原始憑證。但是,相對于諸色入破歷和入破歷算會牒的研究,目前學界對敦煌寺院會計憑證似乎措意較少{1}。
本文擬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借鑒現代會計學的基本原理,同時以唐代官廳會計文書制度和財產管理制度為參照,對敦煌寺院會計文書中的支付命令(判)、文記(取抄署)、施舍疏、契約等原始憑證的編制和使用情況作進一步探討,揭示其在財產管理和會計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深化對敦煌寺院財產管理和運作過程的認識。
一 支付命令(判)
李錦繡先生指出,符牒、判、木契、榜是唐前期官倉庫出給過程中四種必不可少的支納憑據。其中,判是倉庫執行出納手續時所須秉承的詳細支付指令,由其上級機構下達[2]。晚唐五代時期,在敦煌歸義軍政權的官倉庫出納活動中,我們仍然可以覓得“判”的蹤跡,如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歸義軍衙內破用紙布歷》第231—232行略云:“十六日,奉 判支與金銀匠王神神妻亡助葬粗紙兩帖。”[3]是知,歸義軍軍資庫在對外支出庫藏物資時也是“奉判”而行的。以現代會計學角度而言,這類判文正屬于原始憑證的一種,它們起到了通知要求進行某項經濟業務的作用。敦煌寺院會計文書中同樣存在這種性質的原始憑證,如P.3730《酉年(841)正月奉仙等牒并榮照判辭》載:
1. 牒,奉仙等雖沾樂人,八音未辨,常蒙撫恤,頻受賞勞。
2. 及課差科,優矜至甚。在身所解,不敢隱欺。自恨德薄
3. 無能,不升(勝)褒薦,數朝惶怖,希其重科,免有悚遺,
4. 卻加重賞。奉仙等四人,弟子七人,中心忻喜,貴
5. 荷非常。所賜賞勞,對何司取,請處分,謹牒。
6. 酉年正月 日奉仙等謹牒。
7. 檢習博士卿卿、奉仙、君君、榮榮,已上四人各賞絹
8. 一匹;太平已下弟子七人,各賞布一匹。付儭司,
9. 依老宿商量斷割交給分付。廿日 榮照。[4]
史奉仙等人是隸屬于敦煌佛教教團的音聲人,因演習音樂辛苦而獲得了教團的賞勞。奉仙等人向都司申牒的目的主要是詢問從何機構支取。上引文書第7—9行是釋榮照針對申牒所作的批覆。榮照是當時河西教團的最高僧官都教授[5]。他在判語中詳細說明了賞料的品類、數量和支付對象,并要求儭司“斷割支給”。顯而易見,這件牒文并判辭是奉仙等人領取絹布的憑據,而對于作為支付一方的儭司來說,在收到上述書面指令后才能向有關人員支出財物。是以,本牒文并判是一件典型的出納原始憑證。又P.3730V《吐蕃年次未詳沙州教授和尚乘恩判》記載:
(前缺)
1. 光妙神齋日,老宿與法律諸大德商量,賞老
2. 人布兩匹。如無布,麥亦得。仍付戒藏、義辯
3. 依數支給。乘恩。[6]
乘恩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約9世紀前期)曾出任河西教團中的都教授一職[7]。這件由承恩簽署的判文同樣是有關于教團對外支付賞料之事。承恩在判語中對賞賜物品進行了具體指示,并要求將其處分意見轉付與僧戒藏、義辯二人,由他們遵照執行。這件判文也可以證明,都司在頒賜財物一類的出納活動中,上級機構(或僧官)的判文是財物保管機構執行支付手續的必要依據。
在都司因從事放貸業務而引發的物資出納活動中,判文也發揮了原始憑證的作用。據BD.6359V
(6)(咸59V)《辛丑年(821)龍興寺寺戶團頭李庭秀等請便麥牒(附處分)》:
1. 龍興寺戶團頭李庭秀、段君子、曹昌晟、張金剛等 狀上
2. 右庭秀等并頭下人戶,家無著(著)積,種蒔當
3. 時,春無下子之功,秋乃憑何依托。今人戶等各請
4. 貸便,用濟時難。伏望 商量,免失年計。每頭請
5. 種子伍拾馱,至秋輸納,不敢違遲,乞請處分。
6. 牒,件狀如前,謹牒。
7. 辛丑年二月 日團頭李庭秀等牒(朱印)
(中略3行簽名)
11. 準狀支給,至秋征納。十
12. 三日。 正勤。
13. 依上處分,付倉所由
14. 付。[8]
這是一件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教團寺戶向都僧統司申請借貸年糧種子的牒狀。牒文末尾第11—14行為都司僧官的判決意見。都司教授宋正勤首先核準了寺戶的借貸請求,然后某未知名僧官接續判案道“依上處分,付倉所由付”,意即按照宋正勤的批示,并指令將附有判文的請牒送交都司倉,要求都司倉所由遵此向借貸者支付斛斗。文書內容到此為止,但可以推知,都司倉主管者在接到判文后,才將發放糧食給借貸的寺戶。因此,本件既是寺戶向都司辦理借貸業務的申請文書,也是都司倉給付斛斗的原始憑證。
以上案例中,不論是隸屬于教團的音聲人向都司領取賞料,還是寺戶向都司倉借貸,都必須先行申牒請批,通過后,憑判支取財物。而都司倉、儭司等財物保管機構則必須嚴格按照上級僧官或機構發出的判令支出斛斗。上述判令作為支付通知書是十分典型的原始憑證。這類憑證的存在從一個側面說明,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由河西教團直接控制的都司倉等物資收儲機構在出納管理和會計核算過程中就已經建立了較為嚴謹的手續制度。
二 文記(取抄署)
文記或稱文鈔,是唐代官廳會計核算中經常使用的一類原始憑證。據《通典》卷149《兵二·雜教令附》引《衛公李靖兵法》云:
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并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為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抄為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
軍隊營司對軍士攜帶的衣物、武器裝備設有專門的登記文案,即衣裝賬簿。當兵士支用衣物裝備時,隊頭、火長必須予以記錄。而且這些記錄內容被要求“五日一申報營司”,使營司得以及時掌握變動狀況,并用作修改衣裝賬簿的依據。顯而易見,這種由隊頭、火長抄寫的文記即屬于原始憑證的范疇。又唐《廄牧令》復原第44條(唐25條)云:
諸府官馬及傳送馬、驢……軍還之日,令同受官司及專典等,部領送輸,亦注膚、第,并賚死失、病留及隨便附文鈔,具造帳一道,軍將以下連署,赴省勾勘訖,然后聽還。[9]
官馬驢在行軍過程中因死失、病留等所立之文鈔亦屬原始憑證,可敷造帳之用。文記的具體形式究竟如何,上述兩則文獻均未確示。《唐律疏議》對文記的內涵卻有一段重要的提示,該書卷第15《廄庫律》“監主貸官物”條記載:
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準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疏]議曰:……“文記,謂取抄署之類”,謂雖無文案,或有名簿,或取抄及署領之類,皆同……[10]
根據律文、律疏的解釋,文記是有別于文案的某一類文書的統稱。舉凡名簿{1}、取抄、署領等均可歸入文記。取抄的運用較為廣泛,唐《倉庫令》復原第2條略云:“諸受租,……隨訖給鈔總申。”[9]493官倉受納租物時,要向繳送者出具抄文,以作為其完納租稅的原始憑證。這類取抄實物在吐魯番文書中俯拾皆是,如《武周如意元年(692)里正李黑收領史玄政長行馬價抄》(64TAM35:28)云:
1. 史玄政付長行馬價銀錢貳文,準銅
2. 錢陸拾肆文。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里正
3. 李黑抄。其錢是戶內眾備馬價。李黑記。[11]
又大谷5823《周通生納稅抄》云:
1. 周通生納天寶叁載后限稅錢壹伯壹拾
2. 陸文。其載七月二日,典魏立抄。[6]296
以上所引取抄,一件是史玄政繳納按戶抽配的長行馬價后,里正出付與他的書面憑證,一件是縣典給付百姓繳納戶稅的憑證,均為納稅的原始證明。除了用作完納賦稅的憑證,唐代官民間的其他經濟交易活動中也有使用取抄的情形,據《唐景龍二年(708)補張感德神龍二年買長運死驢抄》
(72TAM223:25—1):
1. 張感德先去神龍二年十月內買長運死驢
2. 壹頭,皮壹張,給抄訖。今稱失卻,更給抄。
3. 舊抄在,不在□用限 。景龍二年四月
4. 廿日,胡基抄。會納歷同。典□。[12]
神龍二年,張感德從某官府機構購買了長運死驢一頭、皮一張,同時獲得“抄”文一份,作為交易成立和合法有效的證明。但張感德之后不慎遺失原抄,于是他向發文機構申請補領。承辦官典經過核查有關“納歷”中的雙方交易記錄,確認交易真實發生過,所以向其重新出具了上述抄文并申明舊抄作廢。此案中,張感德遺失交易抄文后還不厭其煩主動向官方申請補領,說明具有法律證明文件和經濟憑證雙重屬性的取抄在當時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能等閑視之。
文記中的署領在出土文書中也有具體實例,《唐開元十九年(731)康福等領用充料錢物等抄》(73TAM506:4/11)略云:
20. 使西州市馬官天山縣尉留□、典壹人、獸醫壹人、
21. 押官壹人,伍日程料,領得錢貳伯伍拾文。開元
22. 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典趙寶領。[13]
這件文書記錄了典趙寶領取市馬官一行人等的五日程料錢,文書末尾有領物人的署名。原編者將其定為領用錢物抄,大致無誤。但根據前揭唐律法條,筆者以為若將其定為“署領”似乎更加妥帖。又大谷1014《西州都督府兵役(兵曹)關系文書》載:
1. 分付和忠錢練
2. 右祿直練從庫出,晉陽押領[(后略)[14]
是知,官員從官倉庫支取俸祿須由本人或代領者立據簽字。本件文記末尾有“晉陽押領”等語,故應為署領無疑。取抄與署領是相對而言的,收納者出具取抄,支領者簽押署領。當然,實際使用中兩者可能并不存在截然區分。
不僅官廳財計管理活動,而且民間經濟交易和私家理財記賬中也會普遍用到取抄署等文記。據《唐會要》卷52《忠諫》記載:“初,有賈人張陟負五坊息利錢,征理經時不獲。楊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訖,悉囚捕,重令償之……又于陟家得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夫書跡,遂追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家僮,促期使納。”商人張陟通過設立賬簿、文記打理商業交易活動。五坊使從張陟家搜檢出的文記是盧載初欠負張陟錢款的書面文件,由負債方盧載初手書,并作為原始憑據由商人張陟收存。
從以上實例可以看出,取抄、署領等文記具有形制簡潔、方便易行的特點,因此,它們在官方和民間的經濟活動中被廣泛應用。唐末五代宋初時期,作為原始憑證的抄在敦煌地區仍然較為常見,如P.2161(P2)《年代不詳(十世紀初)兵馬使岳安□等還谷贖舍抄》略云:
2. 粟拾碩、布壹匹,已上斛斗及干貨都
3. 拾柒碩,并總還訖,一無欠少。今
4. 候陰兼行巷村鄰,押抄示名為
5. 契日,抄在岳家覓不得,已后抄出 ?
6. 在 論限。 舍主兵馬使岳安□(押)[8]400
兵馬使岳某與某人進行了一宗房宅交易,買方全部償清作為房價的斛斗及干貨后,賣方出示了抄文以作憑證,但是事后原抄遺失。本件文書即另行制作的一份證明文件,內中復述了事件原委并申明原抄作廢,而以此新抄為準,此抄亦具有法律效力。又Дx.1417《丙子年(976?)楊某領得地價物抄》略云:
1. 丙子年十二月四日楊□□領得地價物抄。生絹壹
2. 匹,長叁丈柒尺叁寸,準折濕物貳拾伍碩。白斜
5. 已前褐準尺數折物捌石。(押)[8]390
本文起首即有“領得地價物抄”之語,是知為抄文無疑。文書主要記載了地主楊某在一樁土地交易中已收領到地價物若干。以上兩件抄文,第一件末尾有舍主、舍主親屬和見人的簽名、花押,第二件亦有花押。可見,抄文在形制方面一般須具備“押抄示名”。
取抄署在敦煌寺院經濟活動中亦有使用,如Дx.1383《壬戌年(962?)翟法律領物憑》:
1. 壬戌年十月 八 日,于令狐兵馬使手上領得粟貳拾壹
2. 碩伍斗。領得馬攞真邊麥肆碩伍斗,為記。
3. 領物人 翟法律(簽押)[8]389
這則取抄記錄了同一天內一連領取的兩筆麥粟收入。從文末的押抄示名來看,它應該是敦煌某寺制作的原始收入憑證。又Дx.1424《庚申年十一月僧正道深付牧羊人王拙羅寔雞羊數憑》:
1. 庚申年十一月廿三日,僧正道深見分付常住牧羊人
2. 王 拙羅寔雞白羊、羖羊大小抄錄,謹具如后:
(中略)
5. 伍口。已上通計肆拾口,一一并分付牧羊人王拙
6. 羅寔雞,后算為憑。
7. 牧羊人王拙羅寔雞(押)
8. 牧羊人弟王悉羅(押)[3]578
這是一件某寺常住牧羊人從寺院領取放牧羊群的原始記錄,文末有領取者王拙羅寔雞等人的署押,或者亦可將其視作取抄署一類的文記。文書中的“后算為憑”等語表明,本件抄文也是之后寺院與牧羊人進行業務核算的憑證。又S.3984《丁酉年(937)報恩寺牧羊人康富盈算會憑》云:
1. 丁酉年十一月三日[立][契]。報恩寺徒眾就大業寺齊
2. 座算會,牧羊人康富盈除死抄{1}外,分付見行羊數:(后略)[8]372
“死抄”或指羊死亡后,寺院根據牧羊人的報告及其繳送的死羊皮、肉等實物,而向其出具的證明文書。S.4704《辛丑年(941?)二月徒眾納死羊憑據》或即屬于此類死抄的實物,文書記載:
1. 辛丑年三月廿日,徒眾因城北索將頭莊上拔毛日
2. 見納死白羊羔子玖口,羖羊羔子陸口。(押)[3]576
它與前引唐令中“死失、病留及隨便附文鈔”的性質接近。報恩寺在與本寺牧羊人的結算活動中,死抄是點算減少羊數的證明。所以,取抄署等文記既是經濟往來業務的證明文件,也是寺院編制賬簿和從事財務結算的依據。
當然,還有比取抄署更為簡略的文記。如Дx.1365《癸未年凈土寺周僧正還王都料鎖價絹契記》載:
1. 癸未年七月十九日,凈土寺周僧正絹七疋還王都料生鐵口
2. 鎖價用。{2}
本條支出文記省去了經辦人和當事人的署名簽押,大約是隨手記錄以作為編制帳歷時的提示。民間經濟活動中制作的文記與官方相比更加簡易靈活。
目前,我們可以得見的敦煌寺院取抄署領類的原始憑證不多,揆諸情理,單件取抄署多是由寺院向納物者開具,寺院一般自然不會收存,另外這也可能與領得歷(抄錄)的使用有關。敦煌寺院的出納活動頻繁,財計管理者為減少原始憑證的數量、簡化算會手續,較少制作這種一次性的取抄署,而徑以領得歷代替,如S.6981《辛未—壬申年(971—972)某寺某某領得歷》略云:
8. 十二月十四日,領硙戶李章祐舊硙稞(課)粟伍碩叁斗。愿。
9. 十七日,領得南梁戶楊再住算領粟兩碩。愿。壬申年正月
10. 一日,弁才亡贈粟肆碩。愿。……[3]138
本件文書中,某寺僧愿按時序逐日記錄了手上的各項收入。而S.5495《唐天復四年(904)燈司都師會行深信依梁戶朱神德手下領得課油歷》則是專門針對梁課收入一項經濟業務設置會計科目編制的憑證,文書略云:
1. 天復四年甲子歲二月一日,燈司都師會行、深信依
2. 梁戶朱神德手下領得課油抄錄如后:
3. 三月十一日,領得油壹斗,朱。……[3]115
以上兩件領得歷中的每筆收入前均標明日期,末尾有領取者或繳納者的親筆署押(有的加蓋印件,如Дx.4277+Дx.6042)。這種通常被歸為收入賬簿的領得歷,或者也可以視作取抄署的演化和發展,是介于會計憑證和會計賬簿之間的一種文書類型{1}。它們是可以多次填寫、使用的原始憑證,從這個角度看就略接近于現代會計憑證中的累計原始憑證。
綜上,取抄署之類的文記作為原始憑證是敦煌寺院算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類原始經濟憑證。而由一次性憑證取抄署發展而來的領得歷則使賬務處理活動更趨清晰和高效,也為寺院管理者了解和掌控某項經濟業務提供了便利。
三 施舍疏
施舍疏是僧俗施主向寺院、教團布施財物時所使用的文書。通常,它隨施物被一道交與寺院。但由于某些施主的文化水平不高,變通之下,疏文也可由寺院代寫。施舍疏的內容通常包括施物的名稱、數量、去向,施舍的時間、地點、緣由、目的以及施主姓名等[15]。
敦煌寺院將普通布施者個人的施舍稱為散施,散施是寺院的重要收入的來源之一。除了施舍疏,敦煌寺院的入歷和算會牒對信徒的散施財物往往有詳細的登記。因此,寺院或教團進行會計核算時,施舍疏可以作為原始憑證,供編制入歷、算會牒等的賬歷使用。敦煌寺院的施舍疏在形式上有多件連寫和單件之分,在內容上也有繁簡之別。
現代會計制度中,原始憑證的審核是賬務處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只有校驗合格的原始憑證才能作為編制記賬憑證和登記賬簿的依據,以此保證會計核算資料的真實與準確[1]204。作為原始經濟憑證,敦煌佛教教團和各寺的施舍疏存在著明顯的整理、審核痕跡。如P.2837V《辰年支剛剛等施入疏十四件》記載:
(前缺)
………………………榮照…………
(中略)
(三)1. 布壹丈,施入修造
2. 右弟子所施意者,己身染患,圣
3. 力加持,似得減損。今投道場,請
4. 為念誦。
5. 辰年正月卅日女弟子王氏疏。
6. 已前壹拾柒道疏。卅日,榮照。
………………………榮照…………
(四)1. 胡粉半兩,施入修造。鏡一面,施入行像。
2. 右所施意者,為慈母舍化以來,不知神
3. 識,今頭(投)道場,請為懺念。
4. 二月八日女弟子十二娘疏。(后略)[3]59-60
本卷殘文書現由七紙粘綴而成,每紙抄錄施舍疏一至三道不等。每道疏文中所記物品名稱的右側和文書空白處多有勾畫符號,與敦煌寺院各種會計賬歷中所采用的勾畫方式一致。會計賬歷中文字右側的勾畫符號一般表示某筆賬目結算完畢或已清點核對,予以勾銷。文字下方空白處的勾畫符號則表示行文至此結束[16]。是知,審核疏文的重點在于確認其中登錄實物的名目、數量是否正確以及防止他人隨意虛造和涂改。
另外,這卷文書每兩紙的正面騎縫處均有僧官榮照的署押。押縫是唐代官文書處理程式中的重要手續,通常是長官、判官對其職守負責的一種表示[17]。敦煌寺院施舍疏上騎縫署押的作用應與之大致相同。又,本件文書在第三道疏文后載:“已前壹拾柒道疏。卅日,榮照。”這是榮照在辰年正月卅日針對當天(或之前一段時間)施舍疏特別添寫的一條匯總性注記。所以這批疏文是由榮照整理、審核,注記實際是對整理、統計和勾檢結果的扼要說明。
P.2583《吐蕃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也采用了多件連寫的形式。文書殘存部分系由十二紙粘連而成{1},每張紙多只抄錄一道疏文,且抄寫筆跡不同。由此可知,這件文書是由若干獨立的疏文董理、連綴所成,而非一次性抄錄。與P.2837V相同,本卷文書中每道疏文都有勾畫符號。文書第12紙的末尾處還有正勤的署押,筆跡與之前的疏文不同。正勤即前揭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都司教授宋正勤,他應該是這組疏文的整理者或審核者。
類似的施舍疏在吐魯番出土的寺院文書中也有發現,且時代更早。如阿斯塔那170號墓所出《高昌□子等施僧尼財物疏》。這件高昌國統治時期的寺院施舍疏中就有明顯的朱筆勾畫痕跡以及布施財物的朱書合計數字等。[18]可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在會計核算活動中對施舍疏的整理、點算、審校具有普遍性。
當然,教團財計人員對施舍疏的審核并不僅限于施物的收入情況,如羽076R《比丘法鄰僧衣、布、紙施入大眾疏》載:
1. 布僧衣壹薱(對),布壹匹入大眾其布法山便
2. 右所施意者,為寄身深患,藥食雖
3. 投,未蒙痊損,今投道場,請為念
4. 誦
5. 六月八日比丘僧法鄰謹疏
6. 法事真法師
7. 法鄰城門前施布壹匹,紙大小兩帖和?入
8. 大眾
9. 法鄰齋儭,已前儭司并云唱訖,已后其物
10. 見在洪辯。
13. 洪辯[19]
這是僧人法鄰因患病而向道場施物,請為念誦佛經以求早日痊愈的疏文。值得注意的是,這件施舍疏第9行以后洪辯另筆添寫的一道注記,它完整地交代了教團對法鄰所施舍齋儭的處置經過和現存狀況。本案例中,教團對施舍疏的核驗已經超出了簡單的賬物校對,而涉及儭司等前后經手過施物的機構和人員,體現了校核活動的細致與周備。
要言之,針對信眾的施舍,敦煌教團或寺院首先為他們逐一立寫施舍疏以作憑證,其后再將這些零散的單頁粘連成卷,進行編聯整理、統計與審核。施舍疏經過這樣一系列的賬務處理,既可以充分發揮其會計監督的作用,又為后續其他帳歷的編制提供了基礎和便利。所以,作為原始經濟憑證,施舍疏是敦煌佛教教團會計核算和財產管理中的又一重要憑證資料。
四 契 約
中國古代契約制度在唐宋時期日臻完善和發達。敦煌寺院也廣泛使用到雇傭契、借貸契、出租契等各種契約。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民間契約又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一般性的民間契約,僅在法律方面起證據作用;一類除具有法律方面的證明作用,還是登記會計賬簿的依據[20]。敦煌寺院使用的契約文書多數就兼具這兩種功能。
經濟契約是原始交易憑證。現代會計實務中,契約(合同)雖然附屬于會計資料,但不能直接用作會計核算的憑證。敦煌寺院的賬務處理過程中尚不存在如此嚴格之界限。所以,我們或者可以將其納入原始憑證的范疇進行考察。而且,在會計期末,敦煌寺院財計人員確實也常依照契約中所擬定的條款確認收支和執行結算業務。S.6781《丁丑年(917)正月十一日北梁戶張賢君二年油課應見納及沿梁破余抄錄》記載:
丁丑年正月十一日,就庫算會,北梁戶張賢君,乙亥年、丙子貳年課,應見納及沿梁破余,謹具抄錄如后。準契見納油數:(中略)張賢君亥、子貳年中間準契欠油壹碩叁勝(后略)。[3]343
這件抄錄中提及的“契”是指本寺與梁戶張賢君間訂立的捉油梁契約。敦煌文書中留存有水硙、油梁租賃契約的樣文{1},其中即涉及承租方應納梁課數額和繳納時限的規定。此算會文書中的“準契見納油數”、“準契欠油”等語表明,寺院在與承租油梁者算會時是嚴格按照契約規定核算梁戶的已納和未納梁課數目。由此可見,契約文書也是敦煌寺院進行會計核算時所采據的原始憑證,在算會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還有一些契約文書本身就已明確標出將被用作結算憑據,如S.4116《庚子年(940)報恩寺牧羊人康富盈算會憑》記載:
庚子年十月廿六日立契。報恩寺徒眾就南沙莊上齊座算會,牧羊人康富盈,除死抄外,并分付見行羊籍:大白羯羊壹拾叁口,白羊兒落悉無陸口……已前白羊羖羊,一一詣實,后算為憑。
牧羊人男員興(押),
牧羊人康富盈(押),
牧羊人兄康富德(押)。
其算羊日,牧羊人說理,矜放羔子兩口為定。又新舊定欠酥叁升。(押)[8]374-375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將本件文書定名為算會憑。但文書起首所云“庚子年十月廿六日立契”卻又正是敦煌契約文書中慣常采用的套語,如S.1398《壬午年慈惠鄉郭定成典身契(習字)》這種典型的契約文書中就有“壬午年二月廿日立契……恐后無信,故立此契,用為后憑”等語[8]353。所以,本件文書在內容上雖然與一般意義的契約差距稍大,但從形式看,將其視作契約似乎亦可。這種特殊形態的契約正為寺院會計核算提供了重要依據。
契約不僅對經濟業務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有詳盡規定,有時也具備產權或債權的書面證明作用,因此,寺院在一定時間段內對這類原始憑證也會相應地加以妥善保管。大歷九年,長安寺高僧不空示寂后,將“祥谷紫莊將倍(陪)常住,其莊文契并付寺家”{2}。敦煌寺院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據P.3587《年代不明(公元十世紀)某寺常住什物交割點檢歷》記載,敦煌某寺常住什物中有“諸家賣捨(舍)文契及買道、論(輪)硙文書一角。”[3]46本件常住什物交割清單中,購置房地產業和碾硙的契約文書就赫然在列,這正可以說明敦煌寺院十分重視對這一類原始經濟憑證的保管。
五 結 語
原始憑證本身具有內容散碎、形制簡短、運用靈活的特點。在財產管理人員編制完各類賬簿和會計報告后,有些憑證可能很快就被廢棄。所以,在目前存留下來的敦煌寺院會計文書中,原始憑證的數量相對不多。本文列舉和分析的幾例原始憑證遠遠不能反映敦煌寺院會計憑證的全部形式與內涵,但已經可以說明,敦煌寺院在其財計活動中普遍采用到原始憑證,以及時記錄各項經濟業務,嚴格掌握和監督財物出納等情況。這些原始憑證從編制方式看,既有一次性憑證也有可以連續多次填制的憑證;從文書形制來看,則有適應不同場合和需求的判、施舍疏、取抄署、契約等多種樣態。同諸色入破歷等會計賬簿和算會牒等會計報告一樣,原始經濟憑證在敦煌寺院會計文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會計文書體系。
其次,敦煌寺院和教團已經注意到對各種原始憑證區別進行整理、審核與保管,以為之后的登記賬簿和結算業務服務。上文在論及契約、施舍疏等憑證時,對這方面內容曾予以具體分析。歸納言之,當時寺院在原始憑證的保管方面主要采取了以類相從和粘連成卷的方式。有些原始經濟憑證,如BD.6359V(咸59V)號文書中六件關于寺戶向都司借貸的牒狀和S.1475號文書中十多件屬于靈圖寺的借貸契約,雖然都司和靈圖寺的財計人員沒有將它們整理粘貼成卷,但從目前的保存情況可以推斷,在其被利用來抄寫佛經前應該是收存在一起的[21]。另外,除了作為會計資料由財計人員集中收管,有些原始憑證還被列入常住什物加以妥善保存。在原始憑證的審核方面,敦煌寺院采取的具體形式則至少包括勾畫、署押和統計三種,以此確保憑證文書的準確、可靠。寺院和教團的財產管理和會計核算制度之嚴謹于此也可見一斑。
最后,編制原始會計憑證是敦煌寺院會計核算中的重要環節,體現了其財計制度設計和運作的合理性。在敦煌寺院賬務處理過程中,從制作原始憑證到編列各類收入支出賬簿再到編制入破歷算會牒等會計報告,形成了一個基本完整的核算序列。判、取抄署、施舍疏、契約等原始憑證為編制諸色入破歷和入破歷算會牒提供了依據。所以,各類會計憑證在敦煌寺院和教團的財務運作活動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廖洪.會計學原理[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195.
[2]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72-178.
[3]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267.
[4]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113.
[5]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M].京都:同朋舍,1982:364-366.
[6]池田溫,著.中國古代籍賬研究[M].龔澤銑,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407.
[7]姜伯勤.敦煌本承恩帖考證[C]//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380-394.
[8]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86-87.
[9]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6:519.
[10]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6:1132.
[11]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441.
[12]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60.
[13]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10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3.
[14]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M].京都:法藏館,1984:3.
[1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42.
[16]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7,19,339.
[17]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C]//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385.
[18]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2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19-139.
[19]公益財團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吉川忠夫.敦煌秘笈:影片冊:1[M].大阪:はまや印刷株式會社,2009:450-451.
[20]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上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362.
[21]童丕.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M].余欣,陳建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3: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