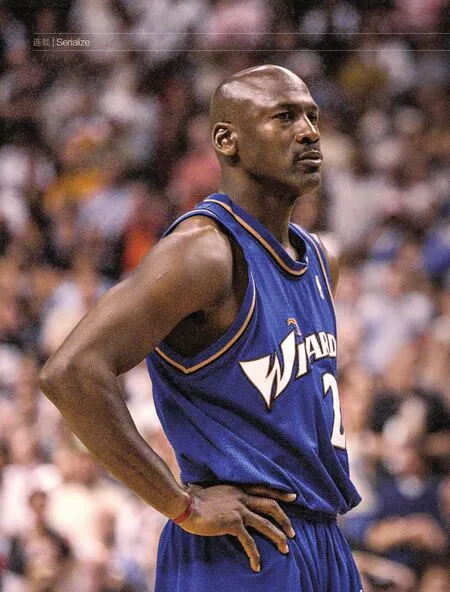我是鯊魚 沙奎爾·奧尼爾自傳
我是鯊魚沙奎爾·奧尼爾自傳
第三章我的父親
在我五歲那年,我們?nèi)野岬搅诵聺晌鞯呢悹柲崾小R舱窃谀抢铮^父開始對(duì)我進(jìn)行嚴(yán)格教育。每當(dāng)我在外面調(diào)皮搗蛋時(shí),他會(huì)揚(yáng)起巴掌毫不猶豫地打我屁股。他讓我像個(gè)男人式地堅(jiān)強(qiáng)起來(lái),不要遇到麻煩總是像個(gè)女孩子一樣地哭鼻子。我也必須得承認(rèn),那時(shí)的我別看個(gè)子大的出奇,卻是一個(gè)不折不扣的熊包,哪怕是一個(gè)比我矮半頭的小朋友都可以肆無(wú)忌彈地欺負(fù)我,現(xiàn)在想起來(lái)真是丟死人了。
家里的生活也日益艱難了起來(lái),有的時(shí)候我們甚至連房租都付不起,吃了上頓沒下頓在我們家是很常見的事情。除了我們幾個(gè)孩子以外,繼父還有兩個(gè)寄養(yǎng)在親戚那里的女兒(他和前妻的孩子)需要他照顧。萬(wàn)般無(wú)奈之下,繼父只好工作之余在外面兼了一份送貨的工作。每天晚上,他都會(huì)開著一輛大卡車在紐約和新澤西兩地來(lái)來(lái)回回地運(yùn)送貨物。常常是在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夢(mèng)鄉(xiāng)的時(shí)刻,繼父還在外面忙碌著沒有回家。為了支撐起這個(gè)家,他真的是沒少吃苦頭。
在我大一點(diǎn)點(diǎn)的時(shí)候,繼父開始帶我嘗試著玩各種球類:棒球,籃球,足球等等。媽媽曾說(shuō)過我天生就是一塊搞運(yùn)動(dòng)的好材料。因此我也常常同其他小伙伴們一起在籃球場(chǎng)或足球場(chǎng)地上跑來(lái)跑去地玩耍,但由于害怕被皮球砸在腦袋上,所以我總是跟在小朋友們的后面來(lái)回地遛圈。
“當(dāng)我把球扔過來(lái)時(shí),你不要?jiǎng)印!币淮卫^父嚴(yán)厲地對(duì)我說(shuō),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站在原地等著。他將球扔了過來(lái),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臉蛋上。
“怎么樣?球砸在你的臉上,只能令你疼痛一秒鐘而已,并不會(huì)給你造成什么永久性地傷害。孩子,不要害怕球。”從那天開始,我再同小朋友們玩球時(shí)總是擠在隊(duì)伍的最前列。
在我九,十歲那么大時(shí),有一次媽媽帶我去見了我的親生父親喬·托尼(Joe Toney)。我想她大概希望我能夠見見自己的爸爸吧。我還記得他租住在一個(gè)小小的公寓里,看上去生活很窮困潦倒的樣子。我沒和他說(shuō)過幾句話,大概是感覺太陌生了吧。在那次會(huì)面之后,我沒有再讓母親帶我去見他。在我的心里,菲爾繼父將我從小拉扯大,他才是我真正的父親。
再次見到托尼還是大約八年前的事情了。那是1994年,當(dāng)時(shí)我正代表美國(guó)參加世錦賽。一天,繼父趕到隊(duì)中來(lái)探望我時(shí),輕描淡寫地說(shuō):“你應(yīng)該去找你的親生爸爸好好談一次,我曾在電視上的一個(gè)訪談節(jié)目中看到他了。”
我感到很驚訝,過后偷偷地詢問媽媽。“父親現(xiàn)在做些什么呢?”
“他不是你父親,他是喬·托尼。他在一個(gè)電視節(jié)目中提到你了。”
沒錯(cuò),托尼和他的一個(gè)小兒子一起出現(xiàn)在那個(gè)訪談節(jié)目里。“我只是想與我的哥哥見面。我很愛我的哥哥,能夠親眼看他一眼我已經(jīng)非常滿足了。”小孩子這樣表白著。
然后,喬又出現(xiàn)在屏幕之上。“沒錯(cuò),沙奎爾就是我的兒子。我沒別的企圖,我只是想讓他知道我非常想念他。”
這件事情過去不久,我曾有一次在拉斯維加斯碰到了我這位同父異母的兄弟。當(dāng)時(shí),他在看到我之后,大踏步地走到我跟前,拍著我的肩膀說(shuō):“嗨,我是你的兄弟。”
我當(dāng)時(shí)沒有認(rèn)出他來(lái),還以為他是我的“球迷兄弟會(huì)”中的一名成員呢。直到他異常嚴(yán)肅地說(shuō)“喬·托尼是我的父親”時(shí),我才猛然回過味來(lái)。他給我看了他們?nèi)业暮嫌埃缓髮⑽依铰愤吰ъo的角落處,義正言辭地對(duì)我說(shuō):“父親怎么想得我不管,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是你的兄弟,我不會(huì)向你要任何東西,你只要知道有我這么一個(gè)同父異母的兄弟就夠了。”后來(lái)曾有一次在紐約又碰到了他,他還是那老一套。“喬·托尼是我的父親。”
曾有人問我,我是否恨我的父親。不,我并不恨他。每個(gè)人都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quán)利,我,他,繼父,我們每個(gè)人都是如此。我在繼父的撫養(yǎng)下長(zhǎng)大成人,沒有繼父也就沒有我的所以我尊敬愛戴他,我將他視作我的親生父親。至于托尼,我只想說(shuō)即使一輩子看不見他,我也不會(huì)想起他。
第四章我很幸福
我的母親盧西里·哈里森是一個(gè)非常漂亮優(yōu)雅的女人。從我記事起到現(xiàn)在,我就很少看見母親會(huì)為了什么事情而愁眉不展過。哪怕是在每個(gè)月的中期我們上頓接不上下頓的日子里,她也依然會(huì)微笑地安慰我們說(shuō):“孩子們,不要發(fā)愁啊,離發(fā)薪水的日子沒有幾天了。”她就這樣樂觀自信,寵辱不驚地生活著。即使是像現(xiàn)在這樣過上了豐衣足食的日子,母親也絕對(duì)不會(huì)擺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姿態(tài)來(lái)。任何時(shí)刻的她都是保持著積極樂觀的生活情緒,而這也是我特別依賴母親的原因。不管我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只要回家撲進(jìn)母親的懷抱里撒撒嬌,就一切問題都沒有了。而母親呢,她也始終寵愛呵護(hù)著我,即使當(dāng)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一個(gè)賽場(chǎng)巨人,在她的眼中還是那個(gè)需要她疼愛的小寶貝。畢竟我是他的大兒子,她和其他那些長(zhǎng)輩們總是給予我無(wú)限的關(guān)愛,而這種溺愛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我任性愛搗蛋的壞脾氣。
還記得在我六歲那年,我們家當(dāng)時(shí)居住在紐約城的奧克街。那時(shí)我有一個(gè)可愛的玩具熊,還有一個(gè)爸爸送給我的打火機(jī)。聽到這里,相信你也知道我干了些什么壞事吧。沒錯(cuò),我趁家里人都不在的時(shí)候用打火機(jī)點(diǎn)燃了那個(gè)玩具熊。我本意是想將熊點(diǎn)燃之后,看看它在火中焦烤的模樣,然后再把火撲滅。但它卻在我意料之外地熊熊燃燒起來(lái)。我有些害怕了,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只能用一個(gè)小木棍將他小心翼翼地扒拉到床底下,藏好之后我就像沒事人似的出去找其他小朋友們玩去了。等到我的父母接到鄰居電話趕回家時(shí),我的那個(gè)殘破不堪的家早已化為灰燼了。而我,也在被母親毫不留情地狠揍了一頓之后隨父母搬遷到別的親戚家暫住了。
在那一段時(shí)間里,我們就往返于新澤西和紐約城之間,在不同的親戚家里過著游擊生活。到現(xiàn)在,我仍能將這兩座城市之間的許多大街小巷的名稱如數(shù)家珍般地說(shuō)出來(lái)。我們有很多窮親戚家可以寄宿,他們和我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都是賺取著一份微薄的薪水,租住在一套帶有兩間臥室的公寓里。我和我的那些堂兄弟姐妹們一起住在一個(gè)大通鋪上,有的時(shí)候一間小小的屋子里能睡得下我們7、8個(gè)小孩子。我們中的一些人還會(huì)輪流睡在地板上。這里沒有空調(diào),沒有。
在那些熱的令人窒息的夏天夜里,我們家在房間的角落處安了一個(gè)簡(jiǎn)易的旋轉(zhuǎn)式電風(fēng)扇。每個(gè)人都希望電風(fēng)扇吹出的那一點(diǎn)點(diǎn)熱風(fēng)能夠久久地固定在自己這邊,我自然也不例外了。躺在潮濕悶熱的地板上,小小的我就這樣傻傻地期待著那一屢屢小風(fēng)吹到我的這邊。有的時(shí)候,我還會(huì)任性地不顧其他孩子們反對(duì)地將風(fēng)扇后的按鈕按下,這樣風(fēng)扇就會(huì)停止四面旋轉(zhuǎn),而只朝著我這邊猛吹了。
那時(shí)家里的冰箱也總是空空如也,饑餓的孩子們幾乎吃掉了所有能吃掉的東西。為了保證我們身體的健康成長(zhǎng),我的祖母奧德薩每天早上都會(huì)要求我們喝下一大勺蓖麻油。真奇怪,那時(shí)我們居然沒有感到惡心。我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母和親戚們的舊衣服,雖然外表看上去不那么美觀,而且每件衣服基本都要穿上三年左右,但我們總比那些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們要幸福的多了。
(待續(xù))
SHAQUILLE O'N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