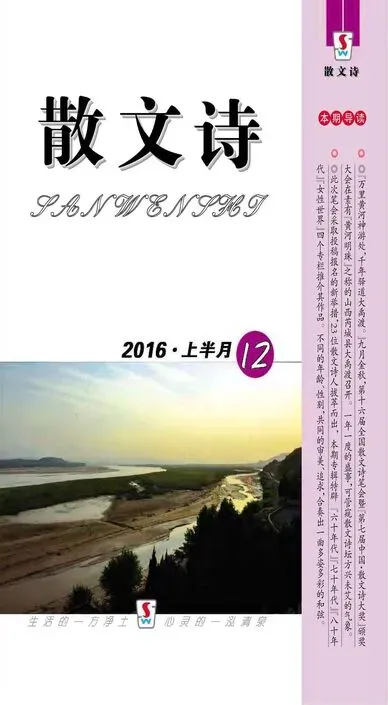西域寫生
新疆◎王信國
西域寫生
新疆◎王信國
心靈沙漠上,散文詩是一泓滋養高貴靈魂的清泉。
風吹著風尋覓風的影子
比如一只野兔,它的毛發被風吹成荒亂的野草。
倒伏,骨頭貼著地殼,聽泥土與植物的誦經。
這是風的影子。只有風吹著風,影子,才那么真實。影子,才有血有肉。
沒有記錄,沒有痕跡,一只野兔完成了屬于野兔的涅槃。它藝術的輪回,或詩意的圓寂,像佛的經典修行。
風吹著風,尋覓風的影子;
風吹著風,尋覓一只鷹埋葬的羽毛。
一萬羽毛,修行一萬年,也走不出風的影子。
看見忍冬花
西風的刀子,戳穿秋天的皮膚,刺向冬天的內臟。
冷寂的云端下,一株忍冬花收攏飛翔的翅膀,不言不語。
遷徙的羊群,時走時停,即使停下腳步,也帶不走一株忍冬花的守望。
在西域,看見忍冬花,就能看見一只鷹的春夏秋冬。
牧者在一個人的馬背上,一遍遍數著羊群;一遍遍數著日漸消瘦的季節;當數到一株忍冬花的背影時,雪期來臨。
看見忍冬花,看見羊群轉場時,牧人消瘦的身影。
讀紅柳
持續大旱。紅柳在干渴中掙扎、喘息。
閱讀,從紅柳開始。從一位女詩人的詩句開始。無需提示,該珍藏的全交給了紅柳。
讀紅柳,讀遺忘了的柔情與心境。那位女子,活在詩句里,笑語盈盈。
對我來說,過去與現在,都那么雷同。
讀紅柳,曾經榮光的部分與挫敗的部分交織、爛漫。
那是一段燃燒的記憶,也是一段燃燒的愛情。活在詩句里的女子,帶著眷戀遠行。
只留下空空如也的天宇;
只留下一望無際風的走廊。
現在,我站在西域大漠,默讀紅柳,默讀失之交臂的愛情片段。
天山之上
天山之上,河流一樣的脈絡,與冰雪一起凝固,與雪蓮花一起綻放。
綻放,在天山之上,既奢侈又素樸。一只鷹對話一輪彎月,讓生死相隨的云杉林,素心如雪。天山之上,我的遠方,比一瓣雪的天涯更遠。
一卷詩書,一壺烈酒,一腔激情,一把冬不拉,足以走近雪蓮花。
天山在上,黑駿馬在下。在下的還有我放牧過的羊群、住過的氈房、用過的奶茶壺、彈過的木吉他,以及永遠不回頭的河流。
天山之上,雁陣馱著姓氏、族別、愛情,遠走他鄉。
琴弦上的宋詞
馬頭琴響起的時候,夏雨開始彈奏潤物的音符。
這是誰的田野與江山?狼群已被宋詞馴服。匕首一樣的獠牙,蛻變成柔軟的動詞。而在形容詞里夜以繼日的圍獵與追捕,早已停止。
琴弦上的雨水,漫過第一朵桃花的記憶,然后,等待第二朵桃花,化繭成蝶。
琴弦上的宋詞,一只黃翎鳥銜著露珠,輪回成女詞人的眼睫毛。
只要眨一眨眼睛,就是一個春秋;
只要眨一眨眼睛,就是一個世紀。
風趕著風逃亡;云牽著云浪跡天涯。只有宋詞,被心跳與眼淚滋養。
一個人的風花雪月,比孤獨更加空闊。馬頭琴弦上奔騰的馬群,落葉一樣四散天涯。
而在宋詞里流浪的風,日復一日自敘、自省、自樂。
鵝卵石不語
鵝卵石不語。還有不語的雪峰,在天山沉默了那么久遠的時光,從未背井離鄉。
一只手緊握另一只手,溫度,是敘述的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在風花雪月的夢境游離。夢境的風景、色彩、語言,是那么清晰,又那么模糊。鵝卵石不語。不語的還有植物的脈絡、奔騰的河流。
春天的一滴露水,或秋天的一條河流,以水的名義,遠走他鄉。
留下鵝卵石,無限沉寂。
不語,有時是一種品質。是一種讓一只鷹奢望了一生,夢幻了一生的品質。
不語的鵝卵石,在經卷里,輪回成另一種鵝卵石。
一粒沙子行走大漠
放逐,流亡,沉寂。一粒沙子行走大漠,胸懷坦坦蕩蕩。
雨水那么遠,飛翔那么夢幻。一粒沙子,是上蒼的孩子。
一粒沙子行走大漠,只要走過苦難,走過風暴,走過空寂,才能敘述,才能綻放。
一粒沙子行走大漠,行走在另一粒沙子的夢境。
在大漠,一粒沙子的春天那么遠,又那么近。一些不愿離開的植物,等待什么,或什么也沒有等待。只有時光留下的碎片,在金子一樣的大漠,化繭成蝶。
一粒沙子行走大漠,行走在屬于自己的指紋里,認祖歸宗。
(王信國1970年出生,新疆作協會員,博樂市作協主席。作品散見《散文詩》《星星》《詩潮》《詩歌月刊》《綠風》《延河》《西部》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