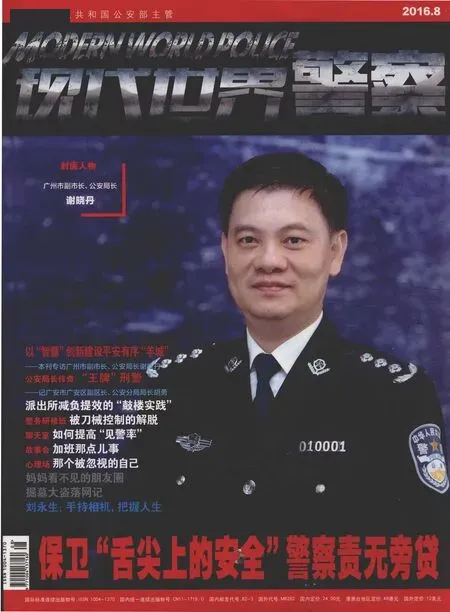劉永生:手持相機,把握人生
文/胡涂
劉永生:手持相機,把握人生
文/胡涂
影像對個人來說是一個形體變化和人生變故的成長史;影像對國家來說是一個興亡成敗的發展史;影像對世界來說則是人類興衰的變遷史。
你現在所拍的每個影像雖然很普通或不被世人看重,可是當影像的生命世代相傳的時候,以前的普通則變得非凡而偉大,偉大的程度可令世人感到震驚!
——摘自“永生博客”

作為一名攝影記者,幾十年手持相機、隨警作戰,劉永生曾被人稱為“領導的御用攝影”“警察圈里的攝影大師”,可在他的心里對自己的定義是——用相機記錄歷史的人。
從拍兒子開始的攝影生涯
劉永生不是科班出身,開始學攝影時,他已經31歲“高齡”,而讓他感受到影像魅力的是他的兒子。1991年,劉永生榮升為父親,看著兒子一天天成長、變化著,他突然覺得應該把這些全部記錄下來。于是,他買了一架二手相機,從捕捉孩子自然神態中體會著影像的曼妙,也在記錄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開始了自己的攝影生涯。
自學是一種痛并快樂的自我修行。自從拿起了相機,劉永生的業余時間就幾乎都被鎖定在那小小的取景框里。從拍兒子到拍景物,從拍景物到拍事件……他不斷摸索著、學習著:用光、取景、構圖、顯影……無數個專有名詞被他的勤奮攻破,越來越清晰的圖像,也培養了最初的自信。可那時,他還不太懂得攝影的含義,甚至覺得攝影和照相應該是同義詞。直到有一次參加全局組織的攝影展覽,他發現獲獎的一張照片,竟然是經常和自己在文件交換站閑聊的治安處的李長根拍的。當時,他肅然起敬,萌生了認真學習攝影的想法。他看到《中國攝影報》上的獲獎照片,覺得照相很容易,便拿著相機走上街頭。可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呼嘯而過的車輛,他卻茫然了。拍什么?怎么拍?此時,他第一次理解了攝影的奧妙,鏡頭是他手中的筆,攝影師的使命就是用鏡頭來表現世界、表達心聲。于是,他把李長根當成了自己的啟蒙老師,在虛心求教中,開始了真正的攝影學習。與此同時,他還訂閱了大量的攝影報紙雜志,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提高自己的技巧和水平。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的家就“一貧如洗”了。因為那時還是膠片時代,他的收入幾乎全部用于購買膠卷、照片紙和顯影定影藥水了。在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他的第一幅作品終于發表了。他永遠也忘不了那張刊登在《首都公安報》上記錄警校學生離別情景的照片。四年同窗,即將天各一方,開始全新的人生。此情此景,只有當事人才能真正體會。他被那些有淚不輕彈的年輕的男子漢們的淚水震撼著,被執手相望的同窗們相互叮囑感動著,于是滿懷真情地按動快門,記錄下這些難忘的離別情景。照片溢滿真情,讓如今已一個個在警營中卓有建樹的“片中人”回望當年,感慨萬千。
有了第一次,劉永生更加自信了,只要自己努力,一定能獲得成功。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勤奮鉆研和不斷實踐,他的攝影作品逐漸出現在《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等主流報刊上,而他也成為《首都公安報》的一名專職攝影記者。
把鏡頭對準所有警察戰友
職業和愛好的融合,讓劉永生陶醉于透過照相機那一方小小的取景鏡來觀察他的警察戰友,記錄他們緊張的工作與無序的生活,表現他們鮮為人知但卻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自從做了專職攝影記者,劉永生有了更多隨警作戰的機會。一開始,他覺得自己只是記錄下他們的工作狀態,從沒想過那些輕薄的圖片會對那些生龍活虎的刑警隊員產生什么樣的作用。
為了獲得更真實的第一手素材,第一次參加朝陽刑警抓捕行動的劉永生要求參與抓捕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在嫌疑人被制伏后再進行拍攝。隊長在行動部署會上,向大家介紹了他的身份。年輕的偵查員們看著他手中的相機,躍躍欲試。他也干勁倍增,白天為辦報紙忙碌,夜里與辦案人員一起蹲守、取證。最后行動終于開始了,可偵查員跳墻進入院內打開大門時,被嫌疑人發現了。偵查員鳴槍警告以后,沖進屋內。黑暗中,幾束手電光成了屋里的唯一光源。劉永生只能借著零亂的光束調焦。隨著快門的“咔嚓”聲,他成功地記錄下抓捕中的每一個精彩瞬間。戰斗結束,屋里恢復光亮。忽然,有人驚呼:“劉哥,你的耳朵流血了?”原來,由于緊貼著鳴槍示警的偵查員,飛迸的彈殼擦傷了他左耳,而他一心想著沖進去,搶鏡頭,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傷痛了……
偵查員們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風采,一邊調侃著彼此的神情,一邊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張記錄下自己年輕身影的報紙。劉永生突然覺得自己的戰友是那樣可愛,自己的工作是那樣有意義。
他在感動的同時,也收獲著戰友們的認可和感謝。2001年,在一次運動會上,劉永生遇到了曾經做過他的封面模特的女警陳蘇。時任經偵處偵查員的她一見面,就激動地說,不久前,她到湖北某地辦案,當地同事認出是她就是某雜志封面人物,給予她明星般的款待,還幫她順利完成任務。還有一個朝陽分局的民警乘火車出差辦案,一名隨意翻看雜志的乘客認出他就是雜志上報道的人物,把他稱為和平時期的大英雄……這些反饋,讓他感受到影像的力量和影響,也更加熱愛他所從事的新聞工作。
2003年春夏,北京民警全部投入抗擊“非典”的洪流。作為一名記者,劉永生責無旁貸地沖在了新聞報道的最前沿,身穿隔離衣,深入公安醫院隔離病區和小湯山“非典”專科醫院,拍攝了2065個影像,真實記錄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首都人民警察堅守崗位、無私無畏、可歌可泣的感人場面……
相比這些積極的方面,更讓劉永生產生創作沖動和欲望的還是老百姓對民警的態度。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社會上出現對警察的負面評價,說什么態度冷橫硬,作風散漫拖。劉永生坐不住了。因為他幾乎每天都和那些基層的民警們生活在一起,親眼看到他們的辛苦、他們的付出、他們的奉獻。不能因為他們連續工作后,偶爾產生的急躁情緒就否定他們所有的努力;不能因為個別的事件,就影響整個公安隊伍的形象。劉永生下定決心,要用鏡頭更多、更廣地記錄下民警的苦和累,讓老百姓理解警察、支持警察。于是,他拍攝萬籟俱寂的夜晚,仍在小區里默默巡邏的社區民警;他拍攝風雪交加的元宵之夜,依然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的巡邏民警;他拍攝千里追蹤歸來,來不及卸下行裝就在椅子上睡著的刑偵隊員;他拍攝滾滾烈火中,上演世上最偉大逆行的消防官兵……就這樣,民警的形象得到了宣傳,而劉永生卻成了徹頭徹尾的“獨行俠”。單位見不著人影,家人只知道他半夜回來過,朋友聚會從來沒譜,知道他忙什么的,大概只有他的相機、存儲卡、電腦和方向盤,可它們又不會說話。而他兒子的照片也隨著工作的忙碌逐漸減少著……直到某一天,他發現那個照片里還一臉調皮的小不點,已經長成大小伙子了。可相冊里,孩子成長的過程幾乎是一片空白。
用相機記錄歷史的每一個瞬間
1997年,劉永生調入首都公安報社,成為一名真正的攝影記者。工作的調動,給了他更大的空間和更廣闊的平臺。他覺得每一天都是新鮮的,每一刻都有做不完的事。
1997年,首都民眾十里長街送小平、香港回歸;2001年申奧成功,舉國歡慶;首都警官合唱團首次赴德文化交流;每年三月的全國“兩會”……劉永生的眼界不斷拓展著。他不但用鏡頭記錄下人們的情感,也在拍攝中有了更深的感悟──警察的身份讓他擁有了別的影友無法拿到的各種場地證件,他一定要拍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
劉永生認為,對于一名攝影師來說,每一天都是有意義的。帶著這個信念,他無比珍惜自己的職業,充分珍視身邊每一件不平凡或平凡的事物,不知疲倦地用獨特的視角記錄歷史的每一個瞬間。
2008年8月24日,是北京奧運會閉幕的日子,劉永生從早上睜眼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一天24小時,只在晚上鳥巢閉幕式現場抽空吃了一袋方便面。而就是這一袋方便面的熱量支撐他捕捉了無數精彩的瞬間,并將其凝固為歷史的永恒。
2009年8月30日至10月1日,是國慶六十周年大慶安保的關鍵時期,49歲的劉永生也經歷了他人生最多的不眠夜。在一個月的時間里,三次連續48小時不眠不休,讓他本來就十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更加嚴重。任務結束后,他反而無法入睡,國產的安眠藥已經失去藥效,不得不服用進口藥物。幾乎是瞬間昏迷般的睡眠持續了一天一夜。醒來時,妻子心疼地問他,你這么拼命到底是為什么啊?他卻振振有詞——在這記錄歷史腳步的日子里,今天你沒拍,明天就再也拍不著了。帶著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感,9月30日凌晨,劉永生就開始了他的“長征”。從東單路口到新華門,從新華門到東單路口,他一刻不停地來回走著,拍著……路上,見他實在過于辛苦的領導,停下車來,執意要捎他一段。可他不能坐車,因為只有不停地走動,他才能發現民警和官兵的每一個感人的畫面,他必須把他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面展現出來,他更要把偉大祖國輝煌的歷史瞬間完整地記錄下來。
回首幾十年從警生涯,劉永生用了知足和感恩兩個詞。因為他覺得,讓自己從一名草根成長為一名獲得了國內外120多個攝影大獎的攝影家的是這個職業,讓自己發現人生的意義和歷史價值的也是這個職業。為此,他熱愛;為此,他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