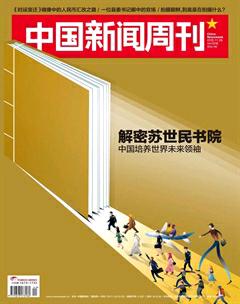拍攝朝鮮,到底是在拍攝什么?
溫天一。
作為目前為止,中國唯一一名獲得朝鮮政府許可進行拍攝的中國藝術家,王國鋒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名攝影師,更多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名導演,借助美術、影像或者媒體等各種媒介,來綜合表達出自己的觀念與思想。
再往前追溯,王國鋒的學術背景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國畫系,畢業后,他覺得宋元山水里的古人心境不再夠承載時代的沉重與深刻,便開始走出從小浸染其中的水墨氤氳,一頭扎進了現實與歷史。
“集體”與“上報”
2011年,王國鋒第一次來到朝鮮。
在此之前,他從沒有來過這個國家。他與大部分中國人對朝鮮的感覺是一樣的,那么與眾不同,但又散發著一種讓人無法回避的熟悉感。
第一次到朝鮮,走下飛機,這個國家留給王國鋒的第一印象是“陌生又熟識,親切又疏離”。
在機場,他沒有看到熙熙攘攘的各國旅客,卻看到清一色穿著黃綠色系制服、樣式類似軍裝的工作人員,他們看起來很年輕,但略帶稚氣的臉上卻掛著統一的肅穆神情。后來王國鋒了解到,機場的這些工作人員并不是職業軍人,事實上,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公務職業制服都與軍裝類似。
而坐在從機場前往的酒店的車上,一片片似曾相識的風景從車窗外緩緩掠過,空曠的街道,穿著灰色與藍色制服的行人出現在大幅標語與宣傳畫的背景之上,這些都讓他覺得有點恍惚。
在首次朝鮮之旅正式成行之前,王國鋒已經花了幾乎三年時間,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與這個國家進行溝通。
在中國,王國鋒是獨立藝術家,并沒有隸屬于某一個官方單位或者團體,他以個人名義與朝鮮官方進行聯系。王國鋒拿著自己的個人資料和拍攝計劃跑遍了朝鮮駐華的一切機構,每個部門對待他的態度全都不一樣,但答復都是石沉大海。
最終,通過一個偶然獲得的、由朋友牽線的非正式渠道,王國鋒送上了之前所拍攝的作品以及自己的拍攝理念資料,并得到了認可。
“等待真是一種磨難。”王國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其實,真正親臨朝鮮,“挑戰”才剛剛開始。
他被安排住在平壤高麗大酒店,那是僅次于朝鮮羊角島國際飯店的另外一個涉外高級酒店。與他同住一樓層的,除了王國鋒自己帶來的三個助手之外,還有朝方派來的一位中文翻譯以及四位工作人員。在隨后的在朝時間段內,王國鋒不被允許單獨外出行動,五個朝方人員與他同吃、同住、同工作,并且,這些朝方工作人員的食宿費用,都需要王國鋒方面承擔。而朝鮮雖然本國消費水準不高,但專門提供給外國人的旅店與飯店,價格卻很昂貴,物價并不亞于一些歐洲發達國家。
“上報”與“集體”是王國鋒對于在朝鮮展開工作的第一感受。
在正式開始拍攝之前,王國鋒已經提前兩三個月提供給朝鮮方面一份詳細的拍攝報告,一一列出自己希望拍攝到的朝鮮各個建筑物。而到酒店入住,簡單的寒暄之后,朝方工作人員立刻就工作計劃與王國鋒進行正式溝通,告訴他,經過嚴格審查的結果,哪些可以拍攝,哪些則必須取消。而那些被允許拍攝的對象,具體的時間和細節也經由官方一一確定核實。“他們不會告訴我原因,只是說,可以,或者不可以。”王國鋒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
在到達需要拍攝的建筑物之時,朝方隨行工作人員會提前拿出類似“介紹信”之類的文件,與當地專屬的管理者再次進行溝通,經過一系列核對交接后,王國鋒等人才被相關人士接待進入。而最讓他驚訝的一點是,與之前在國內拍攝北京站或者美術館等建筑時周圍永遠人潮洶涌的情形不同的是,朝鮮的拍攝現場一片空曠,不是因為朝鮮本身人口密度沒有那么大,而是因為朝方人員在接到通知之時,早已經進行了現場清場。
在拍攝現場,隨著王國鋒一次次按下快門,朝鮮方面的工作人員不時會把相機拿過來,檢查他的拍攝結果。遇到不符合他們標準的情況,他們會立刻要求王國鋒刪除,而某些被保留的成片,在層層遞交給更高級的官方審查過之后,也會再次給王國鋒一些建議,比如“領袖金正恩的形象在照片中顯得不夠突出”。
王國鋒的隨行助理曾拍攝了一張王國鋒工作時的照片,戴著黑框眼鏡的他端坐在三腳架支撐起的相機前面,面無表情,看起來還有點麻木;而在他的后面,團團圍著四個朝方工作人員,一人在揚手指揮,表情激動,另外三人端著手臂,表情凝重。
那幾乎是一個縮影,概括出了他整個朝鮮之行的工作樣貌。
政治、建筑、人
在去朝鮮拍攝之前,王國鋒最被人熟知的作品是以中國和前蘇聯、東德、波蘭等建筑物為主要拍攝載體的“烏托邦”系列。
在拍攝時,王國鋒近距離對準拍攝對象,一個局部一個局部地移動視點進行前期素材拍攝,類似一種傳統中國畫散點透視的方式,后期再通過計算機進行編輯、拼貼合成,將整個畫面全部由巨大的建筑本身所占滿,而所有拍攝時出現的人物,都通過數碼技術抹掉。
在那些作品中,因為沒有多余的樹木或者人物,所以沒有辦法判斷出天氣和季節,因而看起來永遠像是在冬天,天空廣闊而陰郁,仿佛正有風呼嘯而過。由膠片進行拍攝、隨后組合拼貼在一起的碩大建筑上,帶著微弱的顆粒質感,看起來碩大而肅穆,而在每一個細節上,仿佛都在流露出整齊劃一、沉靜無言的氣息。
在王國鋒看來,那些他透過取景框長時間凝視過的建筑:北京站、中國美術館、莫斯科大學、前蘇聯外交部大樓、波蘭華沙被廢棄的前蘇聯領事館……都是一座座在很久之前由于種種原因被樹立起來的紀念碑,承載著遠遠超越它們實際應用功能的意義與語境。
“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逃離社會與政治,它就像彌漫在空氣里的微塵,或者是另一種味道。”王國鋒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形容他拍攝“烏托邦”系列的初衷,“通過這一系列作品我思考的是那一段社會歷史:它們對于今天來說,意味著的是什么。”
但在第一次朝鮮之行結束后,王國鋒開始將注意力由建筑本身,轉移到了人們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在強大的政治與時代語境籠罩下生活著的人們。他的作品在冷冰冰的建筑之外,逐漸有了人物出現。一開始是在龐大建筑的掩映下,那些在看似不經意間被收攏進去的小小生命個體。比如在拍攝平壤某國家級會議中心之時,正趕上修繕維護期間,于是建筑工人與正在慰問的朝鮮女兵文藝團體演出的畫面就被收攏進了鏡頭中,并且在放大之后,幾乎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工人或者女兵臉上凝固在快門按下那一刻的神情。

射擊場女教練員,2015.
隨后,在接下來兩年的朝鮮之行中,王國鋒拍攝了更多由人群組成的大型集體活動與人物合影,并最終落點在一個一個單獨的人物肖像上。雖然在一切活動都要“有組織”“有計劃”進行的朝鮮,真正由藝術家主觀意愿進行的創作幾乎不可能實現,但王國鋒盡可能地在一種由國家力量所掌控的強勁氛圍中,微妙地融入一些并不易被察覺的“主觀性”,并最終將個人意圖隱晦地表達出來。
在王國鋒看來,拍攝朝鮮,這件事情本身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他以一個個體的身份,與一個國家進行了一次合作,而作品實施過程的意義可能要大于完成作品本身的意義。
在拍攝的過程中,他必須時刻保持警醒,并提醒自己始終不忘主觀判斷,“如果我被動地去拍攝他們所安排組織好的對象,則就有被權力利用的可能;如果我想獲得主觀認可的圖像,則是一種充滿風險與博弈的結果。”王國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曾經向朝方提出要求,拍攝一所大學。最終他被帶到了位于平壤的金策工業大學的電子圖書館中,一些穿戴整齊、統一戴著棗紅色領帶的男大學生們早已經提前處于“規定情境”中,聚精會神地緊盯著面前的電腦屏幕進行操作。
王國鋒向翻譯提出,可否要求學生們轉過頭來,集體面對鏡頭,不帶任何表情地完成一張集體肖像。
翻譯隨后與朝方隨行人員商量,再與學校方面對接聯系。獲得許可后,由學校老師與工作人員統一“指揮”,學生們停下手中的操作,集體朝向王國鋒,隨后他摁下了快門,一間帶有縱向縱深感的教室,兩行穿著正裝端坐在椅子上的年輕男孩子們,他們沒有笑,表情凝重,仿佛空氣都凝滯了。
除了大學外,王國鋒還拍攝了大量的中小學以及幼兒園的孩子,其中有位于平壤的朝鮮直屬機關幼兒園,城市少年宮以及一些郊區與農村的孩子。雖然都是“擺拍”,他們大都端端正正地面對著鏡頭,但將這些照片最后擺放到一起,依然能夠從孩子們的衣著、表情或者面色中,捕捉到一些類似階層差異的痕跡。
在進行人物拍攝的時候,王國鋒依然延續著他中國畫式“散點透視”的美學觀念。他曾拍攝了金日成大學的教授一家人,夫婦二人與他們的女兒。這家人是朝鮮的“榮譽家庭”,經常有機會接待一些外國來訪的媒體,朝鮮最高領袖金正恩也曾去家中拜訪過他們,并贈送了一臺電視機。在王國鋒為他們拍攝的合影中,電視機也作為背景入鏡。而最后將成片放在電腦中放大,逐步掃描每一個細節,你會看清圖中每個人胸前佩戴的領導人肖像徽章,他們并不放松的雙手,以及作為背景的電視機上,那張從未被撕下的包裝塑料薄膜。
按照攝影師的習慣,王國鋒下意識地與拍攝人物進行溝通,但隨后就被嚴厲禁止。而幾次進入朝鮮之后,他與隨行翻譯和指派的陪同人員早已熟悉,在工作之外,他也會經常請他們吃飯、喝酒。酒酣飯飽之后,放松下來的他們也會一起開一些家長里短的玩笑,但一旦涉及一點與政治相關的話題,他們的態度會如同被觸碰了開關一樣,立刻嚴肅起來。

在王國鋒的工作室中,還保留著一個類似于霓虹燈廣告牌的環形裝置藝術作品,上面用中文與英文循環往復地寫著“食物有思想”“食物沒有思想”。
這件作品來源于一次王國鋒在北京接待幾個朝鮮來訪人員時候的對話。當時他邀請他們共進晚餐,詢問他們是否愿意去嘗試韓式料理還有肯德基。
在聽到韓國與KFC這樣的詞匯時,朝鮮朋友們的臉上出現了短暫的猶疑,隨后,他們像在心里輕輕地說服著自己,自言自語道,“食物又沒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