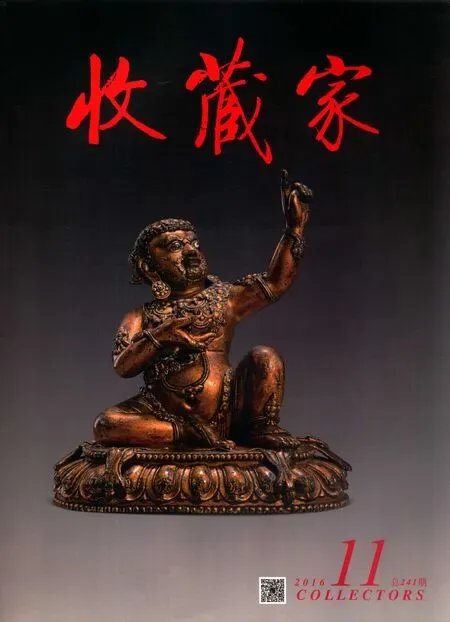吳湖帆與清代三邨
□ 劉曉天
liu xiaotian
吳湖帆與清代三邨
□ 劉曉天
liu xiaotian
清初以來,私家書畫鑒藏群英薈萃、名家輩出,其中尤以梁清標(梁棠邨)、高士奇(高江邨)、安岐(安麓邨)“三邨”最具代表,“三邨”共鑄輝煌,照耀古今,前所未有地推動私家書畫鑒藏達到全新高度,進入嶄新時代。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地區私家書畫鑒藏生機勃勃、方興未艾。吳湖帆作為其中的翹楚和巨擘,風云一時。吳湖帆與清代“三邨”作為不同歷史時期私家書畫鑒藏的領軍人物,會有哪些交集、互動和回響呢?吳湖帆是如何看待清代“三邨”的?筆者借助《吳湖帆文稿》中的相關材料,予以淺顯的回答。
一
梁清標(1620~1691年),字玉立,又字棠邨,號蕉林,又號倉巖,直隸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翰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擢保和殿大學士。長于書法,喜于鑒藏,是清初最大的私家書畫鑒藏家。所藏歷代法書名畫,極為珍貴。凡經其鈐印蓋章的書畫作品,幾乎都為真跡,可惜他沒有留下著錄,其藏品在當時就是南北藏家最想獲取的。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邨,賜號竹窗,浙江平湖人,官至禮部侍郎。工書法,精考證,善鑒賞,收藏名跡甚富,著有《江邨消夏錄》、《江邨書畫目》。《江邨消夏錄》是書畫著錄的集大成者,是后世參考、沿用的典范。
安岐(1685~?年),字儀周,號麓邨,亦號松泉老人。為朝鮮族后裔,居天津,在揚州販鹽。尤精鑒賞,收藏書畫數量多、質量高。乾隆八年(1743年),寫成《墨緣匯觀》,此書為其全部藏品的著錄。身故后,其藏精品絕大部分進入內府。安岐經常在其藏品上鈐印“朝鮮人”,足見故土情深。
高士奇是追蹤梁清標藏品的重要南方藏家之一。《江邨書畫目》記載:“宋李希古《七才圖》”,“棠村中堂藏者。真”。①“宋黃山谷書《古德詩》一卷”,“上上等真跡。梁真定跋”。②
安岐是追蹤梁清標藏品的重要北方藏家之一。《墨緣匯觀》明確提及其所有的三件梁清標藏品,《陸機平復帖卷》,“此卷,余得見于真定梁氏,世傳晉蹟未有若此而無疑義者”,③《顏真卿潘氏竹山堂聯句冊》,“此本為真定相國家藏”,④《顧愷之書畫女史箴卷》,“圖經真定梁蒼巖相國所藏”。⑤
安岐也記載了部分梁清標藏品落入了南方藏家之手,“余向見紫芝臨右軍十七帖冊白粉箋本甚佳,亦項氏物,為真定相國所收,今歸淮安徽人程氏”,“晉顧愷之書洛神賦并圖卷”,“真定相公物,今在淮安人家。”
安岐同時也看重高士奇的眼力。《墨緣匯觀》明確提到十一件來源于高士奇的藏品,多為唐宋元明大家劇跡,絕大部分著錄于《江邨銷夏錄》和《江邨書畫目》。
梁清標作為業內標桿,領袖群倫,高士奇與安岐同為梁清標的忠實信徒,聲名鵲起。時移世易,“三邨”的部分藏品,重現江湖,激烈爭奪,在所難免,諸多藏家無不希冀能從中分得一杯羹,誰有眼力,誰就有機會。“時勢造英雄”,吳湖帆將“三邨”的營養吃透,充實了自己,也譜寫了“一家之言”,流傳后世。
二
吳湖帆(1894~1968年),名翼燕,字遹駿,號倩庵,齋號梅景書屋、四歐堂、雙修閣等,江蘇蘇州人,書畫家、鑒藏家、詞人。與龐元濟、張伯駒、張大千、王季遷、張珩合稱“20世紀中國書畫收藏六大家”。20世紀30年代,受聘于故宮博物院,為1935年“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1937年“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等重要展覽鑒定書畫。
“元四家”之一的黃公望是吳湖帆鐘愛的大畫家,也是他以身家性命努力收藏的對象。吳湖帆是鑒定黃公望的權威,名跡《剩山圖》是梅景書屋的鎮宅之寶。
圍繞黃公望《九峰雪霽圖》的真假鑒定,吳湖帆與梁清標,隔空喊話,再三交流,以吳湖帆挑戰開始,以與梁清標相合而終。
1938年6月26日,徐邦達帶來黃公望《九峰雪霽圖》照片,“以為真跡,非常醉心”,而吳湖帆卻認為,“然此畫余雖未見,覺浮滑不沉著,筆致復纖弱無力,款字亦不佳,決不真,雖有棠邨印無用也”。徐邦達將《九峰雪霽圖》當作真跡,明顯是受到了老師吳湖帆的影響,“梁棠邨鑒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余極力提倡梁之鑒別在安氏之上,近年一輩子都捧梁甚力,邦達之醉此畫亦一時風尚也。”⑧大概從1932年起,吳湖帆就很注意梁清標的鑒藏印章,并且認為梁清標的眼力在安岐之上,但這次梁清標卻被吳湖帆否定了。吳湖帆以書畫作品本身作為鑒定的主要依據,如果書畫作品本身的畫筆、題款存在問題,鑒藏印章作為輔助依據是不起決定作用的。
1939年3月5日,吳湖帆見到“新裝裱”的《九峰雪霽圖》,“此畫裱后頓見神采,較未裝大不相同,畫法殊簡率,頗佳,雖款書略遜,即非真跡,亦必元代善手所摹,下有梁蕉林藏印二,亦真,世傳《九峰雪霽》,即此本也。”⑨3月27日,吳湖帆與孫邦瑞“合購黃畫真跡”,并略數所見黃公望真跡,“余歷年所見,皆不可靠者居多,惟前年龐萊翁所收之《富春大嶺圖》與余去年所得之《富春山居》焚余殘卷兩件,皆著名劇跡。余為黃仲明去年所得之絹本《九峰雪霽圖》,乃梁蕉林舊物,雖不及兩《富春》,亦尚佳。余新獲之大癡畫款識之字與《九峰》在伯仲間,畫更勝之,紙光如鏡,橫裂斷紋甚多,與吾家王叔明卷、季遷新得之王叔明軸皆一類紙也,亦蕉林舊物,可寶也。”⑩吳湖帆在看過《九峰雪霽圖》照片不久以后,就見過未經裝裱的《九峰雪霽圖》實物,但其鑒定意見應與看照片時一致,之后,在見到“新裝裱”的《九峰雪霽圖》時,吳湖帆已經改變看法,認為即便不是真跡,也是同時代的高仿,又過22天,吳湖帆結合題款、畫功、紙張等要素,多方對照,將《九峰雪霽圖》列為黃公望真跡。
吳湖帆對黃公望《九峰雪霽圖》的鑒定充滿戲劇性,可謂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吳湖帆的否定之否定,是肯定、認同梁清標的生動寫照。

黃公望 富春大嶺圖(南京博物院藏)

郭熙 幽谷圖(上海博物館藏)
《梅景書屋書畫記》著錄的“明仇實父尤子求畫周公瑕書長門賦圖”,是一件特殊的梁清標藏品,“原裝冊子藏真定梁式,仇畫右下角有‘梁維樞印’,贉邊有‘梁清遠印’、‘無垢’白文印,卷后有‘葵石子’圓印及梁氏印。按維樞字慎可,崇禎舉人,蕉林相國之父。清遠號祓園,官吏部侍郎,葵石子其別號也。”梁維樞其實是梁清標叔父,梁清遠是梁清標弟弟,此作也說明梁清標家族文化底蘊深厚,有不少人參與了書畫鑒藏。
吳湖帆“捧梁甚力”,主要針對的是上海地區私家書畫鑒藏已經形成的濃厚的追捧安岐的氛圍,吳湖帆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梁清標眼力真在安岐之上嗎?
吳湖帆的書畫鑒藏與高士奇關聯緊密,吳湖帆熟識高士奇的《江邨銷夏錄》和《江邨書畫目》。
1938年3月3日,鑒定“云林小幅”,“此畫為項子京舊物,后歸高江邨,載入《消夏錄》中者。”1939年3月15日,吳湖帆結識藏有夏圭作品的程聽彝。“夏圭卷即《江邨》著錄之十六景卷,程處只存最后四卷而已,故款識舊題均全,其前十二景則早佚矣。”
《梅景書屋書畫記》著錄的“南宋院本桃花鴛鴦圖”的尺寸,與《江邨消夏錄》著錄的《五代黃居寀桃花鸂鷘圖》相比,“依宋尺度之,高三尺八寸毋差”,而寬度是“一尺八寸半”對“二尺”,相差一寸半,“審畫意兩邊似有被截之據,且無江邨印,或因佗故同遭剪裁矣,抑此為宋代院中所摹,亦未可知。”吳湖帆覺得兩者可能是同一件作品。“明蔡九逵銷夏灣記陸包山補圖合卷”,“后有朱臥庵藏印及江邨父子詩跋,載入《江邨書畫目》中”。此作留有高士奇、高岱詩跋,高士奇與高岱并非父子關系,高岱是高士奇的孫子。高士奇與梁清標一樣,也搞家族收藏。

陸機 平復貼(故宮博物館藏)
《梅景書屋書畫記》載:“自以護古為旨,與世夫眩豪夸富者或略有別耳,若云繼孫退谷、高江邨、吳荷屋諸公之后,遣以銷夏,則我不敢。”《梅景書屋書畫記》是吳湖帆謙虛地向孫承澤、高士奇、吳榮光等前輩學習和借鑒的結果,以學術研究為目的和根本,與凡夫俗子不可同日而語,其體例沿襲了《江邨銷夏錄》。作為文人士大夫的后人,吳湖帆與暴富新貴缺少共同語言。梁清標與高士奇,作為文人士大夫,自得吳湖帆高看,安岐作為販鹽的商人,先天不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自己在吳湖帆心中的地位。
吳湖帆將梁清標與安岐直接比較,堅持認為梁清標的眼力在安岐之上,并不是有意貶低安岐,其實吳湖帆這樣做是頗費苦心的。
安岐的眼力早就得到公認,吳湖帆并不質疑安岐的水平。1933年1月31日,吳湖帆見到安岐舊藏、著錄于《墨緣匯觀》的郭熙《幽谷圖》,“絹本真跡,筆墨生動,百讀不厭”,此等寶物理所當然被吳湖帆收入囊中,但一通感慨卻意味深長,耐人尋味,“安岐以一屨人侍權臣明珠,居然受寵起家,擁資百萬,張羅書畫,所收不少,刻《墨緣匯觀》一書,名襲以傳,近人之談收藏者亦引為考據,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為朝鮮人,明珠枋國時賄賂通私,明敗而安亦沒籍,所藏畫歸內府矣。觀安之所藏,未嘗見有只字,安之無文,可知校項子京亦不可同語,況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并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書畫之一厄也。”
安岐出身卑微,但聰明伶俐,倚仗權貴,發家致富,鑒藏書畫,憑《墨緣匯觀》影響后世深遠。安岐從未在藏品上題字,其文化知識無法和項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相比,可現實是好多人連安岐都不如,還自以為是,以為有了著錄,就萬事大吉,這種荒謬之舉,不盡使吳湖帆扼腕嘆息。“一般人購畫處處以著錄為據者,真有盲人瞎馬之誚也。”更為嚴重的是,“若近日海上諸大收藏家津津樂道印章多寡,自夸鑒別之精,問以如何好處,古書古畫何從可貴,皆瞠目不能語,皆憑得價之貴賤為標準,直可玩鈔票為愈耳。大腹賈好談風雅,其實目不識丁,何足以語書畫妙處。”上海地區私家書畫鑒藏存在拋開書畫作品本身,卻以印章、價格、名頭、質地、題跋、著錄、品相、裝裱等為標準的弊端,而這恰恰是吳湖帆極力反對、批判并努力矯正的。當然,受限于時代與資料,吳湖帆對安岐的認識并不準確、全面,而安岐有這么大的號召力,也并不是安岐故意造成的,責任在錯誤追捧他的藏家身上。
吳湖帆借古諷今,樹立反面教材,這樣的安岐自然無法和梁清標比較。吳湖帆以找到“病根”,他懸壺濟世,憑一腔熱血,義無反顧。
首先,吳湖帆尊重前輩、權威的同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看待他們的眼力和水平,并不一味茍同、盲從。
龐元濟(1864~1949年),字萊臣,號虛齋,浙江吳興(今湖州)南潯人。是“六大家”之首,編著《虛齋名畫錄》、《虛齋名畫續錄》等。
吳湖帆一針見血地指出龐元濟“但知題跋,不明畫理”,因此“仍不能深刻,故舊作偽品往往欣受之”。吳湖帆后生可畏,勇氣可嘉,梅景書屋冉冉升起,改變了上海灘龐元濟一家獨大的格局。
其二,吳湖帆敢于否定錯誤的鑒定意見,更敢于購買被否定的書畫作品。1933年4月6日,將“無目者咸以為贗鼎”的“董文敏書畫冊”,鑒定為“董冊中至佳者”,“精品”。1938年5月7日,“以自畫三尺山水一幅”換得“紙破不堪,千瘡百孔,修補綦難,他人皆不敢購”的“為華補菴作”、“文衡山《玉蘭圖》”。
諸如此類記載比比皆是,許多書畫作品的命運因為吳湖帆的膽識得以改變。
其三,吳湖帆著書立說,針砭時弊,將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觀點形成理論加以表達。1937年4月5日,吳湖帆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鑒藏觀。“余擬撰《然犀錄》,專以發揭前人著名偽跡為旨,以后人不致盲從為本。雖所見有限,終比不說為妙,深知必有人反對,但盡我良心為標準,決非妄攻人短也。”據說點燃犀角可以照見怪物,“然犀”有明察事物根本之意。吳湖帆認為得憑良心說真話,不惜得罪人。《梅景書屋書畫記》亦與之呼應,與時俗拉開距離,“吾書一以真跡為斷。如他家不錄絹本,不收法書,此皆偏闕成見,力矯斯弊。”“此皆余個人嗜癖所及,智失愚得,姑不備論。非吾道者,可不觀諸。”
三
清代“三邨”能夠成為私家書畫鑒藏的頂級人物,他們的掌眼人功不可沒。梁清標與張黃美、吳升等人關系密切。安岐則有王翚和顧維岳,《墨緣匯觀》“僧巨然雪圖”記載:“憶甲午歲十二月,余在吳門,時久雪初霽,顧維岳從玉峰攜來,與石谷同觀于吳江舟次。”
吳湖帆主要依靠自己的眼力從事書畫鑒藏,并為他人掌眼,耳熟能詳的就有張珩、錢鏡塘、蔣穀孫、徐邦達、王季遷、劉海粟、潘博山、葉恭綽、徐俊卿、孫伯淵、吳賓臣、吳壁城、彭恭甫、孫邦瑞、劉定之、黃仲明、顧巨六、曹有慶等等。
清代“三邨”重視鑒藏印章和著錄,但論臨摹書畫,皆不如吳湖帆,通過臨摹,吳湖帆提高了鑒定的準確性。1933年2月13日,“臨惲南田《茂林石壁圖》,此為余所見惲畫第一品,筆墨恣放,睥睨一世,洵為奇跡”,“惲之為何等瀟灑曠達,豈其畫如弱女子哉!今獲此圖,始信惲畫之真面目,其纖弱一種蓋皆贗鼎耳。”吳湖帆真正被青史銘記,并將“三邨”在內的歷代大藏家拋之身后的是吳湖帆對人才的培養與呵護。吳湖帆愛才、重才、惜才,無比看重熱愛書畫鑒藏的青年才俊。弟子王季遷、徐邦達后來成為棟梁之才,是離不開吳湖帆的悉心教導的。青年沈劍知、張珩努力專研,吳湖帆同樣寄予厚望。
沈劍知(1901~1975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沈葆楨曾孫。“劍知畫派甚正,目光亦不偏,鑒別力殊深刻,所嫌看得不多,再多觀摩,必成鑒別專家無疑,近日不可多得之同志也。”
張珩(1914~1963年),浙江吳興(今湖州)南潯人,字蔥玉,號希逸,建國后的書畫鑒定大師。1939年4月19日,吳湖帆在觀看了張珩的部分藏品后,由衷感嘆:“蔥玉年才廿六,所藏法書為海內私家甲觀,而自書仿元人亦至佳,洵少年中英俊才也。”吳湖帆練就一雙火眼金睛,縱橫上海灘而屹立不倒,所謂“藝高人膽大”,他不藏著掖著,想做就做,憑過硬的真本領去改變對書畫鑒藏不利的因素和環境,這是可貴的。吳湖帆這種多少帶有殉道精神的行為是勇敢的,清代“三邨”作為高峰,并沒有成為他的負擔,相反,他繼續向前窮追猛打,成就了屬于他自己的豐碑,吳湖帆不僅是書畫鑒藏的大家,他更是書畫鑒藏這一文化事業稀有的捍衛者和超越者。
注釋:

吳湖帆 臨郭熙幽谷圖(西泠印社2009年春拍)
①、②(清)高士奇撰,邵彥校點:《江村銷夏錄(江村書畫目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4頁。
③~⑦ 安岐著,張昌熙標注:《墨緣匯觀》,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責任編輯:尹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