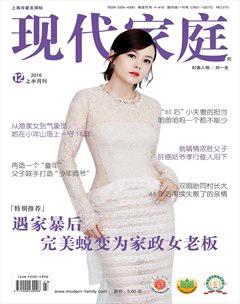張悅然得到了饋贈
起初,張悅然的父親并不知道女兒將自己未發(fā)表的一個故事,寫成了一部長篇小說。當女兒的《繭》需要送給朋友們閱讀時,他幫著寄出去一些。“他大概會翻一下,也許知道了里面的內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帶有“傷痕文學”氣息的故事,只不過是中文系出身的父親向女兒顯示自己也曾寫過小說的證明。他已找不到底稿,甚至記不得當年是向上海哪家文學雜志投的稿。他的小說沒有發(fā)表,過了些年,他自己都忘了小說的具體內容。

《繭》出版后,在各場新書交流會上,張悅然幾乎都會把父親的故事講一遍。大家知道了,這位女作家的父親在讀大學之前是糧食局的卡車司機,做過文學夢——
我爸爸是1977年考上的山東大學,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讀的是中文系。他在1978年寫了一篇小說,名字叫《釘子》。故事發(fā)生在他當時住的醫(yī)院大院里。他大概十三四歲。大院里的一個叔叔,遭人迫害,變成了植物人。兇手一直沒有抓到。對我爸來說,這是他童年里觸動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當他在1978年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想著把這件事情寫下來。
他的小說投到上海那家文學雜志后,編輯回信說很好,決定采用。可是,不久,編輯又給他寄了一封信說,上面的人覺得這篇小說調子太灰,可能沒有辦法發(fā)表了。爸爸聽了很失望。
張悅然的父親從山東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工作,結婚生女,寫作這件事情慢慢就淡了。當這個故事反復通過父親的講述出現(xiàn)在女兒面前時,她心里對這個故事生發(fā)出了某種難以道明的感情,仿佛從父親那里繼承了一筆饋贈。她決定把這個故事重新寫成小說。
醫(yī)院大院也是張悅然長大的地方。醫(yī)院的環(huán)境似乎是反童年的,那是一個離開世界的通道。醫(yī)生身上那種理性地對待生死的態(tài)度,帶給孩童一種堅硬的沖擊。為了寫小說,她回到醫(yī)院,通過工作人員找到一份植物人的檔案。“他一直在醫(yī)院里躺著,被照顧得很好,從來沒有生過褥瘡,一直躺到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在張悅然看來,父親是歷史的“旁觀者”,她是“旁觀者”的旁觀者,于是有了《繭》。張悅然以前寫的小說,并不想讓父親看到。但這一次,她覺得可以鄭重地把《繭》送給父親。寫這本書的時候,她原本沒這樣的想法。寫完后則覺得,這本書也許不僅僅是給80后或者90后看的,50后和60后也許會很想知道他們的子女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之前的歷史。
“他可能會覺得,我的女兒看到的年代是我經歷的那樣嗎?”張悅然說,”真實和虛構之間產生了我們周遭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