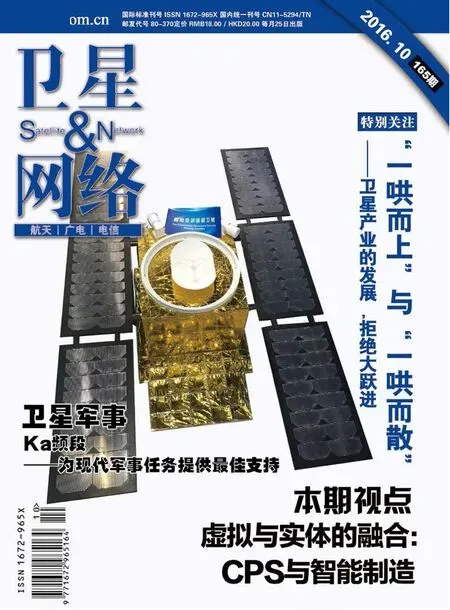近年來我國發射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衛星
近年來我國發射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衛星

2013年9月25日發射的快舟一號,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衛星技術研究所研制的一型主要用于各類災害應急監測和搶險救災信息支持的小型衛星。


2014年9月4日,由北京信威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清華大學共同研制的靈巧通信試驗衛星發射升空。
2015年9月21日,天拓系列的“天拓三號”微納衛星成功發射。“天拓三號”是由6顆衛星組成的集群衛星,包括1顆20公斤級的主星、1顆1公斤級的手機衛星和4顆0.1公斤級的飛衛星。

2015年10月7日12時13分,我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功將1組“吉林一號”商業衛星(1顆光學遙感衛星、2顆視頻衛星和1顆技術驗證衛星)發射升空。“吉林一號”衛星是我國第一顆以省命名的自主研發衛星。
或許有人會說,“一哄而上”也是一種大浪淘沙,“一哄而散”之后,剩下的少數堅守者才是精英和產業棟梁。此言并非沒有道理,但我們在這個時候站出來反對小衛星的大躍進,是因為航天產業與鋼鐵、汽車、家用電器、互聯網甚至房地產等產業,有著本質區別。
60年前的那場大躍進,本質上是因為鋼鐵產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改革開放以來的汽車、家用電器、手機、平板電腦等產業的發展狂潮,也是因為存在著龐大的消費需求。國內投資的一擁而上,主要是為了替代進口、滿足需求。熱潮過后,確實培育出了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
但航天產業并不能做這樣的類比,對航天,特別是小衛星遙感,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現實需求缺口。實際上,國內已經發射升空的資源、高分系列和北京一號、吉林一號,都面臨著需求引導不足,市場能力不足的問題。北京一號作為地方政府主導遙感衛星的先例和范本,雖然在應用領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得到了有關領導的表揚,但在市場銷售上并不盡如人意。北京一號的運營商就多次在各種場合表示,希望政府能增加采購。那么,各地積極籌建的小衛星系統打算為誰服務呢?難道某地的小衛星只為某地拍攝嗎?這對于全球運行的衛星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很難面對這樣的推敲的,多少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進一步考慮到吉林一號打算建設138顆衛星的星座,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打算建立一家商業航天公司來運營全球高分星座,遙感衛星實際上已經供應過剩了。如果從經濟角度判斷,各地完全不需要再發射自己的遙感小衛星。
衛星資源“供大于求”的問題,并非中國獨有,在全球衛星市場中也普遍存在。最近,《休斯衛星通信》發表了一篇就衛星資源供大于求的問題訪問SES的CEO(Karim Michel Sabbagh)的文章——A Clearer Perspective - What is Oversupply?
文章中提到,隨著越來越多HTS衛星發射升天,衛星界紛紛議論衛星資源的供需平衡被打破,衛星帶寬價格即將大幅度下跌。衛星運營商們似乎覺得災難即將來臨。
對此,Karim Michel Sabbagh認為,“直到最近,高級管理人員和分析師們還在以衛星部署的多少來衡量成功與否,還在以是否擁有最大容量衛星(以GHz、GB甚至TB計)來評價該運營商是否有競爭力。我一直覺得這樣的思路不可取。在地面移動通信領域,在某段時間大家也在盲目部署無差異化的移動網絡,在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后才意識到這種做法是錯的。”
這番話,值得衛星產業(特別是地方性小衛星產業)的決策者們深思。

衛星資源“供大于求”的問題,在全球衛星市場也普遍存在。
兩個缺失:“小衛星”發展中難以逾越的障礙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問題是不容忽視和回避的。
首先是基礎技術的缺失。除了清華大學、長春光機所等傳統高水平科研單位,多數地方小衛星的研制更注重于衛星總體裝配,卻很少有人在星載關鍵器件、組件、分系統等方面下功夫。考慮到國內商業現貨器件的發展水平遠遠不如美國,許多元器件尚屬于軍品,商業公司無法買到。對小衛星性能、質量、可靠性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是商業模式的缺失。哪怕是作為商業遙感衛星先鋒的吉林一號,至今也沒有拿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盈利模式。商業公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籌建的全球星座,更是難以找到自己的市場空間。
這兩個方面的缺失,并沒有引起小衛星相關各方的重視,抑或是被選擇性遺忘,但不可否認,這是“小衛星”發展中難以逾越的兩個障礙,從現實條件來看,并無太好的解決辦法。
中國的傳統文化,總是非常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倫理以及達觀的人生態度,例如,百年大計,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財富觀念。但落實到每個人自己身上,往往卻讓自私與貪婪的短視觀念和行為所左右,人性的弱點也可見于此。由此,我們不禁要問:面對供大于求、科研水平低下和商業模式缺失的現實,熱衷于小衛星的地方政府為什么做不到保持一分淡定和清醒?中國的傳統文化,美好而深邃,但落實到我們每個人身上,就做不到大局觀和長遠,做不到為未來20~30年乃至100年的經濟發展而謀略與布局,在一時的熱鬧和政績的需求面前,亂了陣腳。難道每個人都只看重自身利益,是為政之道嗎?那這個“政”長遠的意義又何在?為什么不能放下眼前的短期利益,更多的從內心深處憂心一下祖國的未來,憂心一下我們的子孫后代不被欺辱和有尊嚴的未來。
如今,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迫在眉睫,如此下去,從何談起?智能制造2025的愿景,如何真正穩步實現?
“小衛星沖動”的深層原因及負面影響
要解釋上面的疑問,就要對“小衛星沖動”背后的深層原因進行分析。(我們姑且將“小衛星大躍進”中各方的心態稱之為“小衛星沖動”)
各方利益的聚合導致“小衛星”沖動。
小衛星熱潮的推動者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地方政府、企業、科研機構。
就地方政府而言,產生小衛星沖動的原因并不復雜。
一是航天業作為公認的高技術產業,將小衛星項目作為政績、形象工程的一個高級標簽,既可展示本地對于自主創新的重視,也使相關創新基金有一個說得過去的投放方向。在這種情況下,衛星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并不是考慮重點,重要的是其承載的象征意義。
二是源于地方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這一艱難過程中產生的焦慮,尤其是在尋找自主創新的突破口遭遇困難和挫折時,一旦遇到具有高新技術特征的航天業時,產生如果研制和發射一顆衛星,是不是可以帶動本地的產業升級和創新,進而打破困局、搞活經濟這樣的期待就毫不足怪了。
就企業而言,產生“小衛星沖動”的原因不外下述幾個方面。
一是獲取地方政府相關創新基金及其他優惠扶持政策;二是瞄準航天商業開發和應用的巨大市場空間;三是意欲打破航天業央企壟斷的市場生態,獲得競爭的制高點。
此外,還有個別企業抱著利用小衛星項目提高估值,包裝形象甚至作為融資手段的目的而竭力鼓吹,這類企業在進行小衛星項目時往往回避自身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和缺陷,從而產生很大的隱患,更有甚者,并不在意項目的成敗而導致亂象叢生。
就研究機構而言,參與其中的主要動力往往是將“小衛星”作為自身商業化運作的突破點和機會。
上述三方利益的聚合往往使各自的“小衛星沖動”協同為現實的小衛星項目。但可以看到,上述各方由于其各取所需和不斷變化的功利化利益訴求,決定了他們在發展小衛星的過程中往往著眼于短期行為和眼球效益,甚至不惜違規違法,對衛星產業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傷害。
對衛星產業鏈條和商業運作認知不清晰甚至存在誤區。
地方政府作為“小衛星”熱的主導者,對衛星產業鏈條和商業運作認知不清晰甚至存在誤區,是盲目發展小衛星的重要因素。主要體現在:
首先,總想站在產業鏈條的上游和頂端,反而忽視現有資源是否在應用層面涵蓋了小衛星的功能和作用,導致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衛星產業是一個包括研發、制造、發射、應用、商業開發等等一系列活動的復雜鏈條,每一個環節既相互聯系又明確分工,越是上游鏈條,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越高。地方政府或出于政績和宣傳考慮,或出于提高當地自主創新能力考慮,往往瞄準衛星產業鏈條的上游和頂端,而對大有前景和空間的衛星應用、商業開發等并不重視。但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小衛星雖小,卻也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越過的技術門檻是相當高而且多的。地方政府很難具備這樣的能力和資源,其結果往往是霸王硬上弓,造成不但完全難以為這些小衛星找到合適的應用模式,甚至不能相信它們在技術上的成熟度和可靠性的尷尬局面。
其次,追求小而全。抱有帶動上下游產業的幻想,未意識到小而全正是衛星產業的大忌,很可能產生尾大不掉的爛尾工程,甚而發展到“大到不能倒”的程度,這不僅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對地方經濟發展也會造成極大傷害。
再次,盡管也有一些地方的小衛星瞄準了有需求、有潛力的通信市場。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低軌道通信衛星是一種全球運行的無線電設備,對于頻率資源的使用,必須經過國內國際的充分協調。沒有足夠的頻率資源,哪怕把衛星研制出來、發射上天,也不能投入使用。這其中密布的政策、法律和經濟陷阱,迫使世界各國不間斷地實施艱苦、繁瑣而漫長的協調。初來乍到者可能連國內協調這第一道門檻都翻不過去。根據我們與多家小衛星籌辦單位的接觸,這并非危言聳聽。
商業運作模式不成熟或缺失,對市場只有大而粗的認識,缺乏將市場轉化為效益的途徑和方法。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國內已經發射升空的資源、高分系列和北京一號、吉林一號,都面臨著需求引導不足,市場能力不足的問題。衛星上天了,才來找市場,而現實的市場又與想象中的市場大相徑庭,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這是目前許多小衛星企業面臨的尷尬和困擾。
顯然,小衛星商業運作模式的不成熟或缺失,對市場的認識誤區和錯誤判斷,是助長“小衛星沖動”的另一重要因素。
“小衛星”熱潮下的冷思考
首先,清醒認識產業鏈,找到進入衛星產業的最佳切入點。
航天產業和其他任何產業一樣,都有完整而可以持續運行的產業鏈條。這個鏈條的重點,是廣大的消費者。在這個鏈條上,許多環節未必光芒耀眼,但缺乏任何一個,都會導致整個產業鏈不能發揮作用,所有的投資都將可能有去無回。
衛星行業的產業鏈包括衛星制造、發射服務、衛星測控與運營、終端銷售、數據與增值服務等幾個大的環節。在衛星通信廣播行業,人們對節目、帶寬的需求不斷水漲船高,也就是說數據與增值服務的市場一直在擴大,帶來了對上游環節的持續需求。所以,主要衛星通信運營商一直在訂購新的衛星,不斷擴大衛星數量和通信容量,帶動了衛星制造和發射服務的發展。
小衛星的產業鏈與此相同,不同之處是小衛星制造和發射服務的投入比傳統衛星要少得多、門檻比較低。因此,如果產業鏈運行順暢,這能夠帶來數據和增值服務價格的顯著降低。但是,假如這兩個下游環節根本不存在,那么上游環節的存在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從國內情況來看,最大的問題是現有衛星的應用不充分。無論通信廣播還是對地觀測,都有大量空間資源閑置。也就是下游環節中的應用市場并沒有充分建立和運行起來,雖然衛星在人民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遠遠沒有達到商業化、市場化、產業化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對想要投身商業航天和小衛星的單位和組織而言,最應該做的是積極培育終端市場,開發消費級應用模式、創造用戶基礎。在應用中,才能創造和發現對空間段的需求,推動衛星制造和發射服務的發展。脫離用戶基礎發展小衛星,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
其次,正確認識“供大于求”,選擇合理發展道路。
正如前文中提到,衛星資源“供大于求”的問題,并非中國獨有,而是在全球衛星市場中普遍存在。對此,SES的CEO(Karim Michel Sabbagh)在A Clearer Perspective - What is Oversupply?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很有借鑒意義的觀點:
首先,他認為帶寬就是帶寬,僅是一種商品;不同運營商之間的差異化能力總能幫助運營商們找到新的市場機會,整個行業終會象往常一樣發展。長久以來,商業衛星運營商們都在忙著制造新衛星,忙著在新地域部署衛星覆蓋;他們只專注于滿足客戶對通信容量的需求,并報以相應的帶寬價格。
這種經營方式在過去沒有問題,但不適合新應用、新技術不斷涌現,多種商業模式層次不窮的當今和將來市場。如果運營商們的經營方式跟不上市場需求的變化與發展,并且大家簡單地理解衛星資源過剩,這最終會加劇運營商之間的帶寬價格戰。
其次,他提出,如果認為有了一個體系龐大、自封閉的衛星系統,就可以解決所有通信需求問題,這種觀點是不對的。(衛星)公司要實現業務的中、長期成功發展,需要做好2個方面工作:第一,在公司內部建立能支撐全球、有效適應各種情況變化的能力模型(包括對整個衛星星座、每顆衛星);第二,要沿著整個價值鏈(而不僅是衛星),要根據客戶需求情況的變化對能力模型進行不斷改進,這樣才能更好地服務所有細分的目標市場。
最后,他認為合理的發展道路應該是——對于每個新開發項目,我們必須要清楚我們想做、能做的市場是什么,我們是否具備差異化能力,我們是否有革新的、可靈活調整的方法和途徑。如果缺少這三個因素,則整個項目發展的過程就可能會發生三個方面的問題:低估了總體時間表,低估了所需的資源,低估市場和可替代產品的演變。
要做到這一些,我們在技術和操作層面上要采取的措施都必須是自適應、可擴展的,要注重耐心的市場培育和管理。這些沒有捷徑。
由此,他得出的結論是,衛星行業會繼續很好發展,不會是因為供大于求,也不是因為資金充足,而是因為一些運營商能夠不斷根據千姿百態的市場變化調整他們的業務方式,不受那些吸引眼球的大型星座、“供大于求”等宣傳的影響。
再次,政府應當有準確定位
地方政府有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職責,這是無可非議的。在當今嚴酷的市場形勢下,地方政府為了產業升級所能做的選擇也確實相當有限。然而,航天產業和其他所有產業一樣,有著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的航天產業,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意志非常旺盛,反而無法得到充分發展。
衛星產業確實屬于高技術行業,能夠對周邊產業起到一定的帶動作用。但前提是真正按商業規律辦事,讓市場去選擇某個具體地方適合發展什么樣的產業鏈環節。如果說一定要把本地打造成衛星制造中心,那么不妨看一看北京和上海的衛星制造能力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這兩地的航天產業從建國后不久即開始籌劃,國家不但在財力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勒緊腰帶建立了航天科研制造單位,所需要的龐大投資絕不是某個地方政府有能力籌措和承擔的。更重要的是廣泛召集優秀科學家和科技人才,后來榮獲兩彈一星元勛榮譽稱號的諸多科學家和院士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某個地方打算自建衛星制造能力,不妨審視一下自身的資源,看一看能不能請來哪怕是一位能夠與他們相提并論的領軍人物。

長沙天儀空間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中國首批商業航天公司之一,天儀研究院專注于利用低成本的商業微小衛星為不太為人關注的太空科學實驗、技術驗證這一細分市場提供服務。2016年7月獲得數千萬規模首輪融資,成長迅速。圖為公司CTO任維佳和副總工程師王長安在對“瀟湘一號”做出征前最后的測試。
因此,地方政府應當做到的,是因地制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優先推動衛星服務業的落地,為本地居民和產業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發展環境,營建好衛星產業鏈的應用端和市場端。作為二三線城市的地方政府,還需要注意扶植弱小。真正為民生服務的衛星應用企業,可能規模小到只有幾個人。但這正是衛星產業接地氣的毛細血管。發射一顆小衛星、哪怕是立方體衛星的基金支出,足夠培育起許多個這樣的小企業,不但解決就業,還能從實質上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對小衛星產業發展模式的建議
事實上,中國的小衛星產業還處在尋找模式的階段。因此,我們很難在這里給出什么必定行之有效的模式。不過,我們可以給出一種用來尋找模式的模式。
首先,我們應當把小衛星的用途分為兩類,一類是教學科研,一類是商業應用。
作為教學衛星,主要是針對學生,培育航天后備人才。這類衛星主要是解決有無,應當由政府教育和科學技術普及部門出資,讓盡可能廣泛的學生積極參與。只要衛星上天,接通信號或者下傳圖像,就達到了目的。但是這種衛星不應當設定過高的指標,也不應當投入過多的資金。
作為科研衛星,主要是解決關鍵技術的突破。這其中就應當有所選擇,對于那些國內已經成熟、其他機構已經能夠拿出成熟產品的技術,地方政府就應當慎重,不應當輕易出資支持。否則有過度建設重復建設的可能。對于那些確實處在尖端、前沿的技術,就應當大力支持,這有可能帶動起一系列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
作為商業衛星,我們建議建立一種機制,交流信息、統籌資源。地方政府可以在這種機制下,分析本地的優勢和劣勢,把有限的資金注入產業基金,再通過產業基金籌措人才、技術、渠道等重要資源,建立起適合于本地實際情況的產業基礎。與其他地方相輔相成,共同建設完整、可持續運行的小衛星及其應用產業鏈。

作為我國首顆由高校學子自主設計、研制、管控的納型衛星,“紫丁香二號”凝聚了哈工大航空宇航與科學技術、力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機械工程等8個學科的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累計40多名學生的團隊參與設計與研制,平均年齡不到24周歲。核心成員最大年齡為1991年出生,最小的是1995年生人。
結語
毫無疑問,大躍進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商業航天領域。如果說航天能為地方經濟的升級轉型提供些什么的話,那也應該是建立在充分認識和了解本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有選擇、有目的地引入航天技術和航天應用,真正使它們發揮作用。
航天產業不但自身能為社會提供更多優秀、先進的產品和服務,更重要的是能對傳統產業起到改造和升級作用,創造出新的產業、新的行業;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創造出新的財富,有效地減少傳統經濟模式中對資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破壞,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無論發射衛星還是發展商業航天,都應當首先考察自己是否能起到上述作用,如果不能,就一定是選錯了發展方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決策是否正確。
至于那些打著搞航天、建星座、造衛星的旗號,騙取政府創新基金或政策優惠的人,應當立即逐出航天領域。不能讓他們靡費人民的血汗,也不能允許他們有損航天業的形象和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