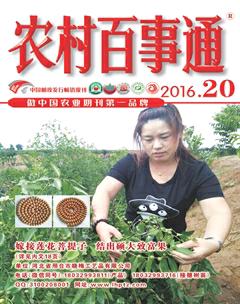“假”離婚的法律風(fēng)險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有不少夫妻想通過“假”離婚的方式規(guī)避各種責(zé)任或獲得某些好處。然而,看似巧妙的方式背后卻風(fēng)險重重。
案例一:“假”離婚,真買房
孫某和藍(lán)某系夫妻,雙方戶籍均在北京,婚后兩人購買住房兩套。2015年年初,孫某判斷一年內(nèi)房價有大漲趨勢,遂打算投資一套房產(chǎn)。但按照北京市限購政策規(guī)定,孫某和藍(lán)某已無購房資格。為取得購房資格,孫某與藍(lán)某商定辦理“假”離婚。離婚協(xié)議中約定,兩套現(xiàn)有住房及家庭其他財產(chǎn)均歸藍(lán)某所有,兒子孫甲歸藍(lán)某撫養(yǎng),孫某每月支付8000元撫養(yǎng)費。2015年4月,孫某與藍(lán)某辦理了離婚手續(xù)。孫某于2015年12月簽訂了一份購房合同。然而,由于離婚后孫某名下沒有任何財產(chǎn)且還貸能力有限,銀行貸款始終沒批下來。到了2016年3月,房價暴漲,孫某想通過法院修改離婚協(xié)議,把其中一套房產(chǎn)劃歸為自己所有,但又怕“假”離婚被識破進(jìn)而喪失購房資格。
案例分析:本案中,孫某為取得購房資格,與藍(lán)某辦理離婚手續(xù),當(dāng)沒有證據(jù)證明簽訂離婚協(xié)議存在欺詐、脅迫等事由時,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離婚協(xié)議中約定的房產(chǎn)劃分對于孫某及藍(lán)某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孫某也就喪失了兩套房屋的所有權(quán),因此原有房產(chǎn)無法作為抵押財產(chǎn)。此外,假離婚屬欺詐行為,如果確有證據(jù)證明夫妻雙方是假離婚,因此取得的購房資格和按揭貸款不受法律保護(hù)。
案例二:“假”離婚,真躲債
王某與趙某于2014年結(jié)婚,婚后兩人經(jīng)營一家水果店。由于經(jīng)營不善,截至2015年年底,雙方對外負(fù)有約6萬元的債務(wù)。為了規(guī)避債務(wù),2016年2月,王某與趙某簽訂離婚協(xié)議,約定雙方此前擁有的一切財產(chǎn)歸趙某所有,王某“凈身”出戶。婚姻存續(xù)期間的一切債務(wù)均由王某承擔(dān),與趙某無關(guān)。此后,王某與趙某到民政部門辦理了離婚手續(xù)。
2016年4月,王某因確實無力獨自償還債務(wù),遂要求趙某拿出原婚姻存續(xù)期間兩人的共同存款2萬元償還債務(wù),并提出復(fù)婚。可趙某拒絕了王某的復(fù)婚要求,并稱她與王某已簽訂離婚協(xié)議并辦理了離婚手續(xù),離婚協(xié)議明確約定,一切債務(wù)由王某承擔(dān),故自己不負(fù)有償還義務(wù)。
案例分析: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fù)的債務(wù),應(yīng)當(dāng)共同償還。”有關(guān)司法解釋進(jìn)一步明確,債權(quán)人就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fù)債務(wù)主張權(quán)利的,應(yīng)當(dāng)按夫妻共同債務(wù)處理。當(dāng)事人的離婚協(xié)議或者人民法院的判決書、裁定書、調(diào)解書已經(jīng)對夫妻財產(chǎn)分割問題作出處理的,債權(quán)人仍有權(quán)就夫妻共同債務(wù)向男女雙方主張權(quán)利。一方就共同債務(wù)承擔(dān)連帶清償責(zé)任后,基于離婚協(xié)議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向另一方主張追償?shù)模嗣穹ㄔ簯?yīng)當(dāng)支持。
根據(jù)上述法律規(guī)定,夫妻雙方在離婚協(xié)議上對債務(wù)的分割只能在夫妻雙方之間產(chǎn)生法律效力,而不能以此來對抗債權(quán)人。債權(quán)人仍可以向王某或趙某任何一方主張償還債務(wù),并不受離婚協(xié)議約定之約束。趙某在償還債務(wù)后,可依據(jù)離婚協(xié)議之約定向王某追償。由此可見,為規(guī)避債務(wù)假離婚,并不能達(dá)到逃避債務(wù)的目的。相反,王某還面臨著失去全部共同財產(chǎn)并最終獨自承擔(dān)全部債務(wù)的巨大風(fēng)險。
案例三:“假”離婚,真避罰
高某與李某于2010年登記結(jié)婚,雙方均系二婚。李某與前夫育有一子。2013年,高某與李某生下一女高甲。2015年10月,全面放開二孩的消息傳出后不久,李某再次懷孕。由于李某與高某所處的北京市當(dāng)時尚未頒布關(guān)于“二孩政策”的實施細(xì)則,高某所在的機關(guān)單位告知高某,此次生育不符合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不予開具準(zhǔn)生證,而且要給予高某處分并罰款。無奈之下,高某選擇與李某假離婚。兩人隨即簽訂了離婚協(xié)議,約定婚姻存續(xù)期間的全部財產(chǎn)歸李某所有,女兒高甲由高某撫養(yǎng)。
2016年3月24日,修改后的《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獲得通過。該條例明確指出,再婚夫妻婚前僅生育一個子女、婚后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雙方可以要求再生育一個子女。據(jù)此規(guī)定,高某與李某生育二孩有了政策的認(rèn)可和保護(hù)。于是,高某向李某提出復(fù)婚請求,但高某與李某“假”離婚后,李某又與其朋友吳某辦理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且兩人相處默契,十分投緣。于是,李某拒絕了高某的復(fù)婚要求。高某本來只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到處罰而“假”離婚,沒想到因此失去了家庭。
案例分析:假離婚并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夫妻雙方只要通過民政部門或訴訟等法定程序,完成了離婚登記手續(xù)或取得了離婚判決,婚姻關(guān)系即告解除。離婚時簽訂的離婚協(xié)議書或判決書中關(guān)于財產(chǎn)分割、子女撫養(yǎng)權(quán)的規(guī)定,以及撫養(yǎng)、贍養(yǎng)義務(wù)的劃分,對雙方當(dāng)事人均具有強制的法律效力,必須遵守。本案中,高某以“假”離婚為由,拒絕接受離婚帶來的人身、財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化,如無足夠的證據(jù)證明對方存在欺詐、脅迫行為,很難得到法律的認(rèn)可與保護(hù)。值得注意的是,在離婚和復(fù)婚之間“折騰”的時候,夫妻共同財產(chǎn)和婚前財產(chǎn)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如果夫妻雙方復(fù)婚后再想離婚,分割財產(chǎn)的比例只能按照最后一次婚姻狀況和最后一次婚姻持續(xù)時間計算。
(北京 李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