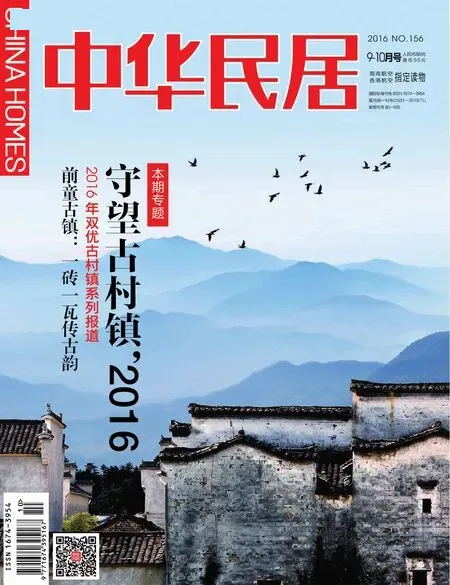印濫觴的印記
印濫觴的印記
《炙轂子》中這樣記錄:漢朝時,柏梁殿遭到火災,一位巫師建議,將一塊魚尾形狀的銅瓦放置層頂上,就可以防止雷電所引起的天火。它就是避雷針的雛形。
王朝走了,帶著它的主人一起,在公元20世紀初集體消失。木頭從此不被賞識,漸漸在燈火霓虹的鋼筋混凝土包圍中一蹶不振。歷經蠶食之后,祖先用智慧對決雷電的實證只能溯回到唐宋,當然遠遠達不到它原本的高度。
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裹挾著碧水白浪,拍擊出“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盛名,許久又許久。湖濱處,一座不那么起眼的磚塔矗立著,它本身并不高聳,三十九米的軀骸,一副八角七層的樣子,看上去卻格外挺拔。磚塔屬八角攢尖寶頂,中間有一柄黝黑的鐵杵直指天穹。四周的裝飾物皆依其所構,呈現出八面包夾的模樣。連接寶頂起固定作用的幾條鐵鏈則順著垂脊向翼角攀爬,逶迤垂下,最終以匍匐的姿勢向大地一體皈依。它就是慈氏塔,也是祖先智慧與雷霆怒火相互對峙的最早實證。正是得益于鐵杵和鐵鏈的組合,才使古塔能在無數次的雷火里幸運逃生。
對比之下,文字纏綿建筑的書籍中,木頭同雷電的博弈要顯得更加豐滿。早在木簡和紙張相互妥協的唐代,繁復的中國文字便第一次記載了避雷的智慧。
祖先的《炙轂子》中,有這樣的記錄:漢朝時,柏梁殿遭到火災,一位巫師建議,將一塊魚尾形狀的銅瓦放置層頂上,就可以防止雷電所引起的天火。屋頂上所設的魚尾開頭瓦飾,實際上兼作避雷之用,可認
為是避雷針的雛形。


雨果說:“西方的建筑是一部用石頭寫成的歷史。”而中華民族祖先的建筑話本,顯然是最先由木頭起了開場白。這段修行注定凄苦,需要在雷電的圍剿中不斷逃離,卻也驚艷了世界。從伊比利亞半島舶行赴華的安文思作了非常詳細的記載。他這樣寫道:“屋角以動物角上的角須形式直指天空,屋頂的形狀則類似被固定在矛樣物上的帳篷。金屬條從巨獸的舌頭探出,另一端插入地里。這樣,當閃電落在屋上或皇宮時,就被龍舌引向金屬條,并直奔地下而消散,因而不致傷害任何人。”
在眾神相擁的古代,樸素的科技只有圍著宗教“轉山”,才能在前人的將信將疑中生根,萌芽。于是,先民對雷電的規避便尾隨了那個時代的文明一起,被放牧在等待覺醒的河谷邊。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玄學是頗具代表性的,如五行、八卦。而在八卦的領域里,“震”卦為“雷”,結合方位之后,又有了“南離、北坎、東震、西兌”以及“南屬東雀、北屬玄武(龜蛇)、東屬青龍、西屬白虎”的考量。是故,在相師術士的“臆斷”下,古人一致地形成了“雷從龍”的思維。而此后,先民為了避免建筑物被雷擊,所必須構造安裝的避雷設施,都被稱之為“鎮龍”。
世事大略如此,一經點撥,便會陷在命數里“抱殘守缺”,經過了瞬間的激發后,又像機括般迅速彈射開來。于是,在古代建筑的表里不凡中,諸多被稱為“鎮龍”的避雷裝置在中國古建筑的身體上開始了生長、繁衍。
譬如,在我國一些古塔的尖端,常被涂抹上一層金屬質膜,接著,再使用易導電的材質同地下的塔心柱直通相連,而柱子的末端又與貯藏金屬的“龍窟”相連。這便形成了古代的一種“鎮龍”。
頗值一提的是,游歷東方的法蘭西高盧人用羽毛和羊皮卷對中國“鎮龍”也作了介紹。1688年,法國旅行家卡勃里歐別·戴馬甘蘭在《中國新事》中記載,中國屋脊的兩頭,
皆有一個仰起的龍首,張開的龍口吐出了曲折的金屬舌頭,遙遙伸向天空,舌根連結的一根細鐵絲,直通地下。這種奇妙的裝置,在發生雷電的時刻就大顯神通:若雷電擊中了屋宇,電流就會從龍舌沿眼睛行至地底,避免雷電擊毀建筑物。
除此之外,諸如直立在許多古塔與宮殿上的“鴟尾”,屋頂上設置成動物狀的瓦飾,還有高大殿宇里常立的所謂“雷公柱”之類的避雷柱,都與大地“暗通款曲”形成良好的導電通道,成為“鎮龍族”里的重要一員。
后來,先輩的智慧在遺產的約定俗成下不斷承襲,縱然時間徑自路過,古老的房子還是戴著“鎮龍”序列倔強地活著,同天穹那側的“霹靂”隔岸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