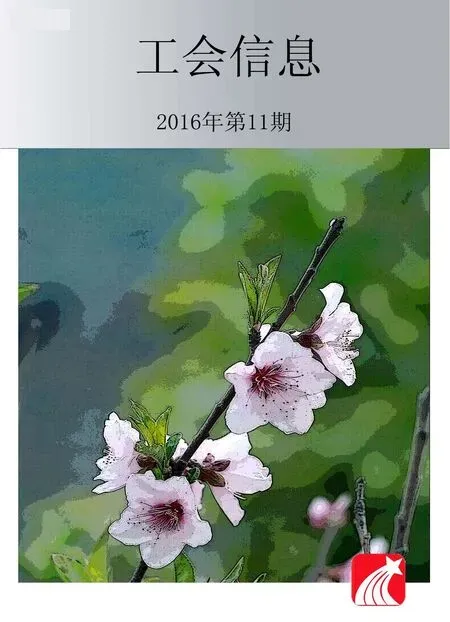郭沫若與佐藤富子的跨國情緣
文/木易 蘇學恕
郭沫若與佐藤富子的跨國情緣
文/木易 蘇學恕

在東京圣路加醫院相識
1916年的郭沫若,還是個血氣方剛的留日學生,對異性的神秘感,使他的頭腦里充滿了浪漫思想。6月,郭沫若的同學陳某進東京一高讀書后,得了肺病,在東京養病,先在杏云堂醫院,后轉到圣路加醫院。
當時,郭沫若在岡山六高還沒畢業,正放暑假,他專門坐車到東京來看望陳某。他見陳某總不見好,自己沒事,就每天不離醫院,對陳某精心照料。他的精神卻被負責這個病人的看護婦(護士)佐藤富子看在了眼里。她對這個青年的友愛精神也相當贊賞、支持,對陳某的病也深表同情。兩人在對陳某的共同照看中漸漸產生了友誼,有時經常一起躺在樓道中守著病房。
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臺藩士族(舊時武士的子孫),父親是個牧師。她的祖先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國有過來往。她的祖父和父親都到過中國。她的家中珍藏著中國古書。她本人也相當喜歡中國。她在仙臺美國人辦的教會學堂——女校畢業后,立志將一生獻給慈善事業。她不顧父母的反對,來到京橋區的圣路加病院當看護婦,想學習產科。
陳某在圣路加醫院總不見好,郭沫若勸他去養生院醫治。陳轉院的時候已不能起床,轉到養生院后不久就死了。
陳死后,有張x光片還放在圣路加,郭沫若處理后事時去圣路加索取。佐藤富子為他找了半天,但沒有找到。她流著淚,答應片子弄到后就給他寄去。
通過這次接觸,郭沫若對佐藤富子一往情深。他給她取了個心愛的名字“安娜”,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喚著。郭愛她的倩影、多情,兩人越來越眷戀,每周三四封信。后來,他在給田漢的信(1920.2.15)中坦白說:“壽昌兄!我實不瞞你說,我最初見了我安娜的時候,我覺得她眉目之間,有種不可思議的潔光——可是現在已經消失了——令我肅然生敬”。
過一禮拜,安娜把片子寄給了郭沫若,并寄來一封英文的長信來安慰郭沫若。
郭沫若在上面的那封信中還吐露了接到這封信后的內心感受,他說:“我當時真感受著一種Bitterish的Swee——tness(苦澀的甜蜜)呀!我以為上帝可憐我,見我死了一個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賢淑的膩友來,補我的缺陷。我倆從那時起,便時常通信,便相與認作兄妹”。
從8月到12月,他們保持了越來越密切的通信聯系。
當時郭沫若想,安娜既然矢志于獻身事業,只當個護士,未免不能做出更大的貢獻,便勸她辭去職務,進女醫學校學習。日本政府規定此種學校每年三月招考,安娜準備的時間不多了,12月放寒假時,郭沫若又去了東京一次,勸她辭去職務,到岡山和自己住在一起,既有生活保障,又能從事準備。郭沫若說:“我把我一人的官契(留學官費——引注)來作兩人使用”。
傾心相愛的歲月
1916年12月,郭沫若接安娜來岡山同居。他原以為兩人可以按婦女解放、平等的原則和平同居,自由相處,互相會尊重理智,謹慎從事,誰知:
“咳,壽昌兄:我終竟太把我柔弱的靈魂過于自信了!我們同居不久,我的靈魂竟一敗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壞了!”安娜知道郭是結了婚的人,而郭也因為結了婚而認為同居不會傷害安娜。
在此期間,郭沫若曾送安娜去東京市立女人醫學校讀書。不久,安娜就因懷孕輟學。
當時,留學生正鬧學潮,提倡凡與日本人結成夫婦的都要離婚,一時形成風氣。郭沫若經受住了考驗,他自己說沒有“殺妻休將”的本領和勇氣。那時候,他的學友郁達夫和成仿吾等還笑話過他對安娜的癡情呢!
1917年,安娜生了個男孩,取名和生。郭沫若的父母才稍微原諒他這種背倫的行為。而安娜的父母卻不同意這門婚事,宣布不承認這樣的一個女兒,以后“不許登門”。
兩人艱難地頂住了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在困苦中唱出了一曲愛的頌歌。
他在《我的作詩的經過》一文中承認:“把我從這瘋狂的一次救轉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因為在民國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戀愛發生,我的作詩的欲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愛情呼喚詩,詩促進愛情。
有了孩子后,兩人只靠郭沫若的一點官費生活,相當艱苦,況且又失去了家庭的支持,難度可想而知。
社會需要年輕的人闖最難的關,而年輕人恰好最缺乏后勁和條件。他們只能靠愛,同齡人的愛支撐著克服困難的意志。
1920年的時候,愛好戲劇的田漢還準備以郭沫若、安娜為模特兒寫戀愛劇。郭沫若給安娜看田漢的信,安娜笑個沒完。
田漢曾問郭沫若:“結婚之后,戀愛能保持么?”
郭說:“結婚是戀愛之喪禮。能永不結婚,常保Pure love(純情的愛)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結了婚彼此總不自由。……有了生育更不自由”。
他是結合自己的體會去說的實話。
1918年8月初,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大醫科。他帶著安娜和兒子和生從岡山遷到福岡,住在學校后面千代松原內一個倉庫樓上。這間屋子面積一丈見方,人立起來可以抵著頂板,房租一月6元。
有一次,成仿吾來后建議他們,和一位盲人陳老先生同住,只要安娜侍候一下他老人家,每月可收點錢,免交房租。安娜聽了,大喜過望得流淚。
“到處隨緣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
郭沫若唯一的一件嘩嘰學生裝放在破藤筐里被老鼠咬了幾個洞,他非常惋惜。安娜安慰他說:“沒有法子!待我今晚把它補補,想來還可以穿得,到明年做件新外套吧!”
安娜節衣縮食,包攬了全部家務,讓丈夫安心學習。不過,不久,陳老先生治完病回國了,這間新居的租期也滿了。
除夕夜,他們遷到了臨海一個只有六七戶人家的漁村——網屋町。
輾轉于中國與日本之間
轉眼已到1922年,郭沫若在九州帝大醫科畢業了,安娜希望他找個固定的職業,如行醫,而郭這時已和郁達夫、成仿吾等創立創造社,一心舍醫從文。就推說:“回國再說”。
安娜為生活的無著擔心,他們已有了三個孩子,再沒有固定的收入怎么行啊!她對郭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也不能不遷就些”。可是,見他整天呆了似地想著別的,安娜也就沒有強迫。
郭沫若把打算去上海辦同人雜志的消息告訴安娜后,安娜也只好先支持他。郭沫若曾說過這樣的話:“她的性格比我強,只要她起了決心,便沒有甚么游移,在我動搖著的時候,反是她來鼓勵著我執行了既定的計劃”。臨走,安娜給他煮了紅豆飯,燒了一條銅盆魚。她要送他到箱崎車站,他怕孩子醒了,沒讓她去。不過,他還是沒有馬上走。他看著柔弱的愛妻似乎又有些遲疑。最后,他想起了需要遷居的事兒。安娜安慰他說:“我在村上有很多熟人,你回國之后還有官費可領,你就甭擔心了。只希望你回國努力,有了固定職業時,我們便回去跟著你”。
1922年3月底,郭沫若回上海。1923年4月2日,安娜帶著三個孩子也來上海,和成仿吾等同住哈同路民厚南里泰東圖書局編輯所的舊樓里。不久,安娜就對上海失望了,覺得還不如回日本好,孩子們有成長、教育的問題,而在上海無固定收入,這些都談不上。她曾勸丈夫開業行醫,但沒有說明。她很要強,決心回國重學產科,然后來滬開業。為了減輕郭沫若的負擔,她把3個孩子也帶走了。
郭沫若覺得怪對不起她的,不得不由衷地敬佩她:“祝福你,圣母瑪麗亞!永遠感謝你喲,我最親愛的妻!”
不久,郭沫若也重返日本。兩人又過了一段安貧樂道的生活。1924 年11月16日,他又回到上海。
1927-1937 在日本渡過十載相濡與沫的歲月
1927年11月初,在血雨腥風的大革命后,他又從香港秘密回到上海,重和家人團聚。他們住在竇樂安路(今多倫路)一棟弄堂房里,周圍大多是日本僑民,便于隱藏。
郭沫若受到蔣介石的通緝后,中共安排他去日本。臨行前,他染上斑疹、傷寒,幾乎喪命,結果留下了耳聾的后遺癥。他住院期間,安娜也得了慢性腎炎,臉浮腫。她硬撐著身子每天去醫院看望他兩次,從早上陪到中午,又從午后陪到深夜,為他操盡了心。為了讓他更適于休養,她把家里打掃干凈,小心翼翼地把郭沫若接回來休養。憑著妻子的柔情和護士的細心,她挽救了他的生命。只有這時,他才深切感到:安娜是“我永遠的唯一的愛人!”
1928年2月1日,他翻譯的德國詩人歌德的詩劇《浮士德》第一部問世,安娜買來“壽司”請成仿吾和孩子們吃,郭沫若抽出一本《浮士德》,提起鋼筆在扉頁上寫了一行題詞:
“Anna:此書費了十年的光陰才譯成了,這是我們十年來生活的紀念。”
接著,他又在第二頁里用德語寫了一行字:“獻給我永遠的戀人安娜。”
1928年2月27日,他們回到日本千葉縣定居。這次,他是左派要人、政治犯。日本政府因涉嫌把他關了好幾天。安娜托人斡旋,才救了他。回到家,他無聲地把她摟到懷里。兩人久久依偎著,不說一句話。
為了安全,他們又一次搬家。剩下的就是他研究寫作,她打工掙錢。兩人過著貧賤夫妻的生活。
每到郭沫若有新書出版,舉家慶賀;每逢有憲兵前來搗亂,都被安娜機智地支走。
后來,他們又定居在千葉縣,房子有五六間,還有花園。
1932年,由郭沫若親自接生,安娜又生下一個兒子:志鴻。從此,夫妻情深,相依為命。到此為止,他們已經有了5個子女。
不過,情深歸情深,郭沫若浪漫難改。“九·一八”事變后,他當時已40多歲了,在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天津《大公報》駐東京女記者于立忱,兩人很快熱戀起來,兩人的共同語言似乎比郭和安娜之間多,風言風語很快也傳到了安娜耳朵里。
1937年底,郭沫若在有關人士的安排下準備回國擔當抗日重任,他把這個意思在回國前透露給安娜。安娜說:“走是可以的,不過,不能象從前那樣的胡鬧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擔心。只要你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我也只好忍受了”。
這話說得委婉而明確,郭沫若當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他對自己的生性浪漫慚愧不已。眼前這個女人是多么善良、體貼啊!他決心“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甘受戒僧的清規”。
臨走的那天晚上,郭沫若坐對妻子,夜深不寐。安娜也醒著,正坐燈下閱讀,沒有注意他的不安。他掀帳吻了吻她的額頭,她也沒有抬頭。由于他沒有告訴她具體的離日日期,她并沒有察覺。他穿著家常和服,飄著袖子,踏著木屐,悄然出門,一再回頭,心中無限眷戀。
分離之后的情變與分手
回國后的郭沫若直到1938年初才接到安娜的一封信,得知了她們的境況。日本人稱安娜是日本“野狗”,關壓、毒打她,逼她讓孩子入日本籍,受到安娜的拒絕。她聲明:“我是‘野狗’,我就熱愛中國!”
然而,不久,經過很短的頻繁接觸,郭沫若和于立忱(當時已逝)的妹妹于立群公開同居了。安娜又怎知道這些?郭沫若一直將這事瞞著安娜。
抗日戰爭勝利后,與郭沫若斷了音信的安娜從夏衍編的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上看到了郭沫若寫的回憶錄《洪波曲》(連載3個多月),她心中多么感謝丈夫在這里提供的信息(盡管在郭看來可能是一個疏忽)啊!她很快打點行裝,帶著長子和生、女兒淑子從日本坐船經臺灣來香港,在一個平常的時刻,突然走進了郭當時安置在林道街的家。
郭沫若愕然了,臉紅了,尷尬了。于立群也不知所措。善良的安娜滿腔怒火,她證實了自己的預料。她太了解郭沫若了!可她是背著家里的除名嫁給郭沫若的。她的心在顫抖。她目不轉睛地盯著郭沫若、于立群和同樣5個緊緊依偎在一起的孩子。她能說什么呢?
她在郭家理所當然地、怒目而視地住了幾天。接著,人們看到,馮乃超代表黨組織要安娜做出犧牲。安娜是基督徒,她學著耶酥的榜樣承擔了這種巨大的痛苦。經黨組織安排,她帶著孩子定居在新解放區的大連市。在那兒她一直住到老,有時也回日本。
1974年秋天,中國正進入“文革”的第八個年頭。剛從日本回國的安娜知道郭沫若身體不好,住院多時,特意帶女兒淑子去看望他。隨著年歲的增長,她不僅相信了基督的話,還洞察了兩性的秘密,原諒了郭沫若。
見到郭沫若的時候,安娜拿著許多在日本故居照的照片給郭沫若看,告訴他哪些地方還保持原樣,哪些地方改造了,他親自栽的樹怎樣了。郭沫若看得興致勃勃,一下子恍如還在30多年前。臨別,安娜和女兒淑子按照日本的方式,雙手放膝蓋上,向他行了告別禮。
郭沫若躺著,他無法還這最后一禮,只能用深情的目光送別。20年的貧賤夫妻啊!郭沫若的目光仿佛包含了他所要表示的那復雜的一切。
這是他們之間最后一次相見。
摘編自改革出版社出版《走向政壇的文化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