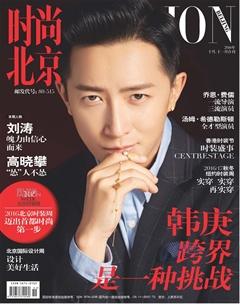北京最有“權”“錢”的胡同

說到北京,最著名的非“胡同”莫屬。北京的每一條胡同都有著自己悠久的身世和獨特的氣質,漫步其中,到處都是名勝古跡,細細品味又似北京的百科全書。它們歷經了歷史的變遷、時代的更替,已不僅僅是城市的脈絡,交通的衢道,更是北京百姓生活的場所,京城歷史文化發展演化的重要舞臺。這其中有兩條胡同,在眾多胡同中頗具特點,因為一條是北京最有“權”的胡同,一條是北京最有“錢”的胡同。
帽兒胡同 一上轎成君王人,再回頭是百年人
帽兒胡同位于北京市東城區西北部,東起南鑼鼓巷,西至地安門外大街。明代,這條胡同稱梓潼廟文昌宮胡同,因有文昌宮而得名。到了清代,因胡同內有制帽作坊而改稱帽兒胡同。帽兒胡同形成至少有七百多年的歷史,胡同名稱的歷史也有二三百年。帽兒胡同沒有平常老街舊巷的落寞,濃密的林蔭下,現代化的汽車與古老的三輪車交錯行駛在紅門灰墻間,隱隱中透著帽兒胡同昔日的非凡地位。
帽兒胡同35、37號院原為清宣統皇后婉容娘家——承恩公府,俗稱娘娘府。婉容的父親為內務府大臣郭布羅·榮源。1906年婉容就生在帽兒胡同榮源府,直至婉容大婚之前都住在這里,應該說她在這里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35號原為花園,是個三進院落,曾經院內山石疊翠,一進院子仿佛走進了蘇州的園林。婉容的閨房是37號院北房最西頭一間。此屋北墻上,裝有一面大鏡子,鏡面長1.76米,高1.25米。據傳說,北京老宅中,像這么大的上百年的鏡子,只有四處。其他三處是金魚胡同的葉赫勒那家、直隸總督榮祿和大太監李蓮英家。更能證明主人高貴身份的,是這處閨房外,木隔斷上的七面橢圓鏡子,以及中堂里一扇六米長、雕工精美、內容為百鳥朝鳳的落地罩。該房至今保留完好的龍鳳彩繪屋頂,更是皇親國戚的權威象征。
婉容的弟弟潤麟晚年回憶,姐姐婉容是個舊式女子,沒有受過現代教育,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老式教育,因而言行舉止都很傳統,具有一種中國傳統女性的道德修養。“早年父母為她請了家庭英語教師、鋼琴教師、音樂及美術教師。姐姐性格很溫和,長得也端莊美麗。她教我寫字、背唐詩宋詞,還教我彈鋼琴、畫畫,都很有耐心,就連我弄亂了她的閨房,她也不會發脾氣。”
婉容打敗了文繡,也打敗了自己的表妹,清末最美的格格——完顏·立童記(漢名:王敏彤),成為了大清皇后。前者為溥儀心儀皇后人選,但終和溥儀離婚;后者癡愛溥儀一生,為愛癡狂終生未嫁。1922年農歷三月,迎娶婉容的鳳輿出宮,前往帽兒胡同,揭開了末代皇帝溥儀大婚的盛大典禮的序幕。
郭布羅·榮源因為女兒成為皇后,獲封三等承恩公。位于帽兒胡同35號和37號的原本平常的貴族宅院,也一躍攀升為皇后府,接受了與尊貴皇戚地位匹配的大規模改建。
自從結婚當了末代皇后,離開帽兒胡同這所娘娘府,婉容就再也沒有回來過。1931年,日本間諜川島芳子將婉容誘至滿州,婉容與溥儀成為日本傀儡。身在長春的婉容受日本方面控制,生活沒有自由,與溥儀也貌合神離,最終分道揚鏢。
1946年婉容死于吉林延吉的監獄里,時年40歲。隨著衰落的婉容家族在無限的失落里四散飄零,這個遠離了當初的主人視線的院落,也從此走上了破落之路。
除婉容之外,這條胡同還住過很多名人,比如明代將領洪承疇、大學士文煜、北洋軍閥馮國璋、當代著名學者朱家等。
寶鈔胡同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寶鈔胡同位于北京市東城區西北部,北起東絳胡同,南止鼓樓東大街。根據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記載,該胡同稱倒鈔胡同。相傳元時倒鈔司設于胡同南口。元朝立有“倒鈔法”,實行紙幣,倒鈔司便是負責全國新舊紙幣兌換的機關。當時,全國的錢都匯集到這里,說最有錢也不過分。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堪輿部門在制京城全圖時,“倒鈔”訛為“寶鈔”,于是便成了現在的寶鈔胡同。
寶鈔胡同西側甲19號有一座那王府。按照《王府生活實錄》說法,“那王府,是外蒙古親王在北京僅有的一處王府。”那王府坐北朝南,南北貫通國興胡同和國祥胡同。那王府歷經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
那王府原來大致的建筑格局是,府門(宮門)三間面南,府門東、西兩側各有角門一座。府門外照例對面是一座影壁,兩側設置石獅、燈柱、拴馬樁和轄禾木。府門內有一座木質影壁,銀安殿建筑宏偉、結構緊湊,殿宇均按皇宮形式建筑,只是規模小一些。那王府與京城內的滿洲王府、內蒙古王府相比,蒙古習俗明顯。每年臘月二十三,都在府中佛堂院內架設一座蒙古包,中間生一個大火爐,府內的喇嘛和其他人員在親王的率領下,圍著火爐高聲念經。如今,那王府已大部分改建,國祥胡同甲2號也曾是王府的一部分,還保留著當年的風貌。
《順天府志》載:超勇親王府在寶鈔胡同,稱那王府。超勇親王府這個稱法源于第一代主人策凌。策凌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策凌隨祖母投奔清廷,留居京師。策凌英勇善戰,由貝子品級晉郡王,直至晉扎薩克親王。王府亦稱“超勇親王府”。那彥圖為策凌第七世孫。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那彥圖襲第七代喀爾喀親王,又稱“那王”,王府遂有“那王府”的俗稱。
民國后,由于那彥圖的特殊歷史地位和聲望,無論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做總統,都給其以禮遇。
那彥圖雖為蒙古人,但對中原廚藝青睞有加。他從老丈人奕那兒學來了做“香白酒”的要領,在那王府如法炮制,長年飲用。那彥圖喜歡吃“衛水銀魚”。衛水,指今天的天津水域。這里盛產一種小銀魚,是魚中的貢品。清人曾有“草橋荸薺大于杯,衛水銀魚白似玉”的美稱。
那王府的主要經濟來源,原本依靠喀爾喀蒙古賽音諾顏部落的供給。外蒙古獨立后,這個來源漸漸枯竭。那彥圖長子祺誠武的仆人曹寬用府契做抵押,向西什庫天主教堂借款兩萬元,到期無力還款,又轉向西什庫教堂神甫包世杰借款七萬元。1931年,祺誠武無法償還債務,那王府被抵押。那彥圖一家被迫搬到豆腐池胡同4號租房居住。20世紀40年代,教堂將那王府轉給金城銀行。解放后成為北京市人民銀行、鼓樓中學、第七幼兒園所在地。那彥圖于1938年逝世,葬于安定門外六公主墳西側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