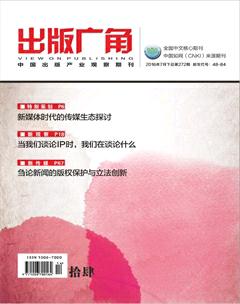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把脈
【摘要】《姐妹鏡像——21世紀(jì)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是張莉教授的重要學(xué)術(shù)論著,是彰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價值取向的學(xué)術(shù)出版物。從某種角度來說,它實現(xiàn)了對新世紀(jì)女性寫作態(tài)勢與轉(zhuǎn)型特點的把脈,也使其成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研究的重要文獻(xiàn)。
【關(guān)鍵詞】《姐妹鏡像——21世紀(jì)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女性寫作;轉(zhuǎn)型;學(xué)術(shù)出版
【作者單位】陳壽琴,重慶師范大學(xué)涉外商貿(mào)學(xué)院。
2014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張莉的《姐妹鏡像——21世紀(jì)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以下簡稱《姐妹鏡像》)。該書對女性寫作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進(jìn)行了及時的關(guān)注和研究,力圖把握21世紀(jì)第1個10年的女性寫作態(tài)勢和轉(zhuǎn)型特點。《姐妹鏡像》的出版對出版界和學(xué)術(shù)界(尤其是中國現(xiàn)代女性文學(xué)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也是研究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出版及社會文化的寶貴資料。因此,本文擬就出版價值與研究價值對《姐妹鏡像》的重要內(nèi)容進(jìn)行梳理,從而探究《姐妹鏡像》對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出版的發(fā)展走向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價值。
一
《姐妹鏡像》的出版價值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彰顯了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的學(xué)術(shù)價值取向和定位。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6月,是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創(chuàng)辦并主管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主要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和全國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界、文化界學(xué)者的中外文優(yōu)秀成果,包括專著、資料、教科書、教參書、工具書和普及性讀物;還出版國外重要人文社會科學(xué)著作的中譯本[1]。這是該出版社的定位。該定位中有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詞:“優(yōu)秀成果”。由此可以判斷,注重出版品質(zhì)和學(xué)術(shù)涵養(yǎng)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在出版《姐妹鏡像》的時候,就已經(jīng)將其列為社會科學(xué)界、文化界學(xué)者的“優(yōu)秀成果”。
近30來年,許多學(xué)者和學(xué)人對中國女性寫作進(jìn)行了多層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以來,女性寫作以其鮮明的性別立場和性別視角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舞臺上成績斐然。相應(yīng)的,對女性寫作的研究也成為近30來年文學(xué)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熱點與生長點。僅從21世紀(jì)出版的對中國女性寫作的研究著作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叢書,如喬以鋼教授主編的“性別視角下的中國文學(xué)與文化叢書”、劉思謙教授主編的“娜拉言說書系”等,這兩大叢書匯集了很多耕耘在此研究領(lǐng)域的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成果。而在“第五代學(xué)人叢書”“同濟(jì)·漢語敘事文學(xué)叢書”等叢書中也包括了對女性寫作進(jìn)行研究的學(xué)術(shù)專著。此外,還有許多學(xué)者和學(xué)人專注于女性寫作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論著,這些論著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很可觀。綜上所述,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姐妹鏡像》的價值定位在于,出版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和文化學(xué)術(shù)熱點相關(guān)的論著,從而實現(xiàn)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及研究把脈。
其次,體現(xiàn)了重要的史料與文獻(xiàn)價值。張莉教授以嚴(yán)謹(jǐn)認(rèn)真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進(jìn)行21世紀(jì)女性寫作的研究。她主要從文化這個特定的角度去描述和勾勒21世紀(jì)10年代女性創(chuàng)作的輪廓。該書第一章“這個時代的不合時宜者”注重結(jié)合文本進(jìn)行具有地域色彩的都市文化分析。她認(rèn)為,都市女性的行為、追求和精神品質(zhì)都是都市的某種隱喻。該書對都市女性的分析,觸及了相應(yīng)的都市文化或都市文化精神。第五章“仁義敘述的難度與難局”是從傳統(tǒng)美德(文化)、現(xiàn)代價值與民族國家話語角度來對鐵凝作品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境遇。第六章“異鄉(xiāng)人”側(cè)重從性別文化來解析魏微作品的愛情、性、身體等內(nèi)涵。第六章“取景器的內(nèi)與外”從性別文化的分析視角、女性與女性的關(guān)系來解構(gòu)或重建“女性烏托邦”。第七章“起義的靈魂”論述的是道德文化與身體欲望之間的繁復(fù)文化意蘊。第九章“先鋒氣質(zhì)與詩意生活”是從21世紀(jì)大眾文化的消費化與文學(xué)性之間的消長來闡釋廖一梅的戲劇,并分析文學(xué)如何在“媚俗、偽善與平庸”的時代文化環(huán)境中保持個人性、文學(xué)性和詩意性。第十章“資本·勞動·女性”則從不可見的女性——女工、農(nóng)村女性、打工妹等底層勞動婦女的文化處境來進(jìn)行解析。整體來看,該書緊扣了21世紀(jì)文化的時代特征去進(jìn)行女性文學(xué)和社會文化的分析,不僅實現(xiàn)了該書在時代文化語境中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把脈的預(yù)設(shè),也實現(xiàn)了其社會文化價值。
如果從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歷史進(jìn)程來看,從20世紀(jì)10年代末開始,時至今日,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已經(jīng)走過將近百年的歷史了。對于中國現(xiàn)代女性創(chuàng)作的評論和研究也相伴相生。20世紀(jì)上半葉的女性文學(xué)批評,主要注重印象式的批評,也注重文化特征的認(rèn)定;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中國女性文學(xué)受西方女性主義文學(xué)批評理論的影響很大,現(xiàn)代女性文學(xué)的研究者人才輩出,研究成果豐碩;21世紀(jì)的女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在繼續(xù)深入發(fā)展和不斷拓展。而《姐妹鏡像》就是21世紀(jì)女性寫作研究的拓展與轉(zhuǎn)型。它是一部研究對象很“新”的,對女性寫作進(jìn)行研究的專著。在文體的考量上,該書注重對不同體裁進(jìn)行全面關(guān)照,重點雖然是小說,但也關(guān)注了詩歌、散文和戲劇。文學(xué)體裁的全面覆蓋,體現(xiàn)了“文學(xué)史”的架構(gòu)意識。事實上,該書確實不失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的“斷代史”。該書在作家作品研究里,對女性文學(xué)的分析與闡釋是符合21世紀(jì)第1個10年的宏觀把握的,是以發(fā)展的眼光打量這些文學(xué)景觀的。該書對21世紀(jì)女性寫作的成就進(jìn)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充分體現(xiàn)其“史學(xué)”價值和文獻(xiàn)價值。這也許是出版者出版《姐妹鏡像》的目的所在。
再次,提倡了敢于挑戰(zhàn)、勇于挑戰(zhàn)的學(xué)術(shù)精神。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之所以出版《姐妹鏡像》,很可能是要提倡一種勇于挑戰(zhàn)的學(xué)術(shù)精神。《姐妹鏡像》的研究對象特別“新”,即剛過去不久或正在進(jìn)行的女性寫作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該書的研究對象最大特點是當(dāng)下性、無定論,因此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作者迎接挑戰(zhàn)的能力和勇氣都值得學(xué)術(shù)界同仁學(xué)習(xí)。
《姐妹鏡像》的挑戰(zhàn)首先表現(xiàn)在對新近的女性寫作進(jìn)行全面或者宏觀的把握。首先,如果作者沒有對21世紀(jì)10年代的女性寫作文本進(jìn)行大量閱讀,沒有敏銳的分析能力和厚實的學(xué)術(shù)素養(yǎng),要梳理這十年間的女性寫作變化軌跡是很難的。況且,分析這期間發(fā)生的重要文學(xué)現(xiàn)象也并非易事,更不要說去界定女性寫作的成就與重要轉(zhuǎn)型。可以說,作者在為21世紀(jì)最初10年的女性寫作的把脈中,成功地梳理了這個時期女性寫作的重要發(fā)展流脈。其次,該書的挑戰(zhàn)還表現(xiàn)在研究個案的選擇上。新媒體時代的女性寫作如此繁復(fù),加之很多作家作品都沒有定論或者還沒有進(jìn)入主流研究者的研究視野,我們應(yīng)該以什么關(guān)注點去選擇作家作品?個案的選擇,需要作者開闊視野、生命感受和藝術(shù)感悟的完美結(jié)合。而對于正在進(jìn)行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言,由于無同類論著可借鑒,編選對象時空距離太近,時代的狀況又很復(fù)雜,現(xiàn)實寫作更是變動不居,因此存在很大的挑戰(zhàn)。既然作者已經(jīng)為這十年來的文學(xué)寫作確立了“社會性別意識”的關(guān)鍵詞,那么這就是她選擇個案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也是服務(wù)于該書的核心觀點。該書選擇的鐵凝、王安憶、林白、遲子建、嚴(yán)歌苓、盛可以、魏微、魯敏、周曉楓、廖一梅、鄭小瓊等女性作家至少代表了作者的價值立場和審美考量,代表了作者對新世紀(jì)以來女性寫作發(fā)展趨勢的判斷。至于這些女性作家是否能代表21世紀(jì)第1個10年的成就,還未可知。畢竟,該書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過近,有些作家的作品還有待時間考驗和研究界的發(fā)掘。
當(dāng)下,出版界比較青睞那些賣點很好的通俗讀物和實用性強的功利性讀物,而對學(xué)術(shù)著作則不是很熱心,更談不上學(xué)術(shù)精神的倡導(dǎo)了。《姐妹鏡像》則體現(xiàn)了出版社對推動人文社科學(xué)術(shù)研究的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
二
《姐妹鏡像》既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的出版物,也是中國女性寫作研究的重要文獻(xiàn)。該書的出版,使其學(xué)術(shù)研究價值同樣引人關(guān)注。
第一,該書宏觀地把握了21世紀(jì)女性寫作“向外轉(zhuǎn)”的轉(zhuǎn)型趨勢。作者提出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向外轉(zhuǎn)”之說,進(jìn)而論述女性寫作與社會現(xiàn)實的緊密結(jié)合現(xiàn)象。如果從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內(nèi)容和表現(xiàn)主體來看,新世紀(jì)女性寫作一是對時代之維度下無法回避的大都市進(jìn)行了描寫,和對都市文化遮蔽下民族文化主體性進(jìn)行重建與思考。現(xiàn)代大都市是21世紀(jì)中國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場域,也是大眾傳媒的聚焦點,足以代表新世紀(jì)文化觀念和價值的主體流向。二是直面人的各種欲望與社會法則。這個話題涉及人與社會的復(fù)雜關(guān)系,所以女性寫作能直視人(尤其是女人)自身的欲望與價值追求,以及人與社會難分難解的關(guān)系。這無疑體現(xiàn)了女性寫作者的主體意識和對人生、社會的擔(dān)當(dāng)。三是對社會底層勞動女性的悲憫性關(guān)注和深切體認(rèn)。這種題材的女性書寫走出了個人化寫作的幽閉,改變了知識精英寫作的高姿態(tài),走近被大眾文化忽視的“小眾”——女性弱勢群體。她們處于社會底層,在喧囂的大眾傳媒時代,她們的聲音是微弱的或“啞聲”的。在大眾媒體的屏幕上,她們只是作為偶爾閃過的背景,或者是當(dāng)代“新聞”中的“祥林嫂”,很快就被媒體和所謂的大眾遺忘。也許,正如《姐妹鏡像》所說,關(guān)注底層女性的女性寫作開始真切地“復(fù)活了這個時代獨有的疼痛、鮮血和眼淚”,而不是被報道的蒼白而失真的面貌,或者被剪輯和處理過的造作[2]。因此,《姐妹鏡像》認(rèn)為,新世紀(jì)女性寫作“在社會性別自覺與文學(xué)自覺的雙重意義上打開了一個新的格局——深具社會性別意識的女性寫作姿態(tài)和書寫樣式”[2]。
如果從中國現(xiàn)代女性敘事的范式來看,女性寫作具有注重自我世界的營構(gòu),注重細(xì)節(jié)描寫,敘述破碎而含混等范式。而21世紀(jì)女性寫作的“向外轉(zhuǎn)”,就意味著對這些“范式”的打破。該書專辟了第二章“非虛構(gòu)女性寫作:一種新的女性敘事范式的生成”來論述這個話題。論及新世紀(jì)女性寫作范式的突圍,該書提出首先在文本的體式上轉(zhuǎn)向“非虛構(gòu)”寫作。“非虛構(gòu)”寫作使女性寫作得以重返當(dāng)代社會的公共言說空間,于是,女性寫作由較為封閉的自我世界走向“我眼中”的世界,表現(xiàn)的視域和空間開闊了;“我”不是自言自說了,“我”成為現(xiàn)實世界的一分子,個人記憶與中國現(xiàn)實重合。“記憶和想象是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和敘事的推動力。” [3]由此,出現(xiàn)了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潛在變化,能“從復(fù)雜的社會環(huán)境生活中書寫愛情、身體、性以及婚姻”“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書寫個人史”和“在浮世中刻畫如浮萍一樣的個人命運”[2]。其次,在細(xì)節(jié)的處理上,注重有意味的細(xì)節(jié)。有意味的細(xì)節(jié)是那些既承載著個人體驗和個人感受,又包含這個時代集體經(jīng)驗的細(xì)節(jié)。只有這樣的細(xì)節(jié),才能觸動人的內(nèi)心,因為這些細(xì)節(jié)是性別立場與社會群體的相互指認(rèn)。這種個人與集體(公共)意識的膠合使女性敘事者體現(xiàn)了一種社會責(zé)任感。《姐妹鏡像》在把握新世紀(jì)女性寫作“常”與“變”的動向上,還是比較準(zhǔn)確的。新世紀(jì)女性寫作與“五四”女性寫作的區(qū)別在于:“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轉(zhuǎn)型深刻,表明她們?yōu)閭€人寫作與社會現(xiàn)實結(jié)合所做的努力,呈現(xiàn)了新的精神氣質(zhì),即為不可見的族群言說的勇氣,對邊緣群體的眷顧和對邊緣立場的堅守。” [2]這個論斷是比較中肯的,畢竟“五四”女性寫作大多屬于知識分子精英寫作。
第二,值得參照的學(xué)術(shù)著作言說方式的“變化”。《姐妹鏡像》在言說方式上,實踐了一種學(xué)術(shù)“新”風(fēng)范:少了許多艱澀的專業(yè)術(shù)語及解析,比較貼近文本,很注重對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解讀與闡釋。該書各個小節(jié)的標(biāo)題都使用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文題;在進(jìn)行新世紀(jì)女性寫作和社會文化的綜論時,該書也是結(jié)合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論述和闡釋的。這樣,似乎感覺該書缺少了“學(xué)術(shù)味”,但是卻能給讀者一種親近感。因此,讀者不會覺得很艱澀難讀,很快能隨著作者的筆觸進(jìn)入21世紀(jì)女性文學(xué)文本的世界,及時了解新世紀(jì)女性寫作的特點與內(nèi)涵。
就研究方法來看,該書沒有特別標(biāo)明使用哪一種文學(xué)批評理論或者批評方法,但是我們能清晰感受到作者對各種文學(xué)批評方法的潛在使用。貫穿全書最明顯的研究方法應(yīng)該是文本細(xì)讀法。這種方法很務(wù)實,從文本中來,到文本中,不會給人感覺很“飄”,也不會給人感覺很“難”。此外,比較明顯的就是比較法,既有歷史性的作家作品比較,又有共時性的作家作品比較,這樣就使該書具有了研究的縱深度,彌補了學(xué)術(shù)味單薄可能帶來的淺易化。
筆者認(rèn)為,這種新的言說方式與該書一再強調(diào)的21世紀(jì)女性寫作的轉(zhuǎn)型有關(guān)。女性的學(xué)術(shù)著作從學(xué)院派的學(xué)術(shù)寫作方式向民間大眾的寫作方式靠攏,由只注重個人學(xué)術(shù)品位和專業(yè)性角度向大眾能讀的角度靠攏。這可能是學(xué)術(shù)寫作的新走向,也是學(xué)術(shù)出版業(yè)為適應(yīng)大眾的接受度而向?qū)W術(shù)著作發(fā)出的一種信號。
第三,21世紀(jì)女性寫作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和文獻(xiàn)。如果從女性寫作和研究史來看的話,《姐妹鏡像》是一部研究對象很新的、對中國女性寫作進(jìn)行比較及時研究的論著。它本身實現(xiàn)了女性寫作的自我證實和她們在文化解碼的“鏡像”中進(jìn)行的自我觀照,也構(gòu)成了21世紀(jì)女性寫作圖景中的組成部分,同時還對同是女性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了姐妹情誼似的真摯解讀。該書對21世紀(jì)女性寫作和性別文化的研究,以及對新世紀(jì)第1個10年的女性作家作品的評價具有比較重要的史料及資料價值,其本身也是非文學(xué)性女性寫作的研究對象,因此它本身也具有研究價值。
毋庸置疑,《姐妹鏡像》是張莉教授的重要學(xué)術(shù)論著,是彰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價值取向的學(xué)術(shù)出版物。從某種角度來說,《姐妹鏡像》實現(xiàn)了對新世紀(jì)女性寫作態(tài)勢與轉(zhuǎn)型特點的把脈,也使其成為21世紀(jì)女性寫作研究的重要文獻(xiàn)。
[1]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DB/OL].http://www.csspw.com.cn/Item/48741.aspx.
[2]張莉.姐妹鏡像——21世紀(jì)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4.
[3]趙倩.基于“記憶”主題的小說敘事研究——評勒克萊齊奧《尋金者》[J].出版廣角(下),2016(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