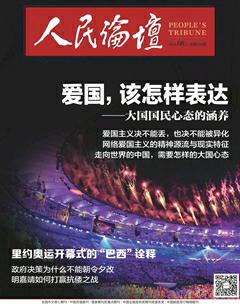探尋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6.9%,降至25年來的最低點,在創造了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之后,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增速整體放緩的新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APEC峰會上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將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將不斷優化升級,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出現更多新的特點、新的規律,出現持續性的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那么,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較之前發生了哪些變化?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究竟在哪里?弄清這些問題,是更好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的重要前提。人民智庫成立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研究課題組,并圍繞此開展了相關的實證分析,現將主要研究過程及研究發現呈現如下。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現狀與挑戰
2011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均值為8.23%,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持續走弱;煤炭、鋼鐵等傳統高能耗產業和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相繼出現產能過剩;世界經濟萎靡帶來進出口總額不斷下降,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經濟增速的換擋調速期、經濟結構的調整陣痛期和對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疊加”推動著傳統經濟動能的轉型調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成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剔除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長率之后,由技術進步和規模效益等因素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通常,我們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國家或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此前很多研究的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間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人力資本結構改善緩慢、就業增長顯著降低、投資率過高且投資結構失衡以及產能過剩帶來資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受益于勞動力和資本的大規模投入,那么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必須依靠結構優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也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一個實證探索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內在邏輯體現在通過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從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態前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動情況,探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人民智庫課題組選取2000—2012年中國省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進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數分解法(數據包絡分析-馬奎斯特指數),從技術效率改善和技術進步兩個角度測度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情況;隨后,課題組在構建經濟增長模型,經過F檢驗、Hausman檢驗(豪斯曼檢驗)等對模型具體形式與回歸方法進行確定基礎上,通過回歸分析進一步實證探索了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城鎮化水平、政府規模、政府干預程度、投資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并分別測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兩個階段上述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情況。考慮到數據統計口徑、變量數值測算等存在一定差異性,課題組更著重于分析各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以及影響程度的變動情況,在此基礎上找出“新動能”,并探討如何更好發揮“新動能”對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以回歸模型為遵循,課題組選取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產出變量,將資本存量(K)、勞動力投入(L)作為投入變量,以2000年作為基期調整相應指標數據,對2000—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動情況進行DEA-Malmquist指數測算與分解,其中,資本存量的測算采用了永續盤存法。同時,選取適齡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測量人力資本投入(HUM);以公路、鐵路、水路建設密度測量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衡量城鎮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體現政府規模(GOV);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比體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SOE);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建筑安裝投資占比情況考察投資結構(CON);以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TER),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相關經濟指標均調整為按可比價格計算。樣本數據統計性描述見表1,主要回歸結果見表2、表3。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
以創新為驅動,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核心是實現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從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兩個路徑同時發力,通過對2000—201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DEA-Malmquist指數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間之初,技術進步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技術效率損失也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技術效率的提升并沒有帶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高。同時,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影響程度也有所差異。測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對于技術進步的吸收要優于其他地區,而技術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時技術效率偏低和技術進步不足也是東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優化投資結構,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途徑。投資驅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而投資結構的優化將成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一直以來,“三駕馬車”帶動著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尤其是2008年之后,4萬億投資為危機后中國經濟軟著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測算結果表明,投資率過高和投資結構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增速緩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間,建筑安裝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其實,這一結果并不難理解,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府績效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擴大投資規模帶動GDP增長的激勵機制下,盲目招商引資,盲目上項目,缺乏深入的市場預測和評估監管,進而造成當前投資率偏高而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在當前仍舊大量存在。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帶來投資效率的降低,而投資效率的降低又勢必影響經濟增長質量。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據測算,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任務,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部分行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呈現典型的結構性過剩,這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調整結構繼而實現增長;另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長中出現很多新的業態模式和新的市場需求,比如根據《人民論壇》關于“當前中國發展動力及其構成”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互聯網+”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得到了公眾的廣泛認可。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2014年,我國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創造了56%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貢獻了74%的新增就業崗位。雖然我們在實證研究中選擇了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來代表城鎮化水平,但測算結果仍然驗證了城鎮化建設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從內在機制來看,城鎮化推動經濟增長,不僅體現在城市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效益,還體現在產業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之間,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通過再配置而提高了經濟增長績效。此外,能夠推定,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還將吸引更為大量的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城市公共事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從而通過優化投資結構更好帶動經濟發展,催生經濟增長新動能。
以全要素生產率引領新常態的對策建議
事實上,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周期上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逐步呈現出新的歷史特點。而通過對2008—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及分解,我們可以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重點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進一步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積極作用。
鼓勵自主創新,構建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落實創新驅動戰略,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科研機構及產業園區之間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實現高效率、高層次的協同合作,構建更為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從而提高創新驅動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實創新驅動并不是空泛的口號,也不是蜻蜓點水的小打小鬧,而是要在發揮市場機制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為市場提供更高端、更環保、更具價值的創新成果,為經濟增長培育核心動力。
完善市場機制,促進投資主體和投資渠道多元化。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并非要否定投資的重要性,投資并不是“洪水猛獸”。事實上,從當前的改革需要來看,創新能力的提高、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都需要投資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資結構。新常態下,進一步調整投資結構,要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疏通產能過剩行業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資監管相關政策法規,降低新興行業準入門檻,提高投資靈活性;通過多元化發展實現投資主體、投資結構、投資方式等的優化。
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健康發展。智能制造、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將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要重視核心技術的應用,創新能力和實力的提高,從而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同時,要高度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城市經濟逐漸轉型的過程中,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高端生產型服務業的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也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一環。此外,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要關注經濟發展中新業態、新模式的變動,提高相關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資本結構,釋放更多的人才紅利。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不能滿足當前經濟多元化發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資本發揮更大作用的制約因素,這為此前的很多實證研究所證實。當前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行業和新領域,都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提供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要成為教育改革的目標之一。因此,通過改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人力資本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將成為提升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重要途徑。從當前來看,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的專業技術性人才,是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切實可行的重要途徑。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更好發揮城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人口流動是“用腳投票”的過程,城鎮化建設既不能走傳統土地城鎮化道路,也不能簡單地走人口城鎮化的道路,而是應該走尊重人們意愿、響應人們訴求的城鎮化道路。對于城鎮化的理解,也不能簡單局限于城鎮地區,而是應該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視域來加以審視。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提高相關政策在基層辦事機構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為人口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提供現實條件,從而實現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并充分發揮城鎮經濟尤其是小城鎮經濟(包括美麗鄉村經濟)在新常態下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于曉萍(見習);統稿:人民智庫高級研究員 欒大鵬)
(本文為人民智庫獨家研究成果,未經授權,謝絕轉載)
責編/楊鵬峰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