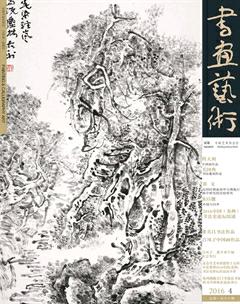國騰飛書法作品
國騰飛
中國書法是一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藝術。雖然經歷了幾千年的滄桑,還是會有大量的經典書作流傳下來,并以不同的風貌反映出時代的精神,表現出永葆青春的強大生命力。這些書作為什么會有如此魅力?南朝書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中說:“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可見自古以來的書法名作,必定是“形神兼備”之作,既展現出優美的外在形式,又洋溢著濃郁的文人氣息,故而流芳百世。
趙孟煩言:“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此語道出了書法最最基本的理法,也就是用筆與結字。用筆上,在這個書寫漢字已經從毛筆轉換成硬筆的時代,人們都習慣了直來直去的書寫方式。結字上,我們每天見到的漢字絕大多數以印刷體為主,人們也習慣了對印刷體的審美。在這樣的現實下,對于書法最基本的筆法、字法的傳承面臨著危機,所以解決這個基礎問題成為了整個社會在書法上的主要關注點。例如書法作品能否在一些書法大賽中勝出,大致上就是看作者能否掌握基本的傳統筆法和能否積累一些古人的結字方法來決定的。然而,書法是不是還有一些更高層次的東西去追求?當我們的基礎技法問題已經解決之后,應該如何建立個人審美的更高標準?我認為無疑是要從書法的文化內涵上來尋找突破口,也就是追求傳統書法當中的文人氣息。
傅山曾說:“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傅山強調為人的剛正不阿是書法立品的第一要務,以顏魯公為例,也是樹立了一個立品的最高標桿。清代朱和羹言:“學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并不朽于千古。”顯然,自古以來,“清剛雅正”之氣是為人、作書、立品的高追求,柳公權言:“心正則筆正”,當人的內心充滿正氣時,筆下的豐富變化不論是奇側、夸張、變形等等,都是以一個“正”字為中心;相反若是心術不正者,不論其筆下如何的變化,最終在字里行間當中體現出來的只能是“扭扭捏捏”的小人之氣。故東坡先生有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也就是說,君子與小人的心境,在其書法上是掩蓋不住的。姜白石對書畫當中體現出來的為人與立品做出了總結:“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后煙云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摹妙跡,到頭只與圬墁之工爭巧拙于毫厘也。”故為人立品、胸有正氣是第一位,也是書畫家在研習過程當中由技上升為道的基石,而通過讀書追求文化涵養便是相對更高的要求。東坡先生有詩云:“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中國書法在技法過硬的基礎上,自古就追求文化修養,這樣的書作往往更加得到人們的珍視。李瑞清在《玉梅花盒·書斷》中言:“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故古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矣。”他強調了“手技”是“不足貴”的,必須在技的基礎上有更高的追求,這就是如何做到“下筆自雅”的問題,“雅”的東西未必能夠力學而成,它需要長時間的積淀,更加需要我們對好的作品和好的書籍多讀、多見、多識,在豐富的人生歷練與文化視野中方能體現出較高層次的氣息,也就是文人氣息。所以,在書畫領域來說,讀書一定要活學活用而不能死讀書,要通過讀書提高見識、攝取經驗,通過積極參與實踐,形成自己獨有的生活體驗,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感知能力、歷史觀念、審美觀念,認識的層次不斷提高,筆下自然會逐漸具備中國文人的清雅剛正之氣。
縱觀當代全國書法展的作品,大都具備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對古人經典作品中基本的筆法、字法、章法技巧能夠熟練的模仿;二是對于作品外在的構成形式具備一定的技巧。這兩個特征都以技術性為重,對一般學書者而言雖不能一蹴而就,但經過名師指導并進行一段時間訓練后也不難掌握。然而書法創作應當有更高層次的要求,就是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性格上的、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文人寫意精神的體現。所以,我認為當代書法作品的品評,也應當注重文人氣息的評判,它從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取代當前全國展對書寫作者的“文化考察”,這種關乎作者文化水準的考察,應當放在作品本身,而非是另設考試,因為考試是可以“應對”的,而直接對書作的文人氣進行品評是無法摻雜手腳的,胸無點墨的書匠也自然是無法偽裝自己的。
當今社會是一個個性張揚的社會,表現在書法上,就是變形和恣意越來越多,有的人過分地追求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內在意蘊和氣息,這就是我們和古人的差距。希望我們能夠認識到這個差距,虛心向古人學習,學書從修身開始,讀書萬卷,腹有詩書氣自華,使我們的書法作品在把握揮運之理的同時,洋溢出雅逸的文人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