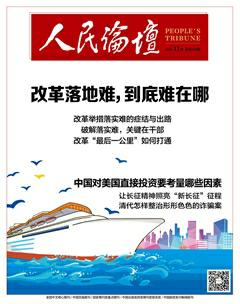如何用刑法修復環境治理中的漏洞
李政寧
【摘要】中國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和司法與同法系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是環境犯罪治理成效不佳的主因之一。文章在借鑒國家環境立法經驗后,結合我國國情提取我國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的修復路徑,以輔助強化環境犯罪刑法的懲處成效。
【關鍵詞】環境犯罪刑法 治理漏洞 修復路徑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新時期我國環境犯罪刑法治理中的漏洞
規制全面性不足,立法科學度不夠。我國刑法典在環境犯罪罪名設置方面的過窄,表現為很多應該被列為規范內的行為如濕地、草原、噪音等容易被破壞和被污染的環境要素,并沒有被列入刑法規范中,如此就導致環境犯罪治理時此部分存在立法空白,使實際環境保護中,與人類生存休戚相關的環境,無法依托刑法得到保護。雖然目前現有刑法尚未對環境犯罪客體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在司法中對環境犯罪客體的認定,卻更偏向權利,而不是局限在某類一般性的社會管理秩序范疇,這也導致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設定的被侵犯的客體與之不符。因此,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歸類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顯然無法突出當前環境犯罪危害結果的嚴重性、特殊性,由此導致的刑法典中環境犯罪地位低下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與當前環保急迫性、嚴重性、特殊性恰相反。
偏離國際標準,立法延展性缺乏。盡管《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對環境犯罪條款進行了修改,但是我國刑事立法在設置環境犯罪時仍按照實害犯模式執行。與使用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各個國家立法現狀相比,我國環境犯罪范疇界定“危險犯”時產生的偏差,主要來自理念的局限性、環境污染行為以及此行為所引發的成效特征。按照國際標準,此類因素應該被列為環境立法中的考慮因素,事實上卻并非如此。相比較環境污染的以上幾類具有持續性的“負性能”,我國環境犯罪立法在理念、方式、內容等方面,不僅無法滿足環境污染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同樣因其與國際標準之間的偏差,使得其在立法和理念層面存在明顯的缺陷。
非刑罰手段缺失,刑罰體系殘缺不全。當前在環境犯罪刑罰設置上,我國的懲罰條款或方式只有罰金刑和有期徒刑兩種。與發達國家的立法方式及現狀相比,我國環境犯罪刑罰內容和體制的不夠完善性已經比較明顯。我國刑法當前在資格刑的設置上只設定了剝奪政治權利一項,而環境犯罪刑罰中此項卻沒有被引入。增設剝奪環境犯罪分子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或者某種職務的資格刑,可在理想范疇達到特殊預防、一般預防的雙重目的。
域外經驗借鑒下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的修復思路
域外不同法系在環境犯罪刑法規制方面的經驗,對我國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的輔助在于三個層面:
扭轉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的理念。環境狀況的惡化源自目前國內外的現代化發展均以經濟和利益為第一要義。科學檢測方式和發展程度在現階段的環保治理中僅能起到預測和輔助作用,環境本身缺乏發聲能力,良好的或者惡化的環境只能通過作用于人,才能表現出來。但如果人無此意識,即便出現環境惡化,人類也無法觀察和體會到。在我國目前的環境刑法治理理念中,此類無法被觀測的和具有動態變更性、持續性的環境犯罪,并不會被視為環境刑法立法規范轄區。即便是國際標準下有關環境問題治理、新興環保觀念的出現及不斷成型,也無法解決我國所面對的此類環境犯罪刑法治理的理念不足和扭曲的問題。
嘗試引入并重新界定環境危險犯概念。與一般犯罪的差異在于,環境犯罪的行為及后果存在滯后性,假設以結果犯作為環境危險構罪要件,自然無法達成很好的預防和懲治的功能。如果使用單一化的行為犯作為要求要件,行為人對環境的危害、引發的后果所存在的差異性,同樣不能統一地使用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我國屬于大陸法系國家,可借鑒同法系代表如日本和德國對環境犯罪的“環境危險犯”的規定,并以此為基礎結合我國環境犯罪治理的漏洞和實際司法需要進行刑事立法的完善,環境危險犯的概念自然需要按照環境犯罪當前及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重新界定,以體現出刑法不僅具有事后懲處作用,還具有事前預警及進展觀測和治理的能力。
優化司法制度,完善相關立法。嚴格責任原則以英美法系國家為應用對象,在大陸法系國家卻并未涉足。我國堅持將主客觀相統一作為刑事立法方面原則,即犯罪行為人必須具有主觀的犯罪意識,并客觀行為已經達成了犯罪事實。盡管嚴格責任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迥異,但是在司法中兩者的性質容易混淆,因此環境犯罪的立法中多忽視其確認要求。實際上兩者必須進行明確區分,如無過錯責任原則不對行為人主觀因素進行要求,相對忽視行為人過失與犯罪事實之間的相關性,嚴格責任原則卻對行為人客觀犯罪行為的存在與否進行嚴苛的衡量,對于行為人能否證明自己屬于過失還是故意方面,則要求行為人必須出示證據。嚴格責任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最為直接的區別在于,兩者均免去公訴方需要證明行為人的客觀過失行為環節,但是這不意味此環節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是將過錯義務的證明轉移到行為人方。
持續完善環境犯罪刑罰手段。以財產刑代自由刑的運作方式可考慮納入到環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各國對環境犯罪刑事治理的持續探索,引發了環境犯罪中罰金刑作為刑罰適用范圍的持續擴展。非刑罰手段和資格刑適用領域的擴大對完善環境犯罪刑罰方式也具有極為明顯的推動作用。相比較審問、思想教育等懲戒手段,剝奪某個領域中的某項權利或者以嚴厲的經濟懲處為基礎,輔之以非刑罰手段和資格刑,可改善現有環境犯罪司法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可彌補單一化刑事處罰無法阻隔的持續犯罪。
當前環境犯罪刑法治理修復路徑的選擇
以人為本健全非刑罰規定及刑種。由于環境犯罪侵犯的是他人、組織、國家的環境權利,其造成的后果具有數量、對象、結果遠大于一般性的犯罪行為的特質,因此獨立設章的過程中可重新界定犯罪范圍等,如將客體限定在公民、組織、國家可享有的健康、安全的環境及權限范疇。
擴展環境犯罪規制范圍。按照政府2013年、2014年、2015年公報,建議將噪音污染、草原破壞行為、破壞濕地行為列入環境犯罪規制中。噪音污染的行為入罪主要以我國近年來的城市化建設進程突進正相關,盡管噪音污染無形,但是其對國人正常生活的限制和影響卻不可估量。建議從立法層面將包含工業建設等在內的噪音污染行為入罪,當然在入罪之前,必須明確分辨噪音影響及類別。刑法目前僅對農耕地破壞進行了懲處界定,草原破壞行為的構罪設置卻缺乏。草原破壞行為入罪原因在于為最大化避免因經濟大幅度增長,而帶來的因放牧過度、開墾、挖掘、采礦等引發的草原破壞。盡管《草原法》第 56 條提出了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也存在司法執行缺乏標準要件的尷尬。
構建科學規制體系及內容。按照適用嚴格責任原則,明確嚴格責任制度,需要正確掌控嚴格責任原則本質。嚴格責任適用時,以過錯原則為基礎,程序法與實體法都需要執行嚴格限制要求。進行司法制度完善時,可從放寬立案條件、完善起訴和立案、有針對性的細化立法和程序步驟、流程等方面考量。
完善起訴實際是針對環保案件起訴意見書來應用的,建議將環保機關專業意見納入到起訴意見里,以應對環境犯罪的各類屬性。環境犯罪規制內容的完善方面,建議變更“結果犯”為“行為犯”、完善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和非法處置進口固體廢物罪的立法限定及懲處措施、優化侵害環境資源類犯罪的對象范圍、說明如珍稀植物制品和走私珍稀植物的懲處方式,擴大毀壞國家重點保護動植物、林木類犯罪行為、非法采伐的內容、范圍,擴展珍貴動物制品、走私珍貴動物犯罪對象范圍等,此類可作為完善規制體系內容的補充條款。
(作者為包頭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錢小平:《環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經驗與中國借鑒》,《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3期。
②陳開琦,向孟毅:《我國污染環境犯罪立法的哲學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
③王勇:《環境犯罪立法:理念轉換與趨勢前瞻》,《當代法學》,2014年第3期。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