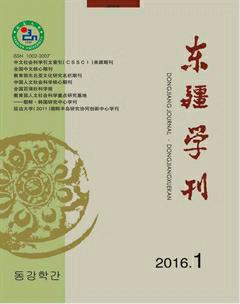對中國“燕行錄”研究的歷時性考察
金柄珉 金剛
[摘要]中國的“燕行錄”研究已經(jīng)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燕行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價值研究、總體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學科研究以及文獻學研究五個方面;“燕行錄”研究中,中、朝、韓的研究各有側重,因此,今后需要進行系統(tǒng)的、帶有具體問題意識的研究。此外,新的視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
[關鍵詞]“燕行錄”;中國“燕行錄”研究;學術課題;方法論
“燕行錄”是朝鮮朝中后期朝鮮外交使節(jié)團來訪清朝的中國體驗敘事。250年間發(fā)生的數(shù)百次燕行留下了280余種“燕行錄”文獻。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對研究韓國文學和中韓關系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和文獻價值,因而部分學者稱其為重要的“歷史文件”。特別是“燕行錄”展示了朝鮮朝時期燕行使節(jié)們深刻的文化反省和嶄新的“域外視角”,反映了清朝乃至東亞歷史文化現(xiàn)場,而我們則從中可以獲得對歷史問題的種種答案。
“燕行錄”具有的這種歷史文化價值,使得“燕行錄”研究在進入本世紀之后,在學界獲得了堪與“敦煌學”比肩的地位,因而有學者提出“燕行錄學”的說法。“燕行”的朝鮮使節(jié)團人員達到數(shù)十萬,是“韓中交流史”的生動現(xiàn)場,也是朝鮮知識分子“通向世界之路”。換言之,“燕行”也是為實現(xiàn)自我認定和自我省察而尋覓新時空的行為。燕行使節(jié)們在燕行旅程中獲得的多樣化體驗與本土經(jīng)驗結合造就了多樣化的文學敘事。不同時代的外交使節(jié),特別是那些進步的知識分子為解決朝鮮朝所面臨的時代課題表現(xiàn)出的苦悶,做出的思索,值得我們深思。
對“燕行錄”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不僅對研究中韓文化關系,乃至研究韓國文學和中國文學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通過相關文本對研究中韓兩國的政治、經(jīng)濟、歷史、哲學、藝術,甚至自然科學諸領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對“燕行錄”研究進行的縱向考察主要局限于依托個別的研究課題進行的先行研究考察,而對研究史的總體考察并不多。其中王友浪、程功、劉加明等人的論文《近二十年中國“燕行錄”研究綜述》,從中韓交流、社會研究、人物研究、文學研究等方面對中國“燕行錄”研究的歷史進行了考察。該論文條理清晰,分析明確,但未能對研究史進行縱向的考察,缺乏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流于泛泛的敘述。韓國雖然有不少考察研究史的論文,但卻沒有論及中國的研究史。本論文在以往“燕行錄”研究的成果基礎上,擬對中國的“燕行錄”研究史進行歷時性考察。同時,以研究史的考察為依托,對“燕行錄”研究要采取的學術課題和研究方法論提出自己的淺見。
一、中國“燕行錄”研究
中國的“燕行錄”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前集中在《熱河日記》的研究上,這與朝鮮的影響有很大關系。改革開放初期,研究《熱河日記》的論文有鄭判龍的《朝鮮實學派文學與樸趾源的小說創(chuàng)作》等。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版了《朝鮮古典文學作品選集》,里面就包含有《樸趾源選集》,收錄了《熱河日記》中的一部分。許文燮的《朝鮮古典文學史》對樸趾源的《熱河日記》進行了分析、評價。韋旭升的《朝鮮文學史》、《中國文學在朝鮮》等著作也對《熱河日記》展開了分析。蔡美花的論文《樸趾源小說的近代思想要素與藝術形象性》分析、評價了《熱河日記》中所表現(xiàn)的文學思想,特別是對《許生傳》、《虎叱》等小說中所表現(xiàn)的近代性進行了深入研究,引起了學界的矚目。
在中國,“燕行錄”研究真正成為學術研究對象還是在中韓建交之后。當時,韓國出版的《國譯燕行錄選集》和與“燕行錄”相關的研究著述被介紹到中國,隨著中韓學術交流的活躍,與“燕行錄”研究相關的學術活動也變得豐富多樣。特別是隨著中國研究生擴招以后,“燕行錄”成為了學位論文的重要研究課題。其中不容忽視的是活躍在中國學術界的中堅古文學者大舉投入到“燕行錄”研究中,成為了“燕行錄”研究得以持續(xù)進行、質量不斷提升的重要契機。
(一)“燕行錄”的文化價值研究
在研究清朝中韓關系方面,中國學術界一直以來都是將《清史》、《李朝實錄》等作為基本資料,所以當韓國出版的“燕行錄”傳人中國之后,中國學術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因為不僅在研究中韓關系方面,在清史研究方面“燕行錄”也同樣是寶貴的資料。因而“燕行錄”研究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成為了重要的研究對象。周俊旗的《韓國版(燕行錄全集)對中國史研究的史料價值》,寧俠、李嶺、曹永年合著的《為“燕行錄”的構建吶喊》,楊軍的《燕行錄全集訂補》,王政堯的《“燕行錄”:17-19世紀中朝關系史的重要文獻》,陳尚勝的《明清時代的朝鮮使節(jié)與中國記聞——兼論“朝天錄”與“燕行錄”的資料價值》等都是闡明“燕行錄”研究學術價值和意義的重要論文。其中,寧俠等人合作的論文是對邱瑞中的著述《燕行錄研究》所作的書評。該論文開篇就寫道,自古以來,新學問大部分源于新發(fā)現(xiàn),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催生了“甲骨學”,敦煌遺書的發(fā)現(xiàn)誕生了“敦煌學”,他們認為從高麗到朝鮮朝700年間形成的文獻形式“燕行錄”必須在世界歷史學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并以此回應了邱瑞中教授首次提出的“燕行錄學”的概念,從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實際上,中國學術界有不少學者都主張建立與“甲骨學”“敦煌學”可以比肩的“燕行錄學”。而隨著中國的“燕行錄”研究的日益深化,“燕行錄”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會越來越高。
周俊旗的論文《韓國版<燕行錄全集>對中國史研究的史料價值》是一篇專門闡述“燕行錄”價值的論文。在敘述“燕行錄”內容構成和特征等之后,他指出“燕行錄”不僅在東亞地區(qū),即使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罕見的,燕行錄文獻具有資料文體多樣、作家背景不同、年代久遠等特征。該論文分別從“燕行錄”的史料價值、中國學界對“燕行錄”資料的利用和研究、“燕行錄”的局限性等三個部分對“燕行錄”的價值進行了論述。有關“燕行錄”的資料價值,作者認為它具有獨特的觀察視角和分析角度、廣泛而豐富的內容、資料查找便利等價值。同時,作者還指出“燕行錄”充分體現(xiàn)出了朝鮮人的聰明智慧,他們通過獨特的視角、思維方式和寫作方法詳細地記錄了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發(fā)表了各種獨具慧眼的評論。不少分析不同于中國文獻,從旁觀者的角度對中國形象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記錄,為相關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難得的參考。他還強調“燕行錄”在中國還是個尚未充分開掘、應用的資料寶庫,并肯定了“燕行錄”的學術價值。另外,作者還指出了《燕行錄全集》編輯過程中的不足之處,強調了“燕行錄”本質性的規(guī)范問題。不過,他還是認為《燕行錄全集》編輯者的意圖及全集的研究價值是不容否定的。該論文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學者對“燕行錄”在學術資料方面價值的看法。
“燕行錄”研究的學術價值可以說與“燕行錄”本身的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價值是成正比例的。陳尚勝的論文《明清時代的朝鮮使節(jié)與中國記聞一一兼論“朝天錄”與“燕行錄”的資料價值》通過考察朝鮮使節(jié)的中國見聞,對“燕行錄”的資料價值進行了深人研究。作者特別強調指出,“燕行錄”不僅是研究中韓交流史的寶貴資料,即使對研究中西交流史也同樣是寶貴的資料。另外,對研究中國的地方史,尤其是研究社會史也具有資料價值。美中不足的是,該論文對“燕行錄”的價值判定僅僅局限在資料價值上了。其實,“燕行錄”的價值不僅僅在于資料方面,其作為歷史的一面“鏡子”也大有意義。因此,對“燕行錄”的價值的理解需要全人類的、整體的學術視角。
(二)“燕行錄”的總體研究
總體研究指的是以多種“燕行錄”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特征的一種研究方法或范式。“燕行錄”總體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有金柄珉的《朝鮮北學派文學研究》、李巖的《實學派文學觀念研究》、金柄珉和徐東日合著的《韓國實學派文學與中國文化之關聯(lián)》、劉為的《清代中朝使臣往來研究》、徐東日的《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楊雨蕾的《燕行與中朝文化關系》、李根碩的《朝鮮的中國想象與體驗(7世紀至19世紀)——以燕行錄為中心》等論著以及葛兆光的《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后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孫衛(wèi)國的《“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記錄》、王政堯的《“燕行錄”初探》、牛林杰、李學堂的《17-18世紀中韓文人之間的跨文化交流與文化誤讀》等論文。
金柄珉的《朝鮮中世紀北學派文學研究》(1990)是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是國內第一篇研究“燕行錄”的博士學位論文,并為延邊大學成為中國“燕行錄”研究的重要陣地提供了契機。該論著對洪大容的《燕記》、《干凈洞筆談》,樸趾源的《熱河日記》,李德懋的《人燕記》,柳得恭的《燕臺再游錄》,樸齊家的《燕行詩歌》等進行了綜合考察,對北學派文人的中國認知和文學觀,及其與中國文人的思想、文化交流,燕行小說、詩歌、散文的特性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部論著在運用傳統(tǒng)的歷史美學方法論和傳記批評方法論的同時,在運用系統(tǒng)論的方法論、接受美學,以及比較文學的媒介學、主題學、精神分析學和神話批評等新的方法論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是徐東日的代表性學術成果。該著作充分顯示了作者寬闊的學術研究視角和見解,以及中國“燕行錄”研究的傾向和水平。在此書中,作者綜合考察、分析了“朝天錄”和“燕行錄”中的重要作品,如洪翼漢的《朝天航海錄》、金埔的《潛谷朝天日記》、許葑的《荷谷先生朝天記》、麟平大君的《燕途紀行》、金昌業(yè)的《老稼齋燕行錄》、洪大容的《湛軒燕記》、李德懋的《入燕記》、樸趾源的《熱河日記》、柳得恭的《燕臺再游錄》等。該著作不僅考察了朝鮮朝使臣們的朝天、燕行的歷史過程,而且歷時性地分析了朝鮮朝使臣眼中的明代中國形象以及不同階段的清朝形象,闡明了形象的內容、形象的變遷及其原因,還對朝鮮朝形成這種不同的中國形象和想象的主要原因等進行了闡釋。在作者看來,朝鮮朝使臣們創(chuàng)造的明代中國形象可以分為“繁榮、進步的中國形象”和“灰色、黑暗的中國形象”兩種,清代的中國形象也可以分為“烏托邦形象和意識形態(tài)形象”。作者在該著作中運用了比較文學研究的形象學理論,但是并沒有盲目受制于這一理論,充分表現(xiàn)出學術上的創(chuàng)新精神。該論著雖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也留下了一定的局限性,如分析一篇“燕行錄”作品出現(xiàn)的形象雙重性時,特別是在闡明同時表現(xiàn)出烏托邦形象和意識形態(tài)形象的原因方面,理論性闡釋軟弱無力。而且在中國形象方面,如果能夠在庶民形象進行深入研究則更能提高其社會史方面的研究價值。
劉為的《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從歷史研究角度對清代中韓兩國使臣往來的制度、使行的種類、使節(jié)團的規(guī)模、使行路線、禮儀等進行了詳細的歷史考察。楊雨蕾的《燕行與中朝文化關系》論述了明代的“朝天”事項和清代的“燕行”事項的歷史狀況以及“朝天錄”、“燕行錄”、“飄海錄”等使行記錄的一般狀況,敘述了“燕行”使臣們與清代文人的文化交流、“燕行”與朝鮮的“西學”及“北學”的關聯(lián)。
李根碩的博士學位論文以比較文學和文化批評為中心,結合結構主義、解釋學、新歷史主義批評方法,綜合考察了20余部“燕行錄”作品,分析、評價了朝鮮使臣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知。并且把著力點放在了中國認知的背景和原因的闡釋上。作者認為“燕行錄”是通過中國認知談論韓國,并從視角的非融合型、視角的融合型、積極的融合型三方面對其特征進行了考察。他認為非融合型以李海應的《薊山紀程》、徐慶純《夢晶堂日史》為代表性作品,其特點是對清朝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作者不詳?shù)摹陡把嗳沼洝贰⒔鹁吧啤堆嘬幹敝浮穼儆谌诤闲停鋵θ招略庐惒粩喾睒s的清朝雖然沒有持否定態(tài)度,但并沒有修正傳統(tǒng)的看法。一方面贊美清朝的治國治世,另一方面又批評清朝對傳統(tǒng)文化的背離。而積極融合型雖然以韓國對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看待清朝,但在傳統(tǒng)觀念基礎上融人了新的觀念,創(chuàng)造出了北學論的新觀念“尊周論”、“尊華論”、“北伐論”,還對偽善的士大夫進行了抨擊。其實,“北學”不過是排斥當時在朝鮮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中國觀念的手段而已。作者還指出,北學派的形成是通過直接實驗體驗中國的視角融合的結果,代表性的作品有《熱河日記》、《湛軒燕記》、《北學議》等。作者的結論是:“從話語的角度來講,不融合是強化傳統(tǒng)話語的形態(tài),混合是傳統(tǒng)話語和對滿清的正面視角共存的形態(tài),融合就是創(chuàng)新新話語的形態(tài)。”該論文還使用了比較文學形象學的方法對“燕行錄”中的套話進行了研究,他深入研究了“(北佬)”、“(高麗棒子)”的詞源和衍變,指出了這些詞語在中朝關系史中的負面作用。該論著角度新穎,方法多樣且富有聯(lián)系,考證嚴密,頗受矚目。作者在結尾部分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之后,指出了韓中在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并認為韓國方面的研究只是以國別研究和中韓交流史為中心展開,而中國方面的研究只是以歷史史料為中心展開。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克服過于集中在文學和歷史方面的局限,進一步擴大研究領域,提出應該通過“燕行錄”開拓東北地區(qū)俗語研究、兒童游戲研究、禮賓文化研究、北京的物價研究等新的研究課題。不過,論文提出的部分觀點,如,將北學視為單純的手段,小說《兩班傳》是燕行體驗的產(chǎn)物等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期刊上發(fā)表的很多相關論文從各種角度對“燕行錄”進行了考察,提出了新的問題,得出了新的結論。如,葛兆光的《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后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一文通過對“燕行錄”的總體研究,指出:“東亞文化共同體是從17世紀中葉以后開始瓦解的。”盡管該觀點值得商榷,但論者眼光獨到、銳利,充分展現(xiàn)了以新的視角把握當時東亞社會、歷史發(fā)展本質的學術態(tài)度。此外,牛林杰、李學堂的論文《17-18世紀中韓文人之間的跨文化交流與文化誤讀》較早從跨文化研究的視角觀照中韓文人之間的歷史和現(xiàn)實,發(fā)現(xiàn)了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
綜上所述,總體研究對引領多樣化的研究提供了契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多樣化研究的總結。
(三)“燕行錄”的作家、作品研究
縱觀“燕行錄”的研究史,可以說對作家、作品研究是最普遍的學術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博士學位論文金哲的《樸齊家文學和清代文學關聯(lián)研究》、劉廣銘的《朝鮮朝話語中的滿族形象研究》、楊昕的《朝天錄中的滿族形象研究》、韓衛(wèi)星的《洪大容文學研究一一兼論與中國文化的關聯(lián)》、許明哲的《<熱河日記)的文化闡釋》、馬婧妮的《(熱河日記)中的中國形象研究》、韓龍浩的《19世紀“燕行錄”中的中國形象研究——以三種“燕行錄”為中心》、樸雪梅的《柳得恭文學的文化批判》、張麗娜的《熱河日記研究》等。
上述學位論文充分反映了中國年輕一代研究人員研究“燕行錄”的特征。在方法論上,這些論文可以分為三大類:金哲、韓衛(wèi)星、許明哲、樸雪梅等人的論文主要運用了比較文學的主題學、媒介學和文化批評等方法;楊昕、韓龍浩、馬靖妮、劉廣銘等人的論文主要運用了比較文學形象學的方法;張麗娜的論文運用了歷史美學、文化學和比較文學形象學等多種研究方法。
金哲、韓衛(wèi)星的論文著重對樸齊家、洪大容與中國文學、文化之間的關聯(lián)性進行了周密的考察,在一定深度上揭示了他們的文學活動、文學交流、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征等,可以說開創(chuàng)了中國北學派文學研究的新篇章。許明哲、樸雪梅的論文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對樸趾源、柳得恭的文學進行了研究。
劉廣銘的論文的價值在于運用了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燕行錄”;楊昕的論文運用比較文學形象學方法對在學界并沒有受到矚目的朝鮮朝時期的“朝天錄”進行了研究,為歷時性研究“朝天錄”、“燕行錄”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韓龍浩的論文運用比較文學形象學方法分析了《燕臺再游錄》、《燕轅直指》、《夢晶堂日史》等三部“燕行錄”,闡明了“燕行錄”的歷史價值、思想價值等,揭示了這些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折射出的朝鮮人的文化心理和總體想象。馬靖妮的論文同樣以比較文學形象學為主要方法闡明了《熱河日記》中的中國形象的特征和本質,以及朝鮮的集團想象。
張麗娜的論文是對《熱河日記》進行總體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在闡述樸趾源文章的時代特性、樸趾源的生平和思想之后,對《熱河日記》進行了條分縷析的研究。即對研究對象進行了詳細的文獻考察、文體考察,闡明了“北學”思想、改革精神及哲學基礎。同時,作者還分析了《行在雜錄》、《山莊雜記》等雜文類作品的內容和創(chuàng)作手法,以及《口外異文》、《盎葉記》等作品的人文精神。并從中國形象的創(chuàng)造、生動的藝術形象刻畫、辛辣的諷刺藝術、樸素而真實的語言藝術等方面概括了《熱河日記》的藝術特色。最后,作者認為《熱河日記》是游記文學的里程碑作品,是游記文學集大成的力作,對朝鮮王朝給予了沉重打擊,并進而成為“文體反正”運動的契機。從時代、國家、文化運動的角度高度評價了該作品的地位。該論文表現(xiàn)出了文史哲統(tǒng)合的視角、方法論的多樣化、分析的嚴謹周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有機結合。不過,論文也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局限,研究的重點和焦點有些散亂,作者核心的問題意識和層層推進的邏輯能力略顯不足。
期刊論文同樣也是以《熱河日記》為研究對象的最多。代表性的論文是李巖的《樸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yè)方略》、《樸趾源(熱河日記)的實學精神和文藝觀探析》,樸蓮順和楊昕的《(熱河日記>中的康乾盛世》,金柄珉的《(熱河日記)與中國文化》、《樸趾源的小說(虎叱)的象征性研究》,王政堯的《18世紀朝鮮的“利用厚生”學說與清代中國——(熱河日記)研究(1)》,張雙志的《18世紀朝鮮學者們對清代西藏的觀察——讀樸趾源的(熱河日記)》等。這些論文運用了歷史傳記批評、比較文學形象學、文化研究等研究方法闡明了《熱河日記》的思想性、藝術性價值,以及文學史、文化史和中韓交流史意義。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國學界研究樸趾源及《熱河日記》的論文超過了100篇,這足以證明其學術意義和價值。
此外,研究“燕行錄”的作家、作品的論文有金柄珉的《試論洪大容與“古杭三才”的思想文化交流》、《朝鮮樸齊家與中國清代文壇》、《(燕京雜絕)反映出的樸齊家的中國文化觀》、《哲理小說<醫(yī)山問答)反映出的洪大容的自然哲學思想和文化意識》,顏寧寧的《(燕轅直指>研究》,谷小溪的《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王振中的《朝鮮燕行使者所見18世紀盛清社會一一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韋旭升的《中朝文士之間的交游——讀(燕臺再游錄)》,劉廣銘的《<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康熙形象——兼與同時代歐洲話語中的康熙形象比較》,樸香蘭的《燕行錄所載筆談的文學形式研究——以洪大容與樸趾源為中心》,《由筆談管窺中朝文人文化意識的差異——以樸趾源、洪大容等為例》,祁慶福和郭平合寫的《清代朝鮮使臣與醫(yī)巫閭山》等。
上述論文,除了部分之外,大體上都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北學派”的“燕行錄”上了。其中一部分是在自己的學位論文基礎上完成的成果。顏寧寧的《(燕轅直指)研究》和谷小溪的《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的意義在于將研究的目光轉向了19世紀的“燕行錄”上。王振中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在考察資料和把握問題方面有一定的深度。劉廣銘的論文將《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康熙皇帝形象與西方的中國形象進行了比較,非常新穎。元老學者韋旭升對《燕臺再游錄》進行了研究,表現(xiàn)出材料分析的客觀性和考證的嚴密性,顯示出了韓國文學研究元老的實力。
祁慶福和郭平合寫的論文對《醫(yī)巫間山》進行了歷史的、文化學的考察,對醫(yī)巫閭山和朝鮮使臣們的關系等背景進行了分析,他們將對金昌業(yè)的《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醫(yī)巫閭山游記和洪大容的哲理小說《醫(yī)山問答》的分析結合起來,具有不容小覷的學術價值。作者在論文中指出“老稼齋筆下,三百年前的巫醫(yī)閭山名勝歷歷在目,詳實的記錄湮滅了時間的概念。金昌業(yè)是迄今所知登臨醫(yī)山中唯一留宿的朝鮮人,這為他仔細踏訪名山,寫出藝術價值頗高的游記創(chuàng)造了條件,后來者無不羨慕不已。”在論述洪大容的《醫(yī)山問答》時指出“老稼齋之后,親身登臨醫(yī)巫閭山并留下不朽名篇者,是朝鮮著名學者洪大容。”并闡述道:“燕行之后,他在《醫(yī)山問答》中升華了自己的北學思想,其論著冠以‘醫(yī)山之名,無疑具有重要而鮮明的象征意義,表明這是一篇燕行啟示錄。”接著作者還指出洪大容打破了儒家的“天圓地方說”,接受了西方的“多世界說”,高度評價其“地轉說”、“無限宇宙說”在朝鮮科學史乃至東方科學史上都留下了璀璨的一頁,并指出這是“燕行北學重要的成果”。該論文還分析了樸趾源撰寫的位于醫(yī)巫間山附近的北鎮(zhèn)廟游記,并且列舉之后登上北鎮(zhèn)廟的43名使臣,指出他們全都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為今后的研究布好了局。在論文中還引入了與北鎮(zhèn)廟有關的中國文人賀欽的故事,認為洪大容想在醫(yī)巫間山尋找桃花洞有可能是要尋找賀欽。洪大容通過真理的化身實翁的形象,表達了自己的觀念和思想:“他在《醫(yī)山問答》中虛擬了一位真理的化身——實翁,通過實翁,表達了自己的觀念和思想。這位實翁在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但這一人物的形象寓含著歷史上曾聞名于醫(yī)巫閭山的醫(yī)閭先生的影子。”雖然論者的這種見解也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自成一說卻是顯而易見的。該論文的特點是將歷史和文學、文學和哲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交匯展開論述。
樸香蘭的《燕行錄所載筆談的文學形式研究——以洪大容與樸趾源為中心》是一篇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論文。作者圍繞著“燕行錄”筆談的文學性及其特征展開條理清晰、層次分明的論述,具體將其作為獨立的文學文本,設定筆談的形成、主題中心的筆談轉換、人物中心的筆談等論題,闡明了筆談的主題、筆談的結構和表現(xiàn)方式等,指出了筆談具有的價值和意義,為“燕行錄”研究,特別是筆談研究做出了相當大的學術貢獻。另外,樸香蘭在其另一篇論文《由筆談管窺中朝文人文化意識的差異——以樸趾源、洪大容等為例》中闡明了中韓文人在女性問題、婚冠喪祭、士農工商等方面的文化意識差異。該論文角度新穎,觀點明確,資料取舍得當,論證嚴密。如果能夠融入跨文化研究的理論,一定會使其研究更加深入。
(四)對“燕行錄”的跨學科研究
跨學科研究大大擴展了“燕行錄”研究的范圍,不僅使得人文社會科學內部可以相互交叉,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嫁接也成為了可能。為更廣泛、更深入地揭示“燕行錄”的人類精神史上的價值提供了學術條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有汪銀峰的《域外漢籍“燕行錄”與東北方言研究》、錢蓉和赫曉琳合寫的《從“燕行錄”看康乾時期中國民俗文化》、楊雨蕾的《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陳冰冰的《(四庫全書)與李氏朝鮮后期的文壇動向》、石云里的《從黃道周到洪大容——17、18世紀中期地動學說的比較》、劉靜的《從燕行錄看18世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劉香的《朝鮮赴京使臣的西洋認知(17-19世紀)——以(燕行錄全集)為中心》)、李春梅的碩士學位論文《(燕行錄全集)中的醫(yī)學史料研究》、陳明的《“吸毒石”與“清心丸”——燕行使與傳教士的藥物交流》、張升的《朝鮮文獻與四庫學研究》等。
以上論文從語言學、民族學、圖書學、文化學,甚至自然科學中的醫(yī)學、天文學角度對“燕行錄”進行了研究,擴大了“燕行錄”的研究領域。這些研究通過對“燕行錄”的多學科著手,對相關學科的研究也很有幫助,形成跨學科研究的良好契機。同時,進一步提升了“燕行錄”的學術價值和意義。如,石云里的論文對洪大容的《醫(yī)山問答》中所體現(xiàn)出的自然科學思想及其文化意識的研究,對研究中韓科學交流史也有著重要意義。陳冰冰的論文考察了韓國方面對清代重大的文化措施和工程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應。劉香的論文考察了中西、中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宗教層面的交流狀況,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而張升的論文通過考察《熱河日記》,從多角度揭示了“四庫學”與韓國文獻的關聯(lián)。作者按著《四庫全書》的館員、篇數(shù),《四庫全書》和“禁書”,對《四庫全書》及總目錄的評論等章節(jié)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韓國文人們的特殊視角和中國文獻沒有記錄到的重要信息。作者通過詳細的考證指出:“朝鮮文獻中保存有相當豐富的四庫學研究資料。這些資料一方面可以彌補中國文獻的缺漏,一方面可以與中國文獻相參證,從而有力地推進四庫學研究。”
(五)對“燕行錄”的文獻學研究
對“燕行錄”的文獻學研究是最基礎的工作,需要豐富的文獻學知識和學術水平。祁慶福的論文《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關于新發(fā)現(xiàn)的(鐵橋全集>》不僅在研究洪大容方面具有獨到見解,在研究浙江和杭州文化方面也很有意義。洪大容和清代文人嚴誠是“生死之交”,在18世紀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美麗的一頁。作者考察和追蹤了當時洪大容和嚴誠的交流情況,從文獻學角度對保存在韓國的嚴誠文集《鐵橋全集》進行了周密的考證和分析,對完善洪大容、嚴誠研究,乃至18世紀中韓文化交流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引人注目的是這篇論文還對在韓國與《鐵橋文集》一同發(fā)現(xiàn)的嚴誠的《嚴誠尺牘》進行了比較分析。這些文獻雖然不是作者發(fā)現(xiàn)的,但他以淵博的文獻學知識挖掘出新的資料并準確地介紹到學界,對此,我們應該給予高度評價。此外,祁慶福和金成南合寫的論文《關于中韓文化交流史史料的發(fā)掘與整理》考察并介紹了傳播到中國的韓國文獻,論文考證了保存在北京大學的《海東詩選》的編者,確認編者為洪大容的文友閔百順。閔百順受洪大容的委托編輯了這部書,洪大容策劃編輯該書則是應清代文人潘庭筠的囑托。通過當時洪大容和潘庭筠的往來信函,可以了解編輯過程和潘庭筠拿到書的內容。作者準確地掌握了這些事實,經(jīng)過考證適時地介紹到了學界,這對研究洪大容的燕行具有重要意義。
黃晉基的論文《燕行途程考——周流河考》對當時“燕行”使節(jié)必經(jīng)的并留下無數(shù)故事的周流河進行了文化地理學的考證。漆永祥的論文《關于“燕行錄”的界定及收錄范圍之我見》和《關于(燕行錄全集)之輯補與新編》運用豐富的文獻學知識對有關“燕行錄”性質的界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闡明了根據(jù)“燕行錄”的性質確定全集收錄范圍問題。作者就界定“燕行錄”的性質問題提出兩個必須滿足的條件:“就作者而言,必須是國王派遣的使臣或使團中的某個成員,個別是負有國王某種特殊使命的官員;就其所到之地而言,必須是到過中國,或者到過兩國邊境的中國境內。反過來說,不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而只具備其中的某一個條件,都不能算做是‘燕行錄。”因而,他認為《漂海錄》、《皇華集》、《柬槎錄》、《賓接錄》等詩文,以及相關著述不能視為“燕行錄”文獻,也不應收錄到《燕行錄全集》中。他的這些觀點在學界內引起了不同的反應,但對界定“燕行錄”的性質,確定“燕行錄”文獻收錄范圍上有很大助益。上述論文為“燕行錄”的文獻學研究樹立了楷模,也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
在文獻學研究方面,對“燕行錄”原典的校點、校注也是重要的內容。在這方面,中國的古文獻學學者擁有相當大的優(yōu)勢。朱瑞平校點的《熱河日記》和劉順利的《“薊山紀程”細讀》等在“燕行錄”文獻整理方面成績突出。朱瑞平校注的《熱河日記》以1931年在朝鮮出版的《熱河日記·別集》作為底本,以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本(26卷影印本)和1968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出版發(fā)行的,即李家源先生校注的《熱河日記》作為了參考本。同時還附有韓國著名古文學者李佑成教授的“序文”、“燕巖樸趾源先生事跡碑”,以及李家源先生的《<熱河日記>解說》等,對讀者的理解有很大幫助。朱瑞平在校點說明中說《熱河日記》是“百科全書式游記”,大贊樸趾源可使它躋身于世界著名文學之列。對于校點原則,作者指出:“至文中錯別字,由于長期傳抄,為數(shù)甚多,為便予讀者,將正字用括號標注于正文中而不改原字。”作者的上述努力和心血對中國學者研究《熱河日記》有巨大的幫助,成為了中國學者全面展開《熱河日記》研究的一個重要契機。劉順利的《“薊山紀程”細讀》是一部校注李海應燕行錄的著述,在文獻整理方面表現(xiàn)出了相當高的水準。該書充分體現(xiàn)了作者誠實的學術態(tài)度、高超的文獻學水平。該書對燕行錄中出現(xiàn)的人名、地名、時間、典故等都做了詳細的注釋。而為了保證文獻整理的正確性,作者甚至親自勘察燕行路程,訪問當?shù)剡z址。作者談到了自己對“燕行錄”的理解,燕行路程長達6000里,“高麗和朝鮮文人的‘燕行錄是用毛筆寫就的,也是‘用腳寫出來的,甚至是用生命寫就的。”作者用自己親身體驗印證了“燕行錄”的價值。上述著述的出版不僅成為中國燕行錄文獻整理的良好開端,也將中國的“燕行錄”研究推上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燕行錄”研究的方法
“燕行錄”研究涉及的學術領域非常廣泛,成果也非常豐富。不過,從總體上看來,朝鮮、韓國的研究主要以本國需求的中國認知為中心,而中國的研究則以歷史、文學研究為中心。因而中國的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不少我們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現(xiàn)象:不是不接納韓國的研究成果,就是拿過來“炒冷飯”。同時,中國的研究在資料甄別方面不夠嚴格,主要專注于樸趾源等18世紀后半葉“北學派”的“燕行錄”,而缺乏對“燕行錄”的總體的、系統(tǒng)的研究,研究方法論也不夠多樣化,在運用上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考慮到這些問題,中國學界當務之急是正確把握學術研究課題,更新方法論,開創(chuàng)嶄新的研究局面。
首先,在“燕行錄”研究上需要系統(tǒng)的研究。因為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
“燕行錄”的相關著作已經(jīng)有數(shù)百卷之多,所以對它的研究不僅需要對其進行系統(tǒng)的考察,還需要帶著具體的問題意識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例如,在中韓文化交流方面,要考察人際交流和往來、筆談和對話、書籍購入和尺牘交流、作品交流和相互影響等,使其全面系統(tǒng)化,歸納其特征。當然要想實現(xiàn)這樣的目的需要閱讀原典,同時也要為形形色色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先行推出“燕行錄”作品的校注。當然,可以閱讀韓國譯本的情況除外。通過全面系統(tǒng)地考察韓國使臣們的中國認知、中國形象和朝鮮朝的“總體想象”的變遷,游記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變化狀況等多方面狀況,對“燕行錄”的特征和價值作深入解讀。
其次,應如實把握“燕行錄”的歷史價值和現(xiàn)實價值,促進跨文化研究和跨學科的交叉研究,解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學術課題。“燕行錄”是跨文化交流的典型產(chǎn)物,我們要把握其中體現(xiàn)出的韓國使臣獨特的文化視角,敏銳地發(fā)現(xiàn)因文化意識導致的觀點差異——即“誤讀和創(chuàng)造性翻譯(或變異)”。歷史上韓國的使臣們通過中國敘事不僅記錄了中國當時的各種文化信息,而且還表達了他們的看法。這些是歷史敘事中的重要發(fā)現(xiàn),也是創(chuàng)造性的見解。當時他們對中國的商業(yè)文化、市民藝術、文人和文壇的動態(tài)、圓明園、琉璃廠、圖書集成、滿族的風俗、漢滿矛盾、文字獄、集市和物價、東北方言、人文地理和遺址等的認識表現(xiàn)出了極其特殊的視角和文化差異。我們應該明白,對這些差異的發(fā)現(xiàn)、理解乃至超越,可以成為認可和理解中國文化,進而理解東亞文化多樣性價值的一面“鏡子”。學術上燃眉之急的課題不一定就是觸及了某種宏大的問題才能獲得肯定,即使是小問題,只要帶著徹底的問題意識去研究就可以。如果通過“燕行錄”能夠找出現(xiàn)在已經(jīng)湮滅的當時東北方言中的一兩個單詞,也是對學術界的大貢獻。而且在“文字獄”大行其道的當時,能夠追蹤筆談對象的復雜心理就已經(jīng)具有了充分的價值。例如,柳得恭的《熱河紀行詩注》寫道,參加乾隆皇帝古稀祝壽的安南使臣雖然穿著滿族服飾出席,但他們的心理活動極其復雜,對此所做的分析可以引發(fā)更大、更深的問題,是真正的“微小大問題”。真正的學問應該是“小題大做”的過程。在韓國《日下題襟集》和《抗傳尺牘》的發(fā)現(xiàn),在中國《海東詩選》的發(fā)現(xiàn),從“燕行錄”研究上看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因而目前的“燕行錄”研究不僅需要“望遠鏡”,也需要“顯微鏡”。為此,一定要熟讀原典,形成相應的考證學風。以上這些迫在眉睫的課題的選定和研究只有在跨文化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相結合之下才有可能。
再次,“燕行錄”研究方面,新的視角和方法論的革新也非常迫切。“人類總是把藝術看作自身生存意義的揭示。當這種意義處于遮蔽之中時,讓你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和藝術存在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辦法。”“燕行錄”研究要擺脫單純的國別視角,需要東亞視角,甚至需要世界視角。事實上,要想真正把握“燕行錄”的價值和意義,必須將其納入到東亞語境乃至世界語境中去分析。例如,比較18世紀朝鮮、韓國“燕行錄”中的中國形象與歐洲人寫的中國游記中的中國形象的差異,揭示形成差異的原因都是極有意義的課題。要想進行這種比較,迫切需要跨文化研究。同時,也要將跨文化研究與政治學、社會學、形象學研究結合起來,而且在運用研究方法論方面,也要根據(jù)研究對象不同,合理地使用好研究方法。對研究方法本身也要進行深入、透徹的理解。例如,看以往的研究,雖然比較文學形象學運用得很多,但由于對該理論理解得不透徹,得出錯誤結論的情況不少。特別是在運用比較文學形象學時應杜絕教條主義傾向。如,“燕行錄”中看到的中國形象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甚至同一作者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烏托邦形象”和“意識形態(tài)形象”復合混雜的情況。無視這種情況單純一貫地將其視為同一形象,必然會招致重大的謬誤。特別是在運用形象學理論的時候,一定要牢記:“當代形象研究將重點放在形象塑造者乙方,探索形象形成的內在邏輯。”因而在使用方法論的時候也要充分考慮具體的情況,把握好方法論本身的局限性。根據(jù)具體的研究對象選擇恰當?shù)姆椒ㄕ摚瑫r按照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將那種方法論融會貫通才是最合理的運用方式。不然,就會陷入問題意識反而落入方法論的窠臼之中,從而不是深入闡釋論題,而是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對方法論正確性的論證。
“燕行錄”既然是歷史現(xiàn)場的敘事,就可以運用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文化交流學,此外,也可以使用歷史社會學批評、傳記批評等傳統(tǒng)的方法,根據(jù)研究對象,還應提倡以文學、文化研究方法為主,綜合運用多學科理論,例如,語言學、心理學、敘事學,甚至地理學、醫(yī)學、考古學等研究方法論。特別是對“燕行”體驗文學研究,迫切需要將比較文學主題學、媒介學、接受美學等與心理學、哲學、文化學等結合進行交叉研究,只有這樣才能使研究深入進行。
最后,“燕行錄”研究迫切需要國內學者攜起手來進行共同研究。“燕行錄”既然是韓國使臣的敘事,就應該積極借鑒有關國家的研究視角,積極汲取他們的研究成果。加強雙方都能揚長避短的合作。因而“燕行錄”研究也要重視與朝鮮使臣的日本使行錄的比較,這不僅對深化“燕行錄”研究具有很大意義,對梳理東亞文化交流史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結語
對“燕行錄”研究史進行歷時考察必須滿足兩個要求:其一是必須對“燕行錄”本身形成一定的研究;其二是要全面把握“燕行錄”的研究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有正確的評價和結論。筆者關注“燕行錄”已經(jīng)20多年了,但仍不敢自夸已經(jīng)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對研究史進行嚴格、縝密的考察決定著論文研究的成功與否。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不能不自責這一點正是本論文的一個缺憾。此外,在“燕行錄”研究學術信息收集方面的不足以及對多樣化的跨學科研究理解不透徹,可能會導致為考察研究史所作的研究對象的選定,以及對個別論著的具體評價失于主觀偏頗的問題。特別是對非燕行文學研究的跨學科論文的評價,盡管在運用相關學科知識方面傾注了努力,但筆者自己對評價的正確與否也無從判定,只能希望筆者的論文對今后的“燕行錄”研究和研究史的考察能有所助益也就心滿意足了。對論文中出現(xiàn)的舛誤還望國內學者同仁不吝賜教。希望今后會有更優(yōu)秀的考察研究史的成果,并進一步促進“燕行錄”研究。
“燕行錄”盡管是韓國使臣的中國體驗,是他們對中國文化資源的多樣化的文學敘事,但也可以說是中韓兩國共有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對“燕行錄”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必將把21世紀中韓文化交流推上新的臺階,也許這正是治學之人的價值和貢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