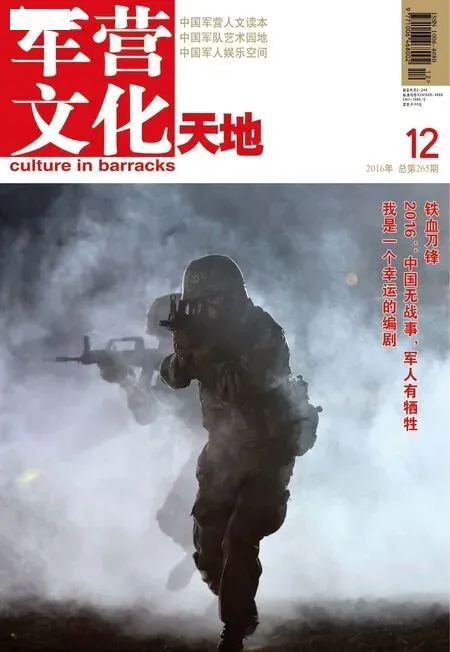我是一個幸運(yùn)的編劇
——專訪《鍛刀》編劇、監(jiān)制王軍
文/喜多瑞
我是一個幸運(yùn)的編劇
——專訪《鍛刀》編劇、監(jiān)制王軍
文/喜多瑞

由著名編劇王軍執(zhí)筆創(chuàng)作、資深制片人曾輝擔(dān)綱制片人兼導(dǎo)演的抗戰(zhàn)題材電視連續(xù)劇《鍛刀》,自國慶節(jié)在央視八套黃金檔開播以來,收視率不斷飆高,可謂是火爆熒屏。
近日,筆者來到著名編劇王軍的家中采訪,剛進(jìn)門便被客廳整整一側(cè)墻的書柜震撼到。滿滿一柜的書籍?dāng)[放得齊整有序,其中有許多戰(zhàn)爭、史詩類書籍。《鍛刀》是以云南滇軍為歷史背景,筆者問王軍是不是在寫劇本前需要做大量相關(guān)功課,王軍卻告訴筆者他本來就是歷史發(fā)燒友,而且《鍛刀》的劇本其實是在沒有提綱、邊拍邊寫的情況下完成的“急就章”。這讓筆者對《鍛刀》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這個自稱“懶而幸運(yùn)”的編劇更加好奇。
開機(jī)前受命,編劇兼任監(jiān)制
筆者:當(dāng)時是怎么一個情況接下了《鍛刀》的劇本?
王軍:在《鍛刀》之前,我正在創(chuàng)作《共赴國難》第一部的劇本,這兩部戲是同一家公司出品,劇情也有近似的歷史背景,就在我寫到第13集的時候,曾輝不由分說,把我抓到了《鍛刀》劇組。當(dāng)時,《鍛刀》的劇本已經(jīng)有兩撥人寫過了,但在開拍前夕演員們圍讀劇本時發(fā)現(xiàn)了重大問題。我看了劇本的前三集和最后一集,發(fā)現(xiàn)確實無法拍攝,只能全部重新寫。由于主要演員已經(jīng)全部選定簽約,服裝量體裁衣基本制作完成;橫店的取景地也已預(yù)定好,美術(shù)組已經(jīng)進(jìn)駐3個月搭景即將完成,所以我只好在保證角色名字和基本人物關(guān)系的前提下,花了9天時間完成了前7集的劇本,以保證劇組能夠按時開機(jī)。之后的所有劇本,都是我在沒有提綱的情況下跟組獨(dú)自創(chuàng)作完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沒有更多時間去查史料的,只能運(yùn)用原來的知識積累去構(gòu)建我的故事。《鍛刀》這部劇涉及的史實部分不會有紕漏,這點我是有足夠自信的。
筆者:很難想象,沒有提綱,您是如何完成劇本創(chuàng)作的呢?
王軍:《鍛刀》這次的劇本創(chuàng)作非常挑戰(zhàn)我的創(chuàng)作技術(shù)。我對人物形象和命運(yùn)的設(shè)計,讓很多演員都很意外,他們已經(jīng)圍讀過兩個劇本了,而我是第一個詢問他們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想法的。跟大廚做什么菜,怎樣選材,才能讓食客們滿意一樣,一名職業(yè)編劇在寫劇本的時候首先應(yīng)該想到的就是:我要寫一個和多個怎樣的人物形象,觀眾才能認(rèn)可呢。急就章尤其考驗編劇的專業(yè)程度。當(dāng)然這種事情,最好不要鼓勵。下不為例吧。
筆者:您在創(chuàng)作中有沒有自己的偏好?
王軍:編劇都應(yīng)該有自己的偏好,說好聽點就是要有美學(xué)追求。如果說吳宇森式電影是一種暴力美學(xué),而我就更喜歡暴力溫情美學(xué),喜歡在暴力環(huán)境下去展現(xiàn)兒女情長。《鍛刀》便是我在這樣一種審美心態(tài)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著名制片人吳毅先生說,《鍛刀》這部戲開創(chuàng)了戰(zhàn)爭劇的一種新類型。我當(dāng)然清醒地知道,這是過譽(yù)之詞。但是以暴力做背景,營造出的規(guī)定情境確實更適合去展現(xiàn)人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的豐富,這一點我很贊同,也是我一向堅持的。
筆者:您還擔(dān)任了《鍛刀》的監(jiān)制。
王軍:對。《鍛刀》這部劇對我來說比較特別的是,我還擔(dān)任了監(jiān)制,常需要去審看已經(jīng)完成拍攝的對編素材,于是就能及時掌握到每一位演員的表演完成度。如果這個演員的表演不理想,那么給予其戲份太重的話,就可能會變成一種浪費(fèi)和災(zāi)難。而有的角色,本身戲份并不重,但這個演員的表演十分出色,那我就要考慮將這個角色發(fā)展起來,讓他出彩。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當(dāng)編劇同時做監(jiān)制的時候,就握有這種權(quán)力,真正可以掌握你的角色命運(yùn),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我想讓你死,你就活不到下一集。
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的編劇都能夠去做監(jiān)制。即便一位成熟的編劇,如果沒有受過基本的表演和導(dǎo)演訓(xùn)練,如果沒有制作經(jīng)驗,也是無法完成監(jiān)制工作的。作為監(jiān)制,你必須對各部門創(chuàng)作有專業(yè)性的掌握,才能發(fā)揮有效作用。我是中央戲劇學(xué)院戲劇文學(xué)系畢業(yè)的,戲文系從一年級開始就有表演和導(dǎo)演訓(xùn)練,這也可以說是作為科班出身的編劇的優(yōu)勢吧。我很支持編劇兼任監(jiān)制,至少可以保證你付出心血的劇本不被誤解和糟蹋。
筆者:您剛才說做監(jiān)制可以把握演員的表演完成度,那您對《鍛刀》的演員表演做何評價?
王軍:徐僧、高峰、蒲巴甲、夏銘浩、王鷗、宋撼寰等等這些演員的表演都令我印象深刻。有一場戲,徐僧、高峰兩位演員的節(jié)奏把握非常精確,情緒外化得極好,兩個人滿肚子都是話,但是又都沒有說話,就已經(jīng)把所有的情感都準(zhǔn)確地傳遞給了觀眾。我第一次看到這場戲的對編,當(dāng)場淚奔。他們能夠把劇本文字表述,如此準(zhǔn)確而高級地表現(xiàn)出來,還加入了很多他們自主在現(xiàn)場設(shè)計的外部行為,讓我十分驚艷。
蒲巴甲是一個有非凡靈性,而且異常努力、用功的男演員,他這次堅持自己來配音,一個藏族小伙子學(xué)說漢語也沒幾年,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能做到非常準(zhǔn)確的表達(dá)了,確實了不起的。另外高峰和夏銘浩飾演的這一對國軍特務(wù)所有的對手戲完全是兩位成熟的表演藝術(shù)家在飆戲。每一次寫到他倆的戲,我都特別興奮、愉快!
關(guān)于王鷗,我后來知道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她所扮演的角色江美蘭和徐僧扮演的角色蕭以恒是一對夫妻,我在劇本里設(shè)置了一個細(xì)節(jié),洞房花燭夜,蕭以恒向江美蘭表示:“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會送你一個戒指。”后面的劇本還沒寫出來,王鷗就提醒徐僧:你的每一場戲都要帶著你的戒指,這其實就是在外化人物對愛情的堅貞。聽說之后,我一下便對王鷗刮目相看,能夠意識到通過一個道具來外化角色的內(nèi)心動作,這說明王鷗真是一位非常專業(yè)的演員。現(xiàn)在想來,給王鷗寫的戲份太少太少,非常后悔。
我最后想說說一個容易忽視的角色——獨(dú)眼,他的扮演者宋撼寰也是位非常優(yōu)秀的青年演員。獨(dú)眼這個角色本來是作為一個敘述支點存在的。宋撼寰有一天就跑到我那里要求加戲。我就問他,你有什么想法嗎?他就說,之前別人都是穿皮靴的,可他沒有,能不能為了要一雙皮靴,而產(chǎn)生一些波折呢?我立馬說好!好!這個是真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我是沒有提綱在寫劇本,這個提議讓我一下子就抓住了獨(dú)眼的人物命運(yùn)線啊,使得這個人物一下子就完整了。他有一個好演員的潛質(zhì),能基于編劇的人物設(shè)計,主動去構(gòu)思創(chuàng)作。有時演員也能成就一個劇本,這在我與他的合作中是已經(jīng)證明過了的。

《鍛刀》劇照
主旋律創(chuàng)作必須合乎邏輯
筆者: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多半對戰(zhàn)爭類題材并不感冒,覺得大多都是“手撕鬼子”的主旋律戲碼,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軍:首先得說,“手撕鬼子”不是主旋律,是暗黑者們的反主旋律,是用骯臟低下的手段抹黑抗日戰(zhàn)爭正義性和嚴(yán)肅性的卑劣行為。“手撕鬼子”和“褲襠藏雷”的編劇、導(dǎo)演和出品公司應(yīng)該從影視行業(yè)驅(qū)逐出去,放任這種玩意兒在公共平臺上播放的審查者和電視臺主管官員應(yīng)該被嚴(yán)肅追責(zé)。影視劇社會影響面大,本應(yīng)該承擔(dān)起相應(yīng)的社會責(zé)任,我們的創(chuàng)作者更應(yīng)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藝術(shù)家也都算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從來都是社會的良心,就有責(zé)任去幫助年輕人盡早地確立是非觀念。
話說回來,所謂的“主旋律”是什么?我記得曾經(jīng)有一個關(guān)于“主旋律”的理解挺好的,是說“通過誠實勞動獲得幸福生活的故事,都應(yīng)該成為我們的主旋律”。這個界定也包含了現(xiàn)實題材。我認(rèn)為,長期以來主管主旋律創(chuàng)作的機(jī)構(gòu)部門和從事主旋律創(chuàng)作的人都有一個思維誤區(qū)——他們把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等同于新聞寫作。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文體錯誤。本來,應(yīng)該把它寫成故事性劇本,把它生成一個活生生的姑娘,結(jié)果卻被弄成了新聞,做成了一個雕像,做得再好,也只不過就是報告文學(xué)體罷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核心是人物,人物沒有生活質(zhì)感,沒有煙火氣,是如今所謂的主旋律題材令人厭煩的關(guān)鍵。
筆者:您認(rèn)為戰(zhàn)爭題材作品想要獲得成功有哪些必備的因素呢?
王軍:我覺得,恐怕一時沒法總結(jié)出一個完整的套路來。就我自身的閱讀經(jīng)驗和創(chuàng)作積累而言,老實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比類型化、講究技術(shù)和苛求歷史細(xì)節(jié)更重要。從劇本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戰(zhàn)爭劇如果是以史實為依據(jù)的,那就盡量依靠史實,從真實歷史人物中確立戲劇主要人物,圍繞它來梳理、建立人物關(guān)系。讓人物自己活起來,活在史實之中,活在自己的人物關(guān)系之中,這是符合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
具體創(chuàng)作中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不外乎有兩點:一是違反基本生活邏輯。這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人應(yīng)該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樣的器物那么簡單,為了漂亮偽造民國時期的軍裝,造出了新納粹軍裝這種行為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當(dāng)然,美式小翻領(lǐng)軍裝替代46式軍裝堂而皇之地用在戲里,已經(jīng)成為節(jié)省成本的潮流,我們也不能免俗。我所說的基本生活邏輯,指的是真實生活質(zhì)感的還原度,應(yīng)該力求逼真地表現(xiàn)那個時代中每個個體生存狀態(tài)的真實,主要指人物的具體生活內(nèi)容和情感關(guān)系的真實。有些熱播劇里經(jīng)常會飛揚(yáng)著當(dāng)代的詞匯和當(dāng)代處理情感關(guān)系的方式,這就是脫離現(xiàn)實,也就是違反了基本生活邏輯,當(dāng)然也就很難獲得觀眾的認(rèn)可。
還有一點,就是不遵從情感邏輯的問題。這說明創(chuàng)作者缺少對人物情感世界的體驗。就像表演有發(fā)現(xiàn)、判斷、思考和表現(xiàn)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情感關(guān)系也是有過程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感情本就有起承轉(zhuǎn)合。哪怕僅僅是有相遇、相熟、相知、相愛這樣的節(jié)點,也算是有了完整的體現(xiàn)。《歷史的天空》《我的兄弟叫順溜》就非常好,情感邏輯非常清晰、有力。
從制作角度來說,所謂制作精良,就是要憑良心干活。你是不是花了心思去做,現(xiàn)在連普通觀眾都能看得明白。《鍛刀》制片人曾輝花了半年的時間在剪輯室里做剪輯、調(diào)光調(diào)色和配音等等后期工作,這些都是外人看不到的辛苦,“修和無人見,存心有天知”。只要是做的良心活,自然就有回報。
編劇做導(dǎo)演具有先天優(yōu)勢
筆者:您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這么多劇本,您是如何評價自己的編劇工作的呢?
王軍:我其實算是一個相當(dāng)幸運(yùn)的編劇,從畢業(yè)之后就開始了創(chuàng)作實踐,沒有一部作品胎死腹中,拍攝完成的也都已經(jīng)播出。我不是個產(chǎn)量太高的編劇,因為我是天秤座又屬豬,比較懶,我也沒有什么生活壓力,所以沒有累死累活掙大錢的念頭。很有意思的是,我只有兩三部戲沒上過央視,其他都是在中央一臺或八臺的黃金時段播出,像《金粉世家》《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緝毒先鋒》,等等。這次從《熱血之共赴國難》改名成《鍛刀》,我心里就有點慌,因為我沒上央視的戲幾乎都是兩個字的劇名。萬一中途生變,該怎么辦呢。好在天遂人愿,一切順利。
筆者:您接下來有什么創(chuàng)作計劃?
王軍: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一部自己滿意的大部頭作品,當(dāng)然這幾乎是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夢想。素材已經(jīng)在準(zhǔn)備了,我還希望能親手將它拍出來。
我現(xiàn)在也在籌備下一部作品,而且將自編自導(dǎo)。我認(rèn)為編劇做導(dǎo)演是有先天優(yōu)勢的,導(dǎo)演的工作其實也是在講述故事,只不過是用行為和鏡頭替代了文字而已。如果你連用語言講述故事的基本能力都沒有,憑什么能做個好導(dǎo)演呢?其實,如今風(fēng)頭正勁的很多導(dǎo)演本身就是文學(xué)系畢業(yè)的,刁亦男、蔡尚君、張一白就是我們中戲戲文系的同門師兄,曹保平、薛曉璐是電影學(xué)院文學(xué)系的老師,姜偉導(dǎo)演最初也是做編劇入行,王家衛(wèi)、科波拉也是如此,很多這樣的例子。所以說編劇去做導(dǎo)演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歌德之前,所有的導(dǎo)演工作都是編劇在做。
編劇和導(dǎo)演有很多共通的東西。首先是都要有整體感,有全局觀。所有的人物在戲中所處的位置和人物關(guān)系演變的整個波峰變化,你要有一個整體的把握,最主要的是你要始終保證你的主題貫穿呈現(xiàn),這就是整體感。第二點是連續(xù)畫面思維能力,我所寫的劇本基本上都是連續(xù)畫面,不是文學(xué)本。專業(yè)導(dǎo)演看我的劇本,立馬就能明白這幾乎已經(jīng)是個分鏡頭劇本了,我的劇本換行就是切鏡頭,我從來不會標(biāo)注“特寫”兩個字,但是導(dǎo)演看到“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頭”,他就能明白這是個特寫鏡頭,人物并沒有入畫。我的劇本里從不出現(xiàn)“鏡頭”兩個字,也沒有“左拉右搖”“前推后移”這些詞,只要出現(xiàn)這些描述,那都是業(yè)余選手,編劇愛好者而已。現(xiàn)在似乎有一種風(fēng)氣,當(dāng)過觀眾的,認(rèn)識2000個漢字的,就敢當(dāng)編劇,這很可笑。
一名職業(yè)編劇的養(yǎng)成其實是非常艱難的,編劇所擁有的復(fù)雜的知識結(jié)構(gòu),恐怕在各行業(yè)中都少見。編劇的日常閱讀看上去是不求甚解,樣樣通樣樣松,其實是在儲備建立自己的索引目錄,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按圖索驥,繼續(xù)去追索研究。不小心成為專家的也未必沒有。但是平時沒有這個積累,臨戰(zhàn)就會抓瞎。
《鍛刀》背景里的這段60軍的歷史我是了解的,但我也只是清楚大框架,細(xì)節(jié)卻不甚了了。好在平時有積累,我就能很快從藏書中找到相關(guān)的文字資料。關(guān)于資料支持,我要感謝我的兩位師友,一位是寫《抗日戰(zhàn)爭的細(xì)節(jié)》的魏風(fēng)華先生,另一位是寫《松山戰(zhàn)役筆記》的余戈老師,他們的作品幫助我快速地解決了很多史實細(xì)節(jié)問題,對我構(gòu)建情節(jié)幫助很大,借此也要向他們表示感謝!
最后也要感謝制片人兼總導(dǎo)演曾輝先生,是他的信任,才有了我的這場臨危受命,而且整個過程我們配合得也相當(dāng)默契。他是我多年來合作過的唯一一位從不催劇本的制片人,任何一名編劇都喜歡這樣的制片人。
我很慶幸完成了《鍛刀》的劇本創(chuàng)作,讓我感覺沒有浪費(fèi)自己的2015年。《鍛刀》在10月11日收煞,這是送給我自己最好的生日禮物,哈哈哈。★
(文章編輯自“喜多瑞劇本觀察”微信公號)
責(zé)任編輯:曹舒雅

《鍛刀》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