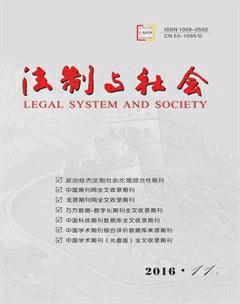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分析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原因
摘 要 造成中國法律信任缺失的原因眾多,除了制度本身的建立健全有所不足外,漫長的中國歷史和傳統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也是不能回避的原因。而研究這些原因的目的乃是探究其中存在的普遍性或規律性,由此發現彌補缺失的可能性。本文分析了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常見表現,并從歷史和文化兩個方面探究了中國法律缺失的諸多原因,并就彌補缺失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 歷史 文化 法律 信任缺失 原因
作者簡介:楊伊玲,黔東南民族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292
對法律缺乏信任也就是對制度缺乏信任,而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乃是人,因此歸根到底其實是對人的不信任。美國學者尤斯拉納就在其著作《信任的道德基礎》中明確表示過對人的信任和對制度(法律)的信任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因此,在討論中國人缺乏對國家法律信任的時候不能僅僅從法律形式、內容或其架構等尋找原因,而需要擴展到與中國人、中國社會相關的更大范圍中,比如歷史和文化。
一、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常見表現
復雜的人情網、嚴重的裙帶關系等是中國社會普遍性缺乏法律信任較為突出和典型的表現。若干年前曾經興起過一陣“北漂”一族回歸的風潮,然而不久之后,這些人中的不少又返回了原本已讓其身心倶疲的北、上、廣。究其原因,這些已經在北、上、廣打拼過的人深感返回家鄉后遭遇的人情關系網之復雜和難纏,相比之下,雖然“北漂”的生活壓力重重,卻相對更加公平和簡單。中國社會之所以人情關系網盛行,除了封建宗族制度的殘余影響,還有“朝中有人好辦事”的實際利益。遇事只要有關系、有熟人,就能跳過繁瑣的中間環節一步到位解決問題。只要身處關系網之中,就能隨時享受既得利益。于是原本沒有關系的人就要想方設法拉關系。只是,少數有“關系”的人享受逾越規矩后的不當得利時,必然就是多數沒有“關系”卻守規矩的人利益受損。而當整個社會中普遍形成了對人情關系的默認時,也就等同于對此類踐踏法律、規則行為的默認。這背后隱藏的深層原因正是法律信任缺失導致的法律權威性、嚴肅性的大打折扣。
二、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歷史原因
(一)宗教
在多數西方國家中,基督教是占統治地位的宗教,這種信仰單一神的宗教中,作為造物主存在的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和人類,也為人類制定了生存和發展的規則,即法律。因此,基督教中的上帝凌駕于所有人和世俗權力之上,故所有世俗之人唯一的信仰就是上帝。由于上帝替人類制定了規則,而法律又等同于上帝的旨意,于是信仰上帝和信任法律之間產生了天然的聯系,這便是宗教影響西方社會法律信任形成的重要原因。
相反,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宗教中出現過與基督教的上帝地位相似的單一神,世俗社會中的君主卻成為了神的代言人,這便“天子”這種稱謂的由來。由于國王或皇帝是“天”的兒子,因此“天子”統治世俗的權力就是“君權神授”,“天子”的命令就成為其他所有被統治者必須服從、不得違抗的“圣旨”。于是一個肉身凡胎的人就擁有了凌駕于整個社會、全體國民之上的統治權力,沒有任何宗教、法律能夠約束和規范他的行為。甚至在某些時候或場合中,“天子”的言語或命令就等同于法律。
不過,雖然被叫作“天子”,這個世俗統治者依然具有所有人類的弱點、缺點。同時,由于存在這樣一個超越其他所有人的特殊權力擁有者,原本應當作為整個社會行為規范標準的法律就不再具有標桿、準繩的本質屬性,反而被異化成了人類統治者的工具。于是法律就出現了不確定性,可以因為君主意志的變更而被隨意地修改。
(二)經濟類型
海洋民族的屬性讓多數西方國家在歷史發展早期階段就開始了以貿易維持生存的生產生活模式,相對匱乏的資源只有在不斷加快的交換中才能滿足更多人的需要,而這導致了商品經濟的迅速萌芽和發展。公平交易促進了契約精神的誕生,通過制定規則并且人人遵守成為實現交易順利進行的保障。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發展大背景下,法律在保障商品交換、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維護了個體、群體的利益,成為人們價值訴求的共同體現。當法律的保障作用、規范作用、管理作用等逐步覆蓋到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所有層面時,個體、群體的人產生對法律的信任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而作為大陸民族的中國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開始了世界上最早的農耕生活,小農經濟最典型的特點就是自給自足,于是有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之說。能夠依靠自我耕作就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商品交換就只能成為一種輔助而非必須。同時,以農業立國的歷代封建王朝受到儒家思想影響還形成了“仕、農、工、商”的認識偏見,將代表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的“商”排到了“下九流”的位置。始終孱弱的商品經濟不僅無法讓商人群體在社會中獲得較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好的發展機會,也不能使其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凝聚足夠的力量與封建貴族階層相抗衡以維護自身權益。這就沒有條件凸顯法律對于人們共同價值追求所具有的維護、管理、規范等作用,也就不存在產生法律信任的社會土壤。
三、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文化原因
(一)對待權力的傳統觀念
“君權神授”讓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對世俗的權力充滿敬畏甚至仰慕,諸如“官大一級壓死人”等民間俗語就是普通群眾對于權力在社會中具有作用的形象化闡釋。兩三千年封建王朝的統治過程中,法律基本只是以君主的統治工具的形式而存在。至于“刑不上大夫”之類充滿特權階級意識的規則制定則更讓整個中國社會形成了根深蒂固以人治替代法治、對法律缺乏尊重和信任的觀念。即使是在現代,當人們談論起“公務員”這一職業時,言語中依然或多或少帶了些許艷羨的語氣。這當中除了包含對社會公職人員優厚的薪酬待遇的假想外,更多的還是對政府公權庇蔭下個體權力增長的臆測。至于近年來在打“老虎”、拍“蒼蠅”行動中不斷被處理的大小官員,這些人經受過多年黨紀國法的教育熏陶,然而事到臨頭依然倒向了腐敗,不能不說還是“權大于法”的封建意識的殘余作祟。
(二)社會關系調整手段
儒家思想在兩千年時間里是封建君主統治國家奉行的主要準則,而這一思想中,法律被置于邊緣化地位。《論語》中有“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竟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孔子的弟子子路某次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指治理國家的先后順序。孔子的回答竟然是以“正名”為先,并且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君、臣、父、子”的順序安排充分說明了封建時期“三綱五常”的宗法制度對于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的決定性影響,儒家理論中不僅沒有絲毫平等思想、自由意志的影子,反而處處充滿了嚴苛的等級觀念和下級對上級無條件服從的要求。同樣,將“禮樂”放在“刑罰”之前,也突出了禮樂所代表的道德優先于法律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從這位被歷代君主奉為古圣先賢之人的論斷中已經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社會關系的調整手段只有倫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不大。
還有一個比較具有典型性的古代中國社會關系形式——家族也具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稍具規模的家族總會選擇一位族長管理整個族群的事務,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承擔起裁判和處理涉及家族內部的人與事。于是,每當族群中出現糾紛需要決斷時,族群中人不會首先想到尋求政府管理單位的幫助,而是見族長,再到家族祠堂中審理。從這一點看,封建中國的家族就相當于一個個小朝廷,而君王如同整個國家的大家長,維系和規范這種背景下的社會關系依賴的只有倫理道德、人情世故。久而久之,中國人思想中預留給法律的信任也就越來越少。
(三)二元狀態中的法律文化
由于傳統文化將倫理道德作為維系和管理社會關系的主要途徑,而統治階級為了使其運用更加富于成效,因而必須動用一切手段確保這一系統的運轉正常,于是將法律放在了倫理對立面,形成了法律和倫理對立的二元狀態下的傳統法律文化。這也就造成了千百年來中國人習慣將“法”與“罰”對等看待的現象。
比如經、史、子、集等古代典籍中涉及到與法相關的論述中就明確地將“法”等同于“刑”:《爾雅·釋詁》中有“刑,法也”;《管子·心術》中有“殺戮禁誅謂之法”。很明顯,殺、戮、禁、誅都是懲罰的手段,且是相對殘酷、冷血的處罰過程和結果。加之歷代封建君主中不乏青睞暴虐刑罰之人,動輒施以“刖刑”等殘害犯人身體或是以“墨刑”等在人身體和精神上烙上永久的恥辱印記,故整個古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于法律形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基本態度和心理陰影。
但反觀西方法律信任形成歷史不難發現,法律最初開始形成時,“保護”的成份遠大于“懲罰”。比如早在古希臘時期的法律就被視作為人們不侵犯對方權利的保障。而西方社會倍加推崇的契約精神也是在法律框架內以契約形式保護簽約雙方既定權利的具體形式之一。
正是由于中國古代封建統治階級將法律本質上同時具有的保護與懲罰的雙重屬性人為異化,只突出和強調其中有利于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被刻意扭曲的法律文化中,人們看不到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效用,也就無法對統治階級手中的法律產生信任。
四、解決我國法律信任缺失的舉措
漫長的歷史發展、獨特的傳統文化和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等諸多原因造成了古代中國不具備培育國民法律信任的基礎,也就為現代中國彌補缺失的法律信任造成了相當巨大的阻礙。信任的瓦解需要時間,信任的建立更加離不開時間的積淀。因此,持之以恒地宣傳、培育法治思想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彌補中國社會既有的法律信任缺失的最重要舉措之一。
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建設法治中國的宣傳力度,并且隨著《憲法》、《刑法》、《民法》等基本法、法規條例等的修正以及更多專門法的出臺,法律在中國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正在得到越來越強的鞏固和凸顯。而在國家、政府、各級管理單位及媒體的不斷宣傳下,“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依法辦事”等尊重法律、信任法律的氛圍正在各地方、各區域形成。
同時,隨著國家大力反腐倡廉,一大批“老虎”、“蒼蠅”的相繼落網也讓曾經在中國社會完全不被約束的人治權力逐漸被關進制度的籠子。當越來越多特權階層被消滅、人情關系網被撕破的時候,普通民眾不僅可以見證法治中國建設的成效,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得以讓長久以來嚴重缺失的法律信任開始逐漸被彌補和建立。
五、結語
中國社會缺乏法律信任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且由于時間累積的漫長導致彌補缺失的困難。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其實也是彌補長久以來法律信任缺失的契機。只要堅持依法執政、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現代中國社會必然能夠形成普遍性的法律信任,實現從人治到全面法治的最終結果。
參考文獻:
[1]曾林.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信任危機與重塑——基于法治的維度.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6).
[2]高國梁.法治思維的承載主體與實現路徑分析.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
[3]黃金蘭.我國法律信任培育的基本路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
[4]姜述弢.構建法律信任: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社會矛盾之化解.學術交流.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