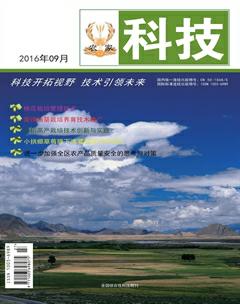理性選擇視角下資源型農村農民的個體行動研究
楊麗新 王振昭 張芬芳
摘要:農民是農村的主體,農民的個體行動更是深刻的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結構及發展走向。本文是在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視角下,以河南省澠池縣曹窯村為例,研究農民的個體行動,旨在探究農民個體行動背后所蘊含的理性思維和理性原則,進一步分析農民個體行動所引起的群體分化和社會結構性變化,并對農村的發展進行了一定的反思。
關鍵詞:個體行動;理性選擇;理性行動
一、資源型農村研究的相關文獻回顧
資源型農村作為農村研究的重要內容,大多數研究者在對資源型農村的研究分析中大都先對資源型農村進行了概念的界定,如宋鈺在《資源型農村轉型發展的路型分析》中認為資源型農村是指因自然資源的開采而興起和發展壯大,并且資源型農業在產業結構和農民的收入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農村;劉倩,孫世芳,張國春在《資源型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一以河北省平山縣溫塘鎮北馬象村為例》中認為“資源型農村是指具有豐富礦產、水力等自然資源或電力、人力等其他資源的農村”;苗娜妮在《資源型農村轉型發展的路徑探究——以山西省澤州縣興王莊村為例》中指出“資源型農村特指地下礦產資源豐富且集體收入依靠資源開采、加工為主的農村”。
資源型農村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發展。從已有的研究狀況分析來看,大多數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資源型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以及農村如何順利轉型上,從經濟學方面(如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效益低下等)、政策制度方面(如產權制度、利益分配等)、可持續發展方面、城鎮轉型方面等對當前我國資源豐富的城市或農村在發展方面遇到的瓶頸進行分析和提出建議,多把側重點放在應用性研究方面,針對資源型農村的現狀及問題解決提出了對策,如趙康杰在《資源型地區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創新研究》中針對產權制度對資源型農村治理的影響提出了產權制度改革和調整利益分配的對策
以上研究都是站在宏觀層次對資源型農村的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議或措施,但美中不足的是研究者多站在理論構建上對資源型農村的發展提出建議,采取的是社會學史中的整體主義解釋方法,即側重于對不同系統的同一行為進行樣本分析或是對一個系統在某個特定時期內的不同行為進行分析,因而在某些方面忽視了系統的內部層次,在個體行動層次缺乏一定的解釋力。本文將從四類農民的個體視角分析支撐其行為的理性因素,這些社會行動又是怎樣影響社會結構的變化,進而探究以此為代表性的整體性資源型農村的發展問題。
二、研究設計
1.研究資料
曹窯村屬于典型的資源型農村,其位于豫西地區,北依群山、黃河,南部地形以丘陵為主,村中共計27戶106人,耕地106.7畝,村落以河谷為界,北面為村居,房屋格局從西到東,由上至下整體呈四階梯狀分布。南坡則是階梯狀麥田,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雖然本村范圍內礦產已經開采近10年,但是村民并無法參與其中,基本上都被外地人承包經營,唯一能夠直接為村民帶來經濟利益的就是耕地被占用獲取的補償款(一畝耕地約賠償2.5萬元人民幣)。
2.研究視角
本文將以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為著力點,深入分析農民的理性行動以及個體行動所一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由行動系統、行動結構、行動權利以及社會最優狀態構成四個部分組成。科氏認為行動者的社會行動是依據理性考量而進行的行動,這些行動一般都是以最小的成本作為獲取更大利益的前提。本文認為農民對于自己發展方向的選擇是建立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之上,他們需要考慮勞力和資源的配置,收益的風險性,傳統力量的限制等綜合因素。因此農民是屬于社會中的“理性人”,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行動目標,是處于社會互動、社會關系中的能動選擇的主體,獲取最大利益的主體,此處的利益除了經濟利益還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等綜合利益。同時農民的個體行動也必將引起宏觀上的社會結構、社會狀態的變化。
三、個體理性行動下的四類村民群體的形成
科氏的理性選擇理論以個體行動著力點,以宏觀的社會結構為研究目標,他采取的是以個人理性行動為基礎而進行的多層次解釋一個體如何展開理性行動獲取最大效益,這些眾多的個體理性行為又是如何形成規范繼而再升華為系統和秩序的。曹窯村由單一的社會狀態形成了高低有序的由四類群體組成的社會結構,也是因為個體的理性行動而形成的結果。在2006年之前,村民之間是沒有這種等級之分的。
四、個體理性行動下的社會結構性變化
單單針對曹窯村這一個小村莊而討論社會變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適用的,但是其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劇烈變化。曹窯村已經和傳統的農業經濟徹底分離,雖然近期資源有枯竭的趨勢,但卻并不影響其社會格局的變遷,這也是資源型社區發展過程中一個必須經歷的階段。當整體的個體都在發生變化時,整體的變化也必將發生,且以更劇烈的方式影響到個體的發展。曹窯村村民村民所形成的四類村民格局也都是個體在面臨社會環境變化時所采取的自己認為符合理性的行動所造成的
五、研究結論與反思
曹窯村的礦產已經處于枯竭階段,其發展無疑也是到了瓶頸期,如果不進行及時的調整其很有可能會經歷較長的迷茫期和停滯期,生存理性適用于傳統的小農社會,經濟理性適用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之后的農業經濟,但單一的經濟理性已經不適用于資源枯竭后的資源型農村社區了,農民需要進一步提升自己理性思維,使自己的個體理性符合團體理性,自己的理性行動成為社會上通行的理性行為,這是之前的“理性行動”所欠缺的。曹窯村的村民首先需要的是從實現自我的低層次的目標升華自己的價值追求,實現“自我”與“超我”的良性結合,將自我的發展與村莊整體的發展結合起來,實現村內資源的整合,如恢復耕地及生態環境、重視教育提升自我內涵、實行高度的土地流轉、利用資金發展集體經濟等,探尋適合本村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