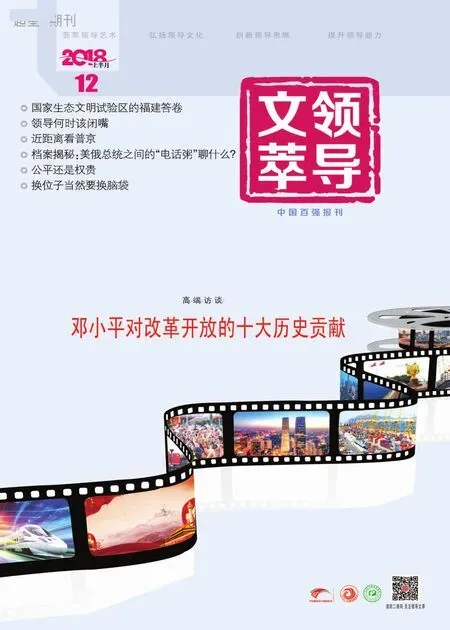如何應對美國的四種戰略
周鑫宇
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是應對中國作為下一個超級大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其中包括采取自強、羈絆、改制、防范等四大戰略手段。不管美國大選結果如何,新總統對華政策的差異也就是在這些戰略上的輕重緩急不一樣而已。無論如何,對這四大戰略,中國應該有明確的應對之方。
第一,對于美國的“自強”,中國總體應采取觀望和鼓勵姿態。美國當前試圖通過國內改革和創新實現新一輪的發展,將此作為應對中國崛起的積極出路。美國的戰略精力如果放在國內問題上,繼續對自身的競爭能力保持自信,有利于遏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把自身的問題歸咎于中國,不對中美關系產生錯誤的判斷。因而中國對此應當在總體上鼓勵和支持,并利用美國的發展機會促進中國的利益。在此過程中中美可能有微觀層面的競爭關系,但在宏觀層面并非絕對你得我失、非此即彼的零和關系。此外,美國無論是在國內的改革創新,還是在國外的戰略收縮、調整、“再平衡”上,都面臨很多挑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處比比皆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會對中國產生戰略需要。中國有主動作為的空間。
第二,對于美國的“羈絆”,中國應當劃出核心利益紅線,同時以我為主、加快發展。在這一戰略手段下,美國會利用各種機會攪動中國的內外矛盾,尤其是威脅中國的政治安全、領土主權完整。中國對此應當有三點認識:首先是對最核心的安全利益劃出紅線,不要讓美國誤判中國的底線。由于美國這一戰略本質是干擾性的,而不是根本對抗性的,所以美國會依據中國的反應做出評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避免引發全局性的戰略崩盤。當然,雙方的核心利益底線要經過反復互動,才能達成較為準確的理解和默契。因而中國并不宜把核心國家利益的紅線劃得太廣、太虛,應做到言行一致,傳遞準確信息。其次是保持戰略耐心。中國應該接受以下事實:美國在找不到遏制中國崛起根本辦法的情況下,將長期對中國實行戰術性的羈絆,可以預見的未來都不會停止。只有隨著戰略態勢的變化,中美創建出新的關系模式,美國的干擾動作才有可能改變。這取決于雙方的努力和歷史的機遇,中國應做充分的心理準備,調整不恰當的心理預期,避免急躁和虛驕。最后,中國應當明確認識到,美國的干擾不能從根本上阻礙中國的崛起。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最終要靠發展來解決。中國甚至應把美國的長期干擾視作一種可轉化的逆境。美國在一些問題上的壓力,可以促使中國加快改革、彌補缺陷,推動中國內政外交走向成熟。反之,將問題簡單歸咎于美國的挑唆,產生不冷靜的排外情緒,最終會自亂心神、延緩改革,反而實現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第三,對于美國的“改制”,中國應當注意其中的風險,在國際制度改革問題上和美國既開展合作,又進行博弈,并用博弈來促進合作。中國已經比以前更加清晰地提出了對新型國際秩序的看法,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創設補充性的國際制度。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和美國開展制度對話、制度合作和適度的制度競爭。應該看到,美國和中國從根本上都依賴和捍衛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短期內,中國應當進一步加強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加強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合作與交融,并研究美國推動的新規則變化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更應當關注如何與美國談判、磨合、協調,建立一套相互容納、合作共贏的新國際秩序。總的來看,美國不可能建立一套排斥中國的規則,中國也不可能建立一套排斥美國的規則,這是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賴的大勢所趨。
第四,對于美國的“防范”,中國要從戰略高度清醒認識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戰略總體是防御性的,但有可能轉為對抗性的。為避免全面對抗的出現,就要把加強政治互信提升到最高戰略層面。同時,中國也應當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如果在某種條件下美國轉向全面對抗中國,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應當提早做出預案。為保證最壞情況下能夠對美反制,中國需要準備一些基本戰略條件:可以確保對美構成關鍵威懾的軍事手段、能夠轉化為同盟體系的外交支點、能夠突破美國海上和陸上封鎖的交通通道、確保國內政治在對抗的高壓下保持穩定等。從目前來看,為了不給美國傳遞誤導性的信息,中國在這個方向上的投入和準備應當是克制的。可以積極建設一些軍民兩用的項目,有意識地開發一些可用于發展目的,同時又可隨時向對抗目的轉化的資源,如開發關鍵性技術、建立更加緊密的外交關系網絡、建設國際海陸交通基礎設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