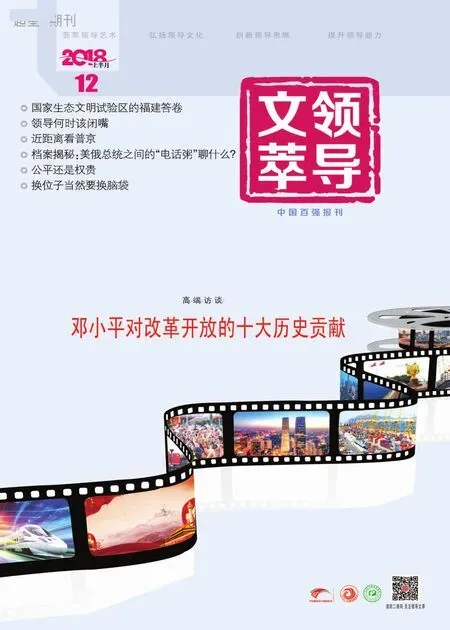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散吏”困境
佚名
7月6日,北京市政府網站公布《北京市“十三五”時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北京市將落實“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然而,一邊是要延遲退休,另一邊卻相反,是要提前離崗。據媒體報道,湖南岳陽、婁底、永州等地一些年齡并不算大的“局辦委”或鄉鎮“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員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務員50歲(或50多歲)以上可退居二線、享受比在職時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請“早退”,成為“休而不退”的“散吏”。
“休而不退”即提前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是在編公務員,占著編制、拿著薪資,享受著高額補貼。就是官場常說的“退居二線”。這些干部離開領導崗后,要等到退休年齡才能正式辦理退休手續。
“退居二線”即機關事業單位領導干部臨近退休達到規定年齡離崗閑居而待遇不變的制度,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是對干部隊伍實行“能下”所采取的方式。在領導崗,叫一線,退下來,稱作到二線。
類似湖南這種給科級干部提半級,鼓勵“老人”退下來的政策,近年來在全國都有出現。
多位官員承認,官員一到年齡退居二線是常態化的制度安排,對這類官員管理長期以來處于失范的狀況:多數在編官員還遠未到達退休年齡,就處于離崗休息狀態;不上班,卻照常財政供養,直至退休。
不過現在,黨內實施幾十年、早已習以為常的“退居二線”稱呼及做法,恐將淡出歷史舞臺。
資源浪費
大約八九年前,時年五十多歲、在宣傳部門工作的慕毅飛接到轉任黨校教員的通知,這是一個新職,黨校的工作比在宣傳部門要清閑很多。身為官場中人,慕自然明白,自己的被“退居二線”與年齡有關。
按慕毅飛的說法,在此后漫長的“休而不退”的時間里,他一直吃著財政飯,卻過著不用每天按時簽到上班的“散吏”生活。在慕所在的這個常住人口為一百多萬的縣級市里,像他這樣的退線干部還有二三百人,慕并不是獨一個享受這種待遇的官員,很多人過著和他一樣的舒服日子。
“退居二線是全國性的通病。”一位體制內的官員對此早已見怪不怪,對退居二線的官員,有的單位不要考勤,但年底考核照樣優秀;有的在家練書法;有的在工廠里幫忙搞“三產”;有的不知道整天干什么,沒人過問。“如果沒有什么事情觸犯法律或者被人舉報的話,當個太平官就太舒服了,不用干什么活。”
但上述官員慨嘆之余,也直言這是對干部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想想吧,他們才五十出頭,大多還精力旺盛,想法很多,僅因為所謂的到齡,就這樣被晾在一邊。”類似的官員還有多少,盡管迄今沒有人做過精確統計,但粗略算來,數目驚人。
江西省革命老區吉安地區的一個縣,在2013年時,該縣就有科級干部799人,231人到退居二線年齡,占28.9%。而江蘇一個人口為40多萬的縣級市,退線干部有100多人,該市市委組織部一官員告訴記者,退線干部人數很難精確計算,內陸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干部編制不一,很難以人口基數比例推測,但以全國目前的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劃論,幾十萬人應該有的。
這么多的退線官員被閑置,是何等的浪費!
退線規范亦難
今年4月,浙江省委已將中央對退線干部的管理精神和省領導的要求逐級下達到市,要求各縣區制定相應規定,各地級市目前都在醞釀研究中。最近,蘇州一個縣級市在江蘇率先出臺了一項對退居二線干部管理的規定,要求退線干部還是要正常上班,遵守機關作息制度。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情況,注重發揮退線干部的特長,可以協助某一個領導工作,或者有些可以參加單位某項重要課題項目的研究。
“中央老早就有這個要求了,不能搞年齡層層遞減,不能搞‘一刀切’,要‘老中青’相結合,要發揮各個年齡段干部的積極性。”一位省級組織部官員說,只是下面執行走樣走偏了。
然而,賦閑的退線官是否就此退出歷史舞臺,一些學者和官員認為不容樂觀。
在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慶樂看來,退線或冗員的出現都是因公務員編制管理的軟約束。“編制約束不僅是數量約束,也有職位設置的約束,但現實中吃空餉、超編的情況大量存在。”從根本上說,是財政預算的軟約束所致。過去你在不在崗,都是財政拿錢,沒有實質區別。各級人代會審議也不會涉及某個崗位為何雇傭5個人而不是3個人這樣的問題,只要人大不專項審議,這個問題就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