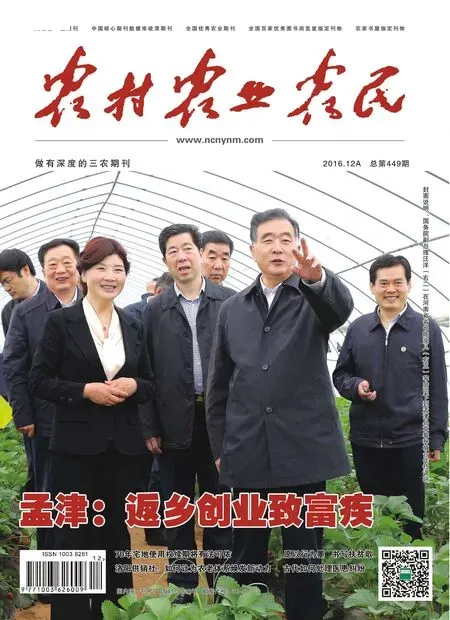松毛嶺旌旗猶在子弟兵忠魂未遠
祁 雷 朱曉楓
松毛嶺旌旗猶在子弟兵忠魂未遠
祁 雷 朱曉楓
“當年紅軍就是在這里打響了長征前在閩最后一戰,并成功開始戰略大轉移。”福建龍巖市長汀縣黨史專家鐘鳴,指著綿延的松毛嶺,說起當年那場激烈戰事。
松毛嶺是長汀縣境內東南部的一座大山,從南至北橫貫40多公里,從東至西寬15公里,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1934年9月下旬,著名的松毛嶺戰役就在這崇山峻嶺之間打響。3萬紅軍經過七天七夜慘烈戰斗,付出近萬人傷亡代價,抗擊國民黨軍隊7萬人的兇猛進攻,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戰斗結束次日,紅九軍團這支剛走下火線的英勇鐵軍,在長汀縣南山鎮鐘屋村(舊名)觀壽公祠前召開誓師大會后,邁出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步。
《西行漫記》中這樣寫道:“從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陜北道路的盡頭為止……”其中的“福建的最遠的地方”,就是鐘屋村。長征開始后,近3萬名福建兒女踏上征途,約占參加長征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人數的三分之一。
三萬紅軍血戰七天抗敵七萬
如今,在松毛嶺東南面的山腳下,有一座叫文坊(舊名溫坊)的村莊,距村口不遠,一座新中國成立后修建的“溫坊戰斗革命烈士墓”矗立山間。每年清明,當地政府都會組織村民聚集在這里,點燃香火,祭奠這些為革命犧牲的烈士。
據記載,在革命年代,當時僅25戶116人的溫坊村,90%以上的青壯年男女參加了紅軍、游擊隊等。不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壯烈犧牲了。
1934年9月1日晚,松毛嶺保衛戰的前奏——溫坊戰斗打響。溫坊村與松毛嶺主峰白葉楊嶺遙遙相對,是后來紅軍阻擊國民黨軍進攻的前哨陣地。
長汀縣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介紹,當時駐守溫坊村的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運動戰”戰術估計不足,事前沒有作嚴密布防和警戒,被打得措手不及。“等到我軍打進溫坊村里,敵人還在睡大覺!”康模生說。史料記載,整個溫坊戰斗,我軍全殲敵人一個旅和一個團,繳獲槍1600余支、子彈44萬多發。
溫坊戰斗之后,真正的惡戰爆發。
在中復村(鐘屋村現名)松毛嶺舊319國道護道班旁的半山腰上,矗立著一座“松毛嶺戰斗烈士紀念碑”,上面刻有開國上將楊成武的題字。當地老人說,碑底下葬有松毛嶺戰役中犧牲的數千烈士遺骨。
驅車前行,在崇山峻嶺間,不時能看到一座座無名烈士墓和當年修筑的土木工事,似乎在述說著那場戰斗的慘烈。沿著一條小徑,我們終于到達松毛嶺山頂。登高望遠,當地黨史專家向我們實地解說了當年的戰斗。
1934年9月23日上午,紅軍長征前在閩最后一戰打響。據康模生介紹,當時敵東路軍3個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紅軍松毛嶺陣地發起猛烈進攻,紅軍和長汀地方武裝與敵人展開激烈戰斗。29日下午2時,紅軍左側高地被敵奪占,形勢十分嚴峻。指揮部當機立斷,趁敵人立足未穩,迅速派出援軍展開反沖鋒,重新奪回高地。

82年前,紅軍長征前在閩最后一戰——松毛嶺戰役,就在這崇山峻嶺之間打響

位于福建長汀縣中復村內的紅軍橋(1934年紅軍征兵處舊址)
這是悲壯的一戰。《長汀縣志》這樣記載松毛嶺戰役:“是役雙方死傷慘重,尸遍山野,戰事之劇,空前未有。”據統計,大戰給紅軍造成近萬人的傷亡。當地老人回憶,戰斗結束半個多月后,松毛嶺上空仍血腥味不減,黑壓壓的綠頭蒼蠅云集在沾滿血跡的松針毛尖上,把松枝都壓斷了。
這更是關鍵的一戰。此役,中央紅軍和閩西地方武裝以3萬人的兵力,血戰七天七夜,抗擊國民黨軍隊7萬兵力的進攻,為中央主力紅軍實施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老農先后送6個兒子上戰場
“救國不分男女”——在中復村的紅軍橋上,還留有當年的征兵標語,這里就是當年紅軍的征兵處。
在橋上的一根木梁上,還清晰保留著一條10多厘米長的刻度線,離地約1.5米。“達到這個高度,意味著人就能夠背起上刺刀的步槍了。”長汀縣南山鎮文化站站長賴富家說。
紅軍在當地的群眾基礎打得非常牢,征兵工作一向進展順利。1934年底,中央蘇區臨時中央政府提出開展“紅五月突擊擴紅運動”,福建蘇維埃政府大力動員,僅半年時間,當地就有7000多人參軍。
當地有一位名叫羅云然的貧苦農民,先后將6個兒子送上了戰場。“為了支援紅軍,老人將老大、老二、老三送上了前線,不幸的是,幾個兒子先后在幾次反‘圍剿’戰斗中都犧牲了。”賴富家說。
松毛嶺保衛戰打響后,紅軍傷亡非常大,急需補充兵員。羅云然得知后,二話不說,帶著剩下的3個兒子來到征兵處,要送孩子們參加紅軍。得知羅云然的情況,征兵的紅軍干部勸他留下小兒子在身邊,被老人一口回絕:“沒有紅軍、沒有蘇維埃,就沒有我們。我和孩子們商量好了,就是斷了香火,也要跟著紅軍干革命!”后來,這3個兒子也都為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據統計,有近3萬名福建人民子弟兵參加了長征,他們來自福建的近30個縣市,其中以閩西的長汀、上杭、寧化、永定、連城、建寧等地為最多。
“家家無門板,戶戶無閑人”。男人們在前線幫紅軍挖戰壕,后方的女人們也沒有閑下來。78歲老黨員鐘家興的母親蔡招生,是當年鐘屋村婦女赤衛隊的隊員。鐘家興老人回憶說,松毛嶺保衛戰爆發后,他母親就組織了一支女子擔架隊,搶運紅軍傷員。
蔡招生和堂侄媳還拆了家里的門板,做成救護擔架,冒著槍林彈雨將紅軍傷員抬下山。“戰場在山上,野戰醫院在村里,中間至少有六七里地,全是山路,加上要躲避敵人的轟炸,一個來回下來都要三四個小時。”鐘家興至今還記得母親的故事。
為了保證反“圍剿”戰斗和戰略轉移期間的物資供給,福建各蘇區成為為中央紅軍提供給養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長汀人民積極籌集糧食、斗笠、被服等軍需物資,僅1931年到1934年,長汀就征集了逾3萬擔糧食。群眾都表示,寧愿自己節省一點,也要讓紅軍吃飽飯,打勝仗。
為了20年前一句諾言
“誰活著回來,誰就要為其他兄弟的父母盡孝!”這是82年前,鐘根基等同村17名熱血青年參軍時,在紅軍橋上跪地起誓時的誓言。
然而,在殘酷的戰爭中,活下來的只有鐘根基一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后,鐘根基先后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已是正團級軍官。
為了兌現20年前的諾言,鐘根基最終選擇離開心愛的部隊,回到了中復村老家。回村后,他婉拒了組織的工作安排,堅決要求留在村里務農。有的人說他“傻”,后來大家才明白,他這么做是為了更好地照顧死去的16個兄弟的家人。
此后,鐘根基除了經常去看望這些烈士的遺屬外,只要哪個兄弟的父母去世,他都會去做孝子,幫忙入殮扛喪。“我能活著幫戰友盡孝,就是最大的幸福。”鐘根基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鐘根基終身未娶,1960年,他收養了兩個失去父母的女嬰,含辛茹苦將其撫養成人。20世紀末,老人離世前給養女留下遺言:“我死后,讓我把軍功章全部帶走,這是我們17個兄弟用命換來的,我要還給他們!”烈士后代憶當年:村口哭送丈夫結果竟成永別
“若要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在南山鎮長窠頭村鐘宜龍家的門口,一副對聯映入眼簾。
87歲的鐘宜龍老人是烈士后代,親生父母在他出生后沒多久便被團匪殺害,后來被當地婦女游擊隊隊長涂從孜收養。回憶起養母,鐘宜龍充滿了自豪:“她是很堅強的人。”
長窠頭村位于長汀與連城交界的松毛嶺山腳下,松毛嶺戰役打響后,涂從孜積極指揮當地婦女游擊隊,暗中給紅軍輸送了很多物資。“我當時還小,經常深夜還看到她在縫送給紅軍的布鞋。”
1934年9月30日,在福建的紅軍兵分兩路,開始了戰略大轉移。涂從孜趕去送丈夫鐘大廷時,大部隊已經出發了,她手拿布鞋,一邊追一邊哭喊著丈夫的名字,終于在村口的橋上追上了丈夫。不曾想,這一面竟成了永別。
養母的革命精神和情懷對鐘宜龍影響至深,這么多年來,他對紅色精神的堅持和傳播從未懈怠。
1951年,當地發生了一場大火,鐘宜龍震驚地看到,山上漫山遍野都是骨骸。后來證實,這些正是在松毛嶺戰役中犧牲的烈士遺骸。
“要讓烈士入土為安!”此后的兩年里,在當地黨委、政府的帶領下,鐘宜龍和村民一道,將散落在山間的1000多位紅軍烈士的遺骸一塊塊拾回,安葬在隘頭崠,并立起了一座兩米多高的無名烈士墓碑。
走出鐘宜龍家,不遠處有一片長滿青草的低洼地,當地村民稱之為青草湖。在松毛嶺戰役中,許多傷重不治的傷員就埋葬在此。
1993年,當地興建水泥廠時,在青草湖又發現大量烈士遺骸,鐘宜龍得知消息后,叮囑在村里的兒子鐘紹錦積極協助當地政府,妥善處理好這些遺骸。每年清明前后,鐘宜龍和村里的紅軍后代都會參加這些英烈的公祭活動,幾十年來從未間斷。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鐘宜龍自掏腰包,在家里辦起了“紅色家庭展”,希望教育更多的后人。筆者注意到,墻邊的木板上,張貼著有關紅軍的文字和圖片;廳內的桌面上,放著長窠頭村革命烈士調查表……
“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紀念革命先烈,也讓下一代人更好地銘記歷史,傳承這份紅色精神。”鐘宜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