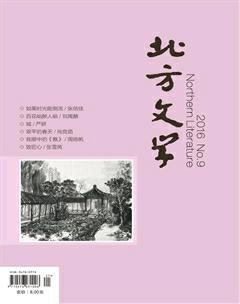由《蘇知縣羅衫再合》情節重構看馮夢龍教化意識
馬琳娜
摘要:《蘇知縣羅衫再合》是 警世通言》中的一篇作品,其題材來源于前代的小說、戲曲。馮夢龍在改寫中融入了鮮明的道德教化意識,即借助通俗文學的形式,以“情教”的方式教育讀者,挽救世風,這主要體現在小說入話的設置、因果報應的模式以及奇巧情節的構筑等方面。改寫后的小說既有明代社會文化的烙印,又體現了馮夢龍獨特的文藝觀。
關鍵詞:《蘇知縣羅衫再合》;馮夢龍;“三言”;教化意識
馮夢龍既是一位通俗文學的大家,又是一位個性鮮明的思想家。他極端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認為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也就是說,文藝作品要通過故事和形象表現作者的意志、思想和情感,而達到感化和教育讀者的目的。要求小說“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2]。所以他這樣解釋三部白話小說的書名:“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3]將倫理意識注入“三言”之中,借通俗小說扭轉人心,挽救世風。“三言”內容豐富,其中一部分故事在前代已有相同或類似的題材表現,并非馮夢龍首創,但他的改寫又是一種文本重構,新舊故事的對比可以看出馮氏獨特的文藝觀念,本文試以《蘇知縣羅衫再合》(以下簡稱《蘇知縣》)這篇小說為例對此做具體分析。
《蘇知縣》見于《警世通言》卷十一,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河北涿州的進士蘇云被任命為浙江蘭溪縣大尹,攜妻鄭氏赴任的途中遭遇船底漏水,誤上江洋大盜徐能的賊船,被徐能捆綁扔進水里。鄭氏逃至一尼庵,生下一子,被迫將孩子棄于路口,恰巧被徐能拾得收為義子。孩子長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懲處了兇手,一家團聚。我們發現,這種歹徒殺人占妻,最終兒子為父報仇的故事在古代戲曲小說中是比較常見的,早在《太平廣記》的《崔尉子》(卷一百二十一)和《李文敏》(卷一百二十八)[4]等篇中就有相關的描寫,元代張國賓的雜劇《合汗衫》又將這種模式搬演到了戲劇舞臺上。可見在馮夢龍小說產生以前,該題材已有較為充分的表現,《蘇知縣》的結尾也說道:“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可推測他的故事應該是根據民間的說唱藝術加工改編而成。在情節大體相同的前提下,馮夢龍的改寫和重構比較明顯地體現了他意存教化、勸懲世人的文藝觀。
一、入話——教化立場的體現
《蘇知縣》的入話寫的是李生的故事。最初李生讀到一首描寫“酒色財氣”短處的《西江月》,頗不以為然,認為“人生在世,酒色財氣四者脫離不得”。恍惚之中,遇見四位女子前來相就,一問方知她們就是酒、色、財、氣。為爭與李生相好,四位皆言己之長,揭他人之短,乃至打成一團。李生驚醒,才知是夢,終于覺悟,原來“酒色財氣”各有其短,不可沉迷,而其中又以“財色”二件更易惹出禍端。在此基礎上展開了蘇云一家悲歡離合的故事,“今日說一樁異聞,單為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后來悲歡離合,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說時驚破奸人膽,話出傷殘義士心。”
本篇的入話在“財色”二字上做文章,蘊含了節制欲望的主題。李生在夢醒之后方悟出“飲酒不醉最為高,好色不亂乃英豪,無義之財君莫取,忍氣饒人禍自消。”“雖說酒色財氣一般有過,……無如財色二字害事。”明確地告誡世人在處理美酒、美色、金錢、意氣等相關問題時不可以隨心所欲、恣意妄為,一定要適度而有所節制,這在當時社會是很有教化作用的。馮夢龍曾說:“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開清凈方便法門,能使頑夫倀子,積迷頓悟,此與高僧悟不何異。”[5]他認為小說家有“勸人為善”的責任,勸誡內容包括重視友情、仗義輕財、節制欲望等等,這一觀念不僅體現在小說正文中,在開篇入話處甚至表現得更為明顯,因為不是故事的主體,故而可以較為自由地直接議論,宣揚自己的道德主張。馮夢龍借助“入話”這一特殊的形式,提出了“節制欲望”的要求,表達了唐傳奇和雜劇同題材作品所沒有涉及的主題。
“三言”中的“入話”常常在補充正文的基礎上,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對世人進行倫理道德的教化。如《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的入話說道:“善惡相形,禍福自見;戒人作惡,勸人為善。” 在開啟正文講述之前先對讀者進行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非常明白地把正文故事所要講述的道理預先表達出來,這既是對宋元說話藝術入話功能的發展,也影響了后來明清小說的道德教化的表現形式。
二、“因果報應”模式——勸善意圖的強化
因果報應本是佛教思想,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因果報應的思想無論對上層統治者還是對下層百姓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點在“三言”中有非常豐富的表現。三言對前代故事的改寫在大體繼承原有情節結構的基礎上,又強化了因果報應的思想。
將《蘇知縣》與相關的本事進行對比,就會發現改寫后果報的觀念明顯增強了。《崔尉子》和《李文敏》故事中的兒子一個是赴試未中,一個干脆就不去應舉、直接報官了;雜劇中改為兒子考中武狀元,與當初張員外所救的趙興孫合力擒住陳虎,交由府尹懲處。馮夢龍采納了雜劇讓兒子高中的改寫,并且進一步發揮,讓徐繼祖(后改名蘇泰)中進士之后又被任命為御史,可以親自審案斷案,最后將徐能一干人等處死的判決也由徐繼祖親自下達。在為父親沉冤昭雪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較以往作品都大,這樣更加凸顯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果報思想,并且道德勸誡意識也非常明確,以因果報應的模式來強化懲惡揚善的意圖。
《蘇知縣》在情節設置上最大的創新就是增加了一個新的人物形象——徐用,他在作品中非常重要,是整個情節得以轉折的關鍵性人物。徐用是徐能的弟弟,在徐能的團伙中大家都稱徐用為“徐二哥”。哥哥徐能是個“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的水賊,弟弟徐用卻是一個“好善”之人。小說是這樣描繪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腳,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徐用在小說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
首先是間接保全蘇云性命。他發現徐能想謀害蘇云后一再加以勸阻,勸阻不成便懇求給蘇云留個全尸,使蘇云逃過砍頭的劫難,被捆綁作一團扔進水里,為蘇云保存了一線生機。
然后是幫助鄭氏出逃,保全其名節。徐能謀害蘇云后,貪戀鄭氏美色企圖據為己有,徐用于心不忍,于是將哥哥和一班兄弟通通灌醉,讓鄭氏逃走,又“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后門,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
“三言”中的許多篇章都有關于因果報應的描寫。如《施潤澤灘闕遇友》主人公施復在一次經商回來的路上撿到一筆銀子,沒有據為己有,反而在撿到銀子的地方等待失主回來尋找。后來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又意外地得到那位失主的幫助而渡過難關,拾金不昧的行為讓施復日后得到了善報,“三言”中還有大量贊揚友情、信義的故事。當然惡行就必然受到惡報,《桂員外途窮懺悔》寫桂遷忘恩負義,他的妻子、兩個兒子先后死去,又投胎為狗;直到后來誠心懺悔才可以“逾年無恙”,書中寫到:“輪回果報,確然不爽”,“奉勸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負心郎”。小說中人物的命運似乎受到了天道的支配,以天道來壓制社會中的丑惡,保證社會的安定,所以果報的模式進一步凸顯了作者道德教化的意圖。
三、奇巧的情節——教化意識的凸顯
“三言”中有不少以偶然巧合為情節基礎的作品。偶然和巧合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常見的,但在文學作品中可以通過情節的刻意安排得以實現。《蘇知縣》即運用了多種偶然巧合完成了情節的重構,這種重構不僅是藝術技巧層面的,也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它反映出當時比較普遍地存在于社會中的命由天定的思想,也反映出作者個人強烈的懲惡揚善的愿望。
先看男主人公的命運。在《崔尉子》和《李文敏》中,男主人公被惡人所害,真的遇難了。后來《合汗衫》雜劇改寫為男主人公死里逃生、得救脫險,從生與死的可能性上進行分析,很容易知道這種得救脫險實屬偶然。但《蘇知縣》沿用了雜劇的情節,寫蘇云被陶公救起,還被陶公帶回家中,由陶公牽頭,安排他在村中教學。這就為最后的大團圓結局埋下了伏筆,彰顯了好人自有好報的道德感召力量。
再看女主人公的遭遇,這是改寫的一個重點。男主人公的死里逃生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對女主人公是否“貞節”這個情況的處理。在元雜劇中我們看到的是女主人公被迫“從賊”,二十年來忍辱負重,伺機報仇,最終團圓。對于女主人公被迫失節的問題沒有過多的糾結,顯得十分寬容。而《蘇知縣》做了重大的改變,安排鄭氏逃走了。為保證鄭氏能安全逃走、保全名節并生下兒子,小說又安排了三個新的人物形象。前文所述的徐用為幫助鄭氏出逃將哥哥徐能灌醉。徐能家里的老仆人朱婆,本是徐能派來監視并勸服鄭氏的,也因為“十分可憐鄭夫人,情愿與他作伴逃走。”路上朱婆因年老多病擔心拖累鄭氏,勸鄭氏先走;又恐泄露了鄭氏的行蹤,“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干凈好人。望著路旁有口義井,將一雙舊鞋脫下,投井而死。”還有尼庵里的老尼,尼庵本是“佛地,不可污穢”,但老尼同情鄭氏,同意他到庵后的廁屋住下產子,孩子生下后,老尼“凈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價看覷鄭夫人。”后來又收留鄭氏到當涂縣慈湖老庵中潛住,鄭氏從此在尼姑庵生活下來,直到最后與蘇云“羅衫再合”。
這三個形象在鄭氏遭遇困境的時候先后出現,并且都在最危急的時刻給予她幫助,就每個個體而言實屬偶然,而聯系在一起又使讀者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數。他們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可以說偶然的背后是一種必然,我們看到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不顧自身的利益,救人于危難,有的甚至犧牲了生命,由于他們的出現,保全了女主人公的貞節,再次凸顯了道德教化的意圖。不獨《蘇知縣羅衫再合》,“三言”中的其他一些作品也表現了類似的主題。如《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女主人公被妖怪劫持之后,無論妖怪如何威逼利誘,堅決不愿屈從,惹得妖怪大怒,命人“管押著他。將這賤人剪發齊眉,蓬頭赤腳,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與他三頓淡飯。”張氏“寧為困苦全貞婦,不作貪淫下賤人”,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名節。
之所以會對“貞節”問題格外重視,應該是與理學在明代的巨大影響有關。一般認為,馮夢龍在晚明積極倡導“情教”,以情反理,受到了心學創始人王守仁的影響。但這并不全面。《元史·列女傳》是明代朝廷主持修撰的,其中《列女一》說道:“……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于過中,然較于茍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6]應該可以代表明代官方的立場,《明史》中記載的貞潔烈婦更是不勝枚舉,在這種觀念統治下, 既要完成最后的團圓以體現善惡終有報,又要保全女子的貞節,比較好的辦法就是安排女子逃走,或是以自己強烈的意志作為抵御。而這些安排必然會增加故事巧合與偶然的比重。情節的重構受到了社會歷史意識的影響,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理學統治下的社會,女性不再屬于自己,而是丈夫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即使是丈夫死亡也得不到改變,相反,社會規范要求女性在“夫死”之后進一步保持自己的貞節,以此捍衛丈夫對“妻子”這一私有財產的絕對控制權。所以女性對自己貞操的捍衛,某種程度上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她的丈夫、甚至是整個社會對她的期待與規定。所以三言中的這些女子越是表現出對貞節的堅守,越可以反映出社會意識形態對文學作品的強大力量。再看三言中的其他作品,《大樹坡義虎送親》中林潮音對素未謀面的勤自勵的堅守,并不是出于愛情,僅僅是因為二人已有婚約在先。《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中顧阿秀也因為自幼訂親,堅持從一而終;后來受惡人奸騙,“自縊身亡,以完貞性”。女子面對貞節問題的時候,常常顯得固執而堅決,她們的行為顯然不可理解為對愛情的追求,反映的是禮教強大的規范人心的力量。
通過對《蘇知縣》情節重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馮夢龍對“勸善懲惡”的不遺余力,為了達到教化的目的,往往加重情節中奇巧的成分,人為地設置人物的遭遇和命運,不惜犧牲故事的真實性,使果報的模式更加突出。遺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與元雜劇相比,明代的社會文化背景的烙印非常明顯地呈現出來,小說也因此部分地喪失了敘事的真實性和情節發展的正常邏輯,喪失了某種超社會形態的價值,沒有了元代作品那種渾樸與自然之美。但是他所做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隱藏在小說背后的作者的一顆熱誠的濟世之心,作為新思潮代表人物又與與理學家的思想觀念有本質的不同,他的小說絕非道德的傳聲筒。他說“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8]出對虛偽的名教、惡劣的社會風氣的極為不滿,提出以“情教”來改造社會,即使在“教化”中也不斷表現出對人性的關注,所以他承認并肯定這個現實的世界,肯定人們對物欲的追求,肯定商人的美好品德,甚至熱烈歌頌青年男女對愛情婚姻的自由追求。“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作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9]都是從“真情”這一社會理想出發,以情的方式向百姓說理,以情的方式來維系、重整社會秩序。所以馮夢龍在小說史上的意義不只是結構技巧、語言藝術層面的,而且是社會意識、道德意識層面的。如此,在一個個曲折離奇又打動人心的故事中,就會既有大膽進步的追求又有正統保守的說教,但無論哪種,都是在自覺地運用情教的模式,闡發、宣揚大致符合傳統儒學的道德觀念。因而道德說教與作品的情感內容間產生沖突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釋:
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154.本篇《蘇知縣》引文皆出于此版本,不另注。
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54.
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395-397.
馮夢龍.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287.
馮夢龍.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59.
參考文獻:
[1]馮夢龍.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3]馮夢龍.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4]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1.
[5]天然癡叟.石點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6]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7]臧晉叔.元曲選[C].北京:中華書局,1958.
[8]馮夢龍.情史類略[M].長沙:岳麓出版社,1984.
[9]馮夢龍.馮夢龍全集,第七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